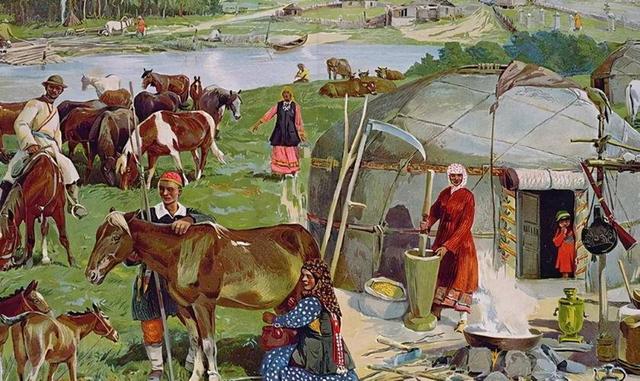乾隆三十年(1765年),因云南中缅边境上的两属(清、缅)土司与缅甸爆发了‘花马贡’争端、持续相互混战,导致清朝与缅甸贡榜王朝之间矛盾重重、冲突频繁,最终到了直接开战的地步。
乾隆三十年(1765年)七月,在清缅双方前期不断发生小规模冲突后,第一次‘征缅之役’(即第一次‘清缅战争’)爆发;但以云南地方绿营为主的清军征缅首战失利,清军前线最高长官、时任云贵总督刘藻也因指挥作战不力而被乾隆帝追责,最后在忧愤愧疚中自杀。
至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四月,新任云贵总督杨应琚又率云南地方绿营军队发动了第二次‘征缅之役’;起初,清军入缅作战顺利,原缅属的整欠和孟艮两土司管辖地均被清军占领。
但在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九月的新街(缅甸八莫)之战时,清军不敌缅军的进攻、失礼后败退回国,出征将士也伤亡惨重。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十二月,清缅两军又会战于陇川,但清军依旧不能取胜,且前方战线迅速崩溃,士兵多有溃逃败退回国;到了这个时候,原先一心主战的杨应琚也胆战心惊,赶紧派人到陇川与缅兵议和。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正月初四,按照与清军的和议内容,缅军原本准备从陇川撤军,但清军趁机进驻猛卯、以监视缅军撤军;这时候时双方因沟通不畅而发生误会,缅军于是围攻猛卯城,而清军在出城追击时损失颇大,和议顿时宣告失效。此后,杨应琚继续调兵上万人进驻木邦土司地区,与缅军持续对峙。
第二次‘征缅之役’爆发后,清军胜少负多、在战场上很被动,但杨应琚一味上捷报给乾隆帝,吹嘘清军大胜、前后杀敌过万人。乾隆帝在查阅战报时逐渐对云南军情产生了疑惑,心中疑云顿生,于是派御前侍卫福灵安(傅恒长子)前往云南、仔细调查实际战果后再将真实情况回奏。
福灵安抵达云南后,很快就搞清楚了战场实情,并据实以奏;乾隆帝雷霆震怒之下,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二月下旨逮捕云南提督李时升、总兵朱仑,押送进京问罪后处死。三月,云贵总督杨应琚也被逮捕进京,严加审讯后从宽赐死。乾隆帝并以伊犁将军明瑞(傅恒之侄、傅文之子)接任云贵总督,主持第三次‘征缅之役’。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四月,明瑞千里迢迢从新疆赶到了昆明,就任云贵总督;此后,明瑞用心筹备各项对缅作战的事宜及后勤筹划。
当年十一月,一切准备停当的明瑞兵分两路,亲率一万七千大军(内含满洲八旗二千人)作为南路军,由宛顶(云南畹町)经木邦、锡箔直捣缅都阿瓦(缅甸曼德勒);而参赞大臣额尔景额则分率八千军队(内含满洲八旗九百人)作为北路兵,经铁壁关、新街取猛密,再转兵南下与明瑞会合于阿瓦城下。

明瑞出兵后一路进军顺利,先后占领了木邦(缅甸兴威)、旧小、大叠江、锡箔、大山等缅属土司的管辖地,并在蛮结(缅甸南渡河以东)取得前所未有的大胜,克敌营垒十六座、斩首二千,生俘三十四人,缴获枪炮粮草牛马无数。此间,明瑞留兵五千人驻守木邦,以参赞大臣珠鲁讷为木邦守将,负责后勤辎重转运及后方防守重任。
之后,明瑞再接再厉,率兵深入,先克天险天生桥,又占据宋赛(缅甸送速)、邦亥,至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十二月十八,清军前锋斥候已经前出至象孔(缅甸辛古),距缅都阿瓦仅七十里之遥了。
但缅甸在明瑞大军来攻之下,在清军进军的道路左右坚壁清野、疏散军民,导致清军粮尽无法补充、马疲人乏,已经无力再发动攻城战斗,就此迟滞在象孔不前。
并且,清军北路军在十一月十六抵达老官屯(新街附近)后,与夹江树栅严防死守的缅军对峙作战,清军连日攻击不胜,伤亡惨重。就连主将额尔景额都患急病亡于军中;其弟额尔登额接任北路主将后庸碌无能、畏惧避战,一味退守。
而得知缅军小股军队已经出现在自己军营后方后,惶恐之下额尔登额擅自从老官屯前线撤军,退到四十里外的旱塔地区避战,由此开始徘徊不前,放弃了与明瑞大军会合的战前军事计划。
北路军由额尔登额代领、从老官屯前线撤军、退到旱塔地区驻扎、不能前来与南路军会师合攻阿瓦的坏消息传到了明瑞军中后,一心想要攻克阿瓦的明瑞在无奈之下,只得于十二月十九下达了退兵令,命全军退到孟笼(今缅甸孟隆)就食。
清军撤退后,缅军开始大举反击,并将主力军队用在攻击木邦的方向,以断绝明瑞大军后路;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正月初二,缅军将清军所设的天生桥、蛮结、蒲卡、锡箔等处后勤台站一一攻克,明瑞大军的后勤情报线路被断。
正月初八,缅军数万人包围了木邦,围攻十日后克城,珠鲁讷自杀尽忠,清军大部分溃散逃回云南。此时,明瑞已经在孟笼休息了十多天,还在这里过完了春节;听闻木邦被围且失守后,明瑞于正月初十由孟笼向宛顶方向撤退。

正月十四,因缅军紧追不舍,明瑞在退兵途中于蛮化突然出兵反击,痛歼缅军,使其不敢再追得那么紧;二月初七,清军抵达小孟育,距离宛顶边境只有二百里了。
明瑞命全军在此休息了三日,然后在二月初十夜间沿探明的小路突围,明瑞率副手参赞大臣观音保、领队大臣紥拉丰阿,及精锐御前侍卫及八百名八旗军殿后、掩护总兵哈国兴、常青、本进忠等率领的大军主力撤退。
在与缅甸追兵的激战中,领队大臣紮拉丰阿中枪阵亡,参赞大臣观音保在重伤后为了避免被俘,以携带的最后一支箭刺喉自杀;明瑞也在断后作战中身受重伤,在用尽力气疾驰了二十多里后,自知无法脱险的明瑞自尽殉国,并‘手截辫发、取扳指授其仆归报,而缢于树下,其仆以木叶掩尸去’。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二月十三及十四两天,在总兵哈国兴、常青的率领下,由小孟育突围的上万名清军安全地回到了宛顶,其中还包括了大批伤病员及体弱文官。
留守云南境内的参赞大臣阿里衮和云南巡抚鄂宁,从撤退官兵口中得知征缅主将明瑞和副手观音保、紥拉丰阿,及部分八旗精锐留下断后,没能一起返回时,大惊失色后立即将撤回来的将士文官们分开软禁,随后加以详细审讯。
与此同时,携带着家主明瑞的发辫扳指、突破了重重险阻从小孟育脱险回国的明瑞家仆们,也安全抵达了宛顶,随即也见到了阿里衮和鄂宁。
意欲从撤退将士们和明瑞家仆的口中查明明瑞没有随同主力突围、最终失陷缅甸境内的‘真相’的阿里衮和鄂宁,在经过数天的严格询问后,终于证明了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事实——身为征缅主将的云贵总督、一等诚嘉毅勇公明瑞,在此次撤军突围的关键时刻,居然是主动带着副手和少数的精锐为北撤大军断后,且在后续的激战中壮烈殉国!
查明实情后,阿里衮和鄂宁立即向乾隆帝上疏,将整个事情的原委完整地汇报给乾隆帝;与此同时,阿里衮和鄂宁派人护送明瑞家仆奉其发辫扳指返京、以赴其家告哀,再将徘徊不前、贻误战机、违抗圣旨的北路清军主将参赞大臣额尔登额、副将云南提督谭五格弹劾至乾隆帝御前,请求严查这两名‘无耻败类’。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二月二十八,京师中忐忑不安等候前线军报的乾隆帝,从阿里衮和鄂宁的六百里加急奏疏中得知了明瑞的确切消息——南路清军征缅作战失败、但大部分军队已经安全撤回云南境内,可主帅明瑞、副将观音保、紥拉丰阿为掩护大军撤退而主动留下断后,已经壮烈战死疆场!
而从缅甸撤退回来的将士文官的详细笔录,以及明瑞家仆带回其家主发辫扳指之事的询问记录,还有弹劾额尔登额、谭五格的奏疏,阿里衮和鄂宁也一并送到了乾隆帝的御案上。
自己深为看重、一心着重栽培的俊才能臣、外侄明瑞断送在了缅甸崇山峻岭中的惊天坏消息传来,让乾隆帝伤心哀痛不已,而明瑞之亡,北路军主帅额尔登额、副将谭五格不可推卸其罪!
在怒不可遏之下,乾隆帝命阿里衮、鄂宁将额尔登额与谭五格逮捕进京,严加审讯,又特命明瑞叔父——领班军机大臣、保和殿大学士傅恒为主审,会审二人、明定其罪。
因征缅之役已经失去了一个儿子(福灵安)、一个侄子(明瑞)而心痛哀悸不已的傅恒,虽然对额尔登额与谭五格咬牙切齿地痛恨,但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及清晰的思维逻辑,在审讯中逻辑严密、询问严厉而缜密,使得额尔登额哑口无言,毫无辩解余地,老老实实叩头认罪,承认自己‘贻误战机、坐视主将失陷、有心玩误’的罪名。
审讯结束之后,傅恒立即将审讯结果上报给乾隆帝,建议将额尔登额判处‘磔刑’,乾隆帝立刻批复同意,且没遵循秋后行刑的惯例,在判决的当月就把额尔登额拉到了菜市口直接行刑,同案犯谭五格则减刑一等斩首弃市。

因第三次征缅之战虎头蛇尾、先胜后败,就连全军主将明瑞也殁于战场上,乾隆帝在羞恼惊怒之下,决心发动第四次征缅之役,一定要将敢于冒犯天朝上国的蕞尔小邦缅甸给降服,以保全朝廷的颜面。
而缅甸在‘第三次清缅战争’中虽然成功地击败了清军,但也暴露出了缅军不擅长平原野战、不能完成‘歼灭战’的弱点;此外缅甸统治者对清军强大的攻击力以及清朝雄厚的国力也有了清楚的认识,深知继续与清军进行长期作战实在是勉为其难。
另外,缅甸虽然此时已经攻灭暹罗(泰国)大城王朝,但暹罗国内的抵抗势力在郑信(吞武里王朝建立者、华裔)的带领下,依旧在国内不断发动起义,且屡屡击败驻暹罗的缅甸军队,这让缅军头疼不已,对缅甸在暹罗的统治也产生了极大的威胁。
因此,两面受敌、无心也无力与清军再战的缅王孟驳,在刚刚取得对清军的胜利之后,就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四月,释放了在木邦被缅军俘获的八名清军士兵,让他们带回来孟驳亲书的‘求和文书’,想要与清朝息兵议和。
但乾隆帝认为缅甸之前多次出兵侵扰西南边陲,而刘藻、杨应琚、明瑞前后三任云贵总督都因征缅之役不顺而丧命(一人羞愧自尽、一人赐死、一人不屈自戕),于是坚决不肯同意缅王的议和请求,反而降旨说缅王既有悔罪乞降之意,必须“束身归命、或专遣大臣前来递上降表,方允和议。”
乾隆帝的这种不切实际的要求,缅王孟驳自然也不干,清缅之间的和议宣告破裂;第四次‘征缅之役’即将开打。
为了毕其功于一役,彻底击败缅甸贡榜王朝,乾隆帝随即下旨调集了前所未有的精兵强将,准备对缅甸发动规模庞大的第四次进攻;而原来曾跟随明瑞第三次出征缅甸的满洲八旗全数调回内地(以防影响作战士气),另调关内外的八旗一万三千人、贵州绿营兵九千人赶赴云南参战(后来又加派了八旗兵一万人、福建水师两千人入云南参战)。

至于第四次征缅作战的主帅人选,还没等乾隆帝下旨挑人,时任领班军机大臣、保和殿大学士、一等忠勇公傅恒就自告奋勇、向乾隆帝自请‘督师’,要亲自前往云南统帅军队出征缅甸(为死去的儿子和侄子报一箭之仇,同时也是要向乾隆帝表明自己的态度)。
乾隆帝对傅恒的自荐当然十分满意,于是授予傅恒‘经略’之要职,就任第四次征缅主帅;另外,乾隆帝并以已经在云南处理军务的阿里衮为副将军,协助傅恒指挥作战。
为保此次作战万无一失,乾隆帝还任命了舒赫德为参赞大臣,先期赶赴云南,与由云南巡抚晋升为云贵总督的鄂宁进行先期的作战筹划准备,以备后续(第四次)展开的征缅之役顺利进行。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四月,先期到云南筹办后勤粮草事宜的舒赫德,在赴永昌(云南保山)前线实地考察之后,与新任云贵总督鄂宁联合给乾隆帝上疏,说明了征缅之役的五个难题——
一、出兵所需的十余万匹军马、驭马难以办齐。
二、按十个月的战争进程算,兵粮共计四十二万石,云南全省难以供应严充足。
三、大军行军路程困难,由永昌至缅甸境内的地形道路更差。
四、军粮转运,所需民夫约百余万人次,而境外作战,雇用役夫更是几乎不可能完成。
五、云南气候多瘴、水土不适北方人长期留驻,前几次的战事,清军因病死亡或失去战斗力的比战死的还多。
所以,舒赫德、鄂宁认为‘征缅实无胜算可操’,建议乾隆帝还是以招安和议为上,设法将缅甸重新纳入朝贡体系内,以免再动刀兵而损害国家元气。

可惜,对舒赫德、鄂宁的正确建议,乾隆帝不但没有接受,反而暴怒不已,痛骂两人‘行事乖谬、无耻之见’,革去了舒赫德的尚书、参赞大臣官职,回京待勘;鄂宁则直接降职,改授福建巡抚。
之后,乾隆帝召时任伊犁将军阿桂(明瑞的继任者)回京,授其兵部尚书之职,以备云南作战听用;六月间,乾隆帝又命阿桂出任新任云贵总督、副将军,与阿里衮一起辅佐傅恒指挥征缅之役。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十一月,阿桂抵达了云南永昌前线,与另一位副将军阿里衮会合;乾隆帝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初,以明德接替阿桂为云贵总督,以便使阿桂能专心于征缅军务。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二月,在做好了赶赴云南指挥作战的一切准备后,经略、保和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一等忠勇公傅恒率大军从京师出发,赶往云南会合副手——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参赞大臣阿里衮,内大臣、兵部尚书阿桂,预备率军第四次出兵、征讨缅甸贡榜王朝。
傅恒出征之时,在皇宫太和殿向乾隆帝陛辞,乾隆帝则亲自为傅恒授‘敕、印’,并把自己阅兵时所穿的甲胄也赠给傅恒,以此表示对傅恒的绝对信任和殷切期望,希望傅恒到云南后旗开得胜、一举击败并降服缅甸。
那么傅恒的‘第四次征缅之役’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和结果呢?下一篇文章继续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