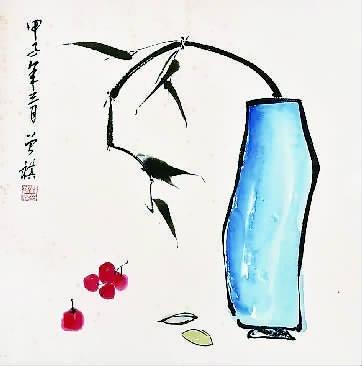
春华
与汪曾褀的文字初次相遇,缘起于故乡宣化的葡萄。十多年前,宣化作协组织编著《宣化葡萄香天下》,我负责组稿,每天和描写宣化葡萄的文字打交道。偶然在北京图书大厦买书,邂逅了汪曾褀的《葡萄月令》,开卷惊艳,先生对宣化的葡萄如此用笔:“一月,下大雪。雪静静地下着。果园一片白。听不到一点声音。葡萄睡在铺着白雪的窖里。”
《葡萄月令》从一月写到十二月,一脉天然灵动,山溪般流淌,不修饰、不造作、不刻意、不呆板,灵动而自在,随性又隽永。所有的修辞手法,在这天然去雕饰的文字面前,都黯然失色。一种柔软而温和的力量从文字深处,一直熨帖到读者心里。
作者写到葡萄喝水:“浇了水,不大一会,它就从根直吸到梢,简直是小孩嘬奶似的拼命往上嘬……”整篇文字口语化,却充满诗的节奏韵律,这其中包涵着作者丰富而深厚的生活阅历。汪曾褀的文字,原本经过江南水乡的浸润、西南战火的淬炼、坝上风沙的洗礼、戏剧舞台的打磨,可谓百炼钢,化为绕指柔。
提到葡萄开花时:“都说梨花像雪,其实苹果花才像雪。雪是厚重的,不是透明的。梨花像什么呢?——梨花的瓣子是月亮做的。”平凡的字眼,组成平凡的句子,讲着一个平凡的事物。却在平凡之上,让人忍不住击节赞叹。
《葡萄月令》不仅记录着我家乡葡萄,绵延千年的前世今生,更可洞见一个有趣而高远的灵魂,他爱着这世界,恰似草木对光阴的钟情。
读汪曾褀的散文,可以感觉,他对生命自身的任何一种细微的情绪,都充满欢喜与好奇。“生鸡活鸭、鲜鱼生菜、碧绿的黄瓜,彤红的辣椒”都认为他们在“热热闹闹,挨挨挤挤”中“感到一种生之乐趣”即使在下放劳动期间,他也同样在艰苦的环境和劳动中,时刻发现美,认为给葡萄喷波尔多液“这活儿有诗意”;在坝上采到大蘑菇,也要陶陶然带回北京,给全家人做一碗汤;一顿莜面窝窝,让他反复回味,自言这是一辈子很少吃到的好东西;因为把唱戏的女工“打扮得如花似玉,几个女工高兴得不得了”而感觉到生命的价值;被发配到坝上画马铃薯叶子,他说是“神仙的日子”……
汪曾褀,便是如此重视生命的每一份际遇,体验生活的每一个过程,并在其中寻觅到,真实而超然的诗意境界。
汪曾褀的小说,如一幅原生态的民俗风情画,在面前徐徐铺展,没有主题的深奥玄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如听一位垂暮的老者,栖身在古旧老屋的躺椅上,向你娓娓道来,讲述左邻右舍,发生在身边的趣事,悭吝的八千岁、渡船上身世凄苦的卖唱男女、卖杂食而天赋《异秉》的王二、身陷生活的泥沼依然向往着美好的《辜家豆腐店的女儿》……
从贩夫走卒到高人名士,那些细小琐屑的题材,是一粒粒细小的种子,被作者的用心收集,随意地栽种在文字的土壤里,鲜活着开出花来,天然明媚。
我曾用心在汪曾褀的作品里,寻找他在张家口生活过的痕迹。在小说《七里茶坊》中,他写道:“我很喜欢七里茶坊这个地名”汪曾褀说:送客上路的,到了这里,客人就说:“已经送出七里了,请回吧!”主客到茶坊又喝了一壶茶,说了些话,出门一揖,就此分别了。七里茶坊一定萦系过很多人的感情。不过现在却并无一家茶坊。我去找了找,连遗址也无人知道。时至今日,我们的城市,茶马古道的起点,遗憾的是,茶坊这个地名已然丢失了。汪曾褀当时下放在张家口,住在“碗大炕热”的车马大店里,做着掏公共厕所、刨粪冰的工作。每天蘸着麦麸大酱吃莜面窝窝,喝着蒸锅水,抽着掺了榆树叶子的烟,记载着文化馆的快板“天寒地冻白不咋,心里装着全天下。”这个“白不咋”本地人听了,都会会心一笑。
在骡马店的大炕上,汪曾褀欢喜着他的位置:离灯近,可以看书,没酒,四个人聊昆明的美食,聊坝上的山川风物,聊怀来的“青梅煮酒”,三个工友一起,给合同工小刘凑钱娶媳妇。
文章的最后,风雪夜来的几个坝上赶牛人给作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过年,怎么也得叫坝下人吃上一口肉!”我老是想着高个儿这句话,心里很感动,很久未能入睡。这是一句朴素的、美丽的话。”
一个身陷泥潭的人,依然以旷达、平和的心态,深爱着这个世界,已知乾坤大,尤怜草木青。在人们纠结于月亮与六便士的取舍,而陷于迷茫错乱的现实世界,汪曾褀以一生的沉淀,写出至淡至浓的优雅与情致,用他温润的人格魅力、达观超然的名士情怀,依然,治愈着无数迷路的心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