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的夏秋之交,安徽大地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旱灾。整整十个月,天空如同被厚重的幕布遮盖,滴雨未下,导致全省大片区域陷入干旱的深渊。六千多万亩肥沃的农田饱受摧残,仿佛一夜之间失去了生机;四百多万民众与二十多万头牲畜面临着饮水难的严峻考验。在那些受灾最为严重的地区,上半年刚刚栽种下的幼苗和脆弱的幼竹,几乎无一幸免地枯萎在了焦渴的土地上。

这一年,安徽省的粮食总产量锐减至1482万吨,与1976年相比,减少了整整200万吨,人均产粮也相应下滑至314公斤,每人减少了55公斤的口粮。在缴纳公粮、集体提留以及预留种子之后,农民们手中的口粮所剩无几,许多地方的百姓甚至不得不再次踏上外出乞讨的艰难路途,只为在这荒年中寻得一线生机。而随着秋季的深入,旱情非但没有缓解,反而愈发严峻,秋种工作几乎无法开展。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天灾与人祸交织的困境,安徽省委展现出了非凡的勇气与智慧。一方面,他们迅速组织起全省的人力、物力、财力,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抗旱救灾的战斗中;另一方面,则积极研究制定减灾度荒、摆脱困境的有效策略。1978年9月1日,一个紧急而意义重大的省委常委会议在万里的主持下召开。

会上,万里同志语气坚定,目光如炬,他提出:“我们必须不遗余力,想尽一切办法确保秋种工作的顺利进行,为明年的夏季丰收奠定坚实基础。”“我们绝不能眼睁睁看着大片土地荒芜,那样只会让我们的处境更加艰难。与其让土地闲置,不如将其划分出来,借给农民个人耕种。我们要竭尽全力种好小麦,还要广泛种植蔬菜,特别是胡萝卜,以帮助我们度过这个难关。在这干旱肆虐的特殊时期,我们必须打破常规,采取特殊政策来战胜这场灾难!”
经过常委们的深入讨论与权衡,会议最终形成了一个大胆而富有创新精神的决定——“借地度荒”:对于那些集体无力耕种的土地,将其单独划分出来,借给农民个人耕种;对于超出计划扩种的部分,收获时不计入征购范围,由生产队自行分配;同时,鼓励农民充分利用村旁、宅旁、路旁、水旁的空闲地以及开荒地,广泛种植粮食和蔬菜,收获归个人所有,无需上缴国家。

这一政策的出台,犹如一股春风拂过干涸的心田,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生产自救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原本荒芜的边地很快被油菜、蚕豆和小麦等作物覆盖,秋种任务不仅顺利完成,还超额完成了当年的目标。据统计,仅“借地度荒”这一项措施,就为全省增加了1000多万亩的秋种面积。到了1979年夏收之后,旱灾的阴霾逐渐散去,安徽省的农业生产迅速恢复,这一转折点的到来,与省委“借地度荒”的英明决策密不可分。更为深远的是,这一“借”字,如同一把钥匙,悄然打开了通往“包产到户”改革浪潮的大门。
1979年春,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深入贯彻,各地纷纷探索并推行了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其中尤以包产到组和包产到户最为引人注目。这些新的责任制形式直接对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传统管理体制提出了挑战,自然也引发了一些思想保守者的质疑和反对。一时间,关于联系产量责任制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引发了一场规模空前、影响深远的大讨论。
从乡村到城市,从政府机关到街头巷尾,从工厂车间到学校课堂,每一个角落都在热议着这场农村改革的利弊得失。人们仿佛打开了话匣子,各抒己见,争论得不可开交。这场改革不仅震撼了农村,更震动了整个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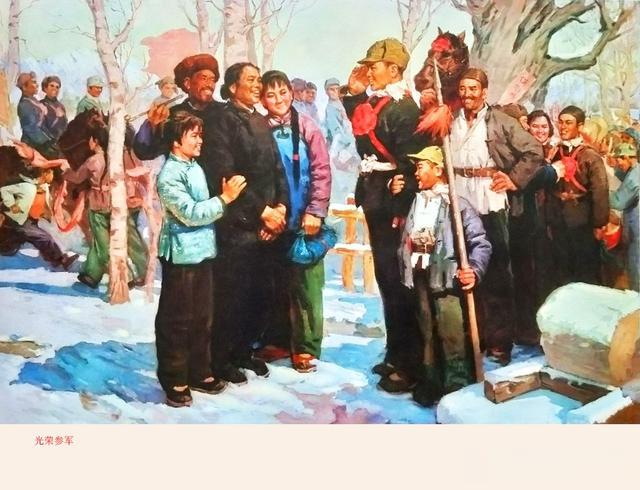
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万里同志始终保持着头脑的冷静和态度的坚定。他在各种会议和场合反复强调:“对于农村改革,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被外界的流言蜚语所干扰。”“各种形式的责任制都应该在实践中相互竞争、相互比较,从而得到发展。只要能够增产、增收、增贡献,就是好办法。”“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分田单干的潮流岂是几个人能阻挡的?”
“省委对于各种形式的责任制不搞派性,不偏向任何一方,而是让群众在实践中去鉴别和选择。”“对于各种形式的责任制,我们要试验一年,年终再进行总结。”万里还特别叮嘱我们,当前农村责任制形式多样,干部群众的认识存在差异,我们要密切关注农村的动态,及时汇报情况和问题,为省委的决策提供依据。

1980年4月27日,在陈庭元的精心安排下,凤阳县委政策研究室郑重印发了《关于板桥区实行“包产(干)到户”情况的调查》一文。这篇报告紧随小岗生产队包产到户的调查报告之后,再次将焦点对准了包产到户这一改革实践。
次日,中共板桥区委会便下达了《关于农业生产实行“包产(干)到户”责任制的几点意见》,这份文件不仅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农村首个关于“包产到户”的管理办法,更标志着包产到户在政策支持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这两份材料的印发,不仅表明了凤阳县委对包产到户的正式认可,更为其正名,为其后续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同年6月中旬,随着上述两篇文章的广泛传播和县委的明确态度,包产到户在凤阳县掀起了第二轮高潮。板桥、小溪河、总铺三区除少数社队外,几乎全面实行了包产到户;刘府、武店区也出现了“明组暗户”的现象;大庙、门台区的包产到户户数也急剧增加。面对这股势不可挡的改革浪潮,凤阳县委于7月4日作出决定,允许东三区的板桥、小溪河、总铺实行包括包产到户在内的各种责任制;而西四区的刘府、武店、大庙、门台则暂时只实行包干到组。

随着包产到户在凤阳县绝大多数地区的广泛推行,县委深刻认识到,与其被动地跟在群众后面,不如主动出击,尊重群众的意愿,因势利导,站在群众的前面引领这一新生事物的健康发展。邓小平同志对包产到户的支持,实质上是对农民的解放,是对生产力的解放。
如果说,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分得土地是第一次解放,那么包产到户无疑就是他们的第二次解放。尽管第一次解放让农民成为了土地的主人,但随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却让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被僵化的经济体制所束缚。事实证明,即便是社会主义制度,其体制也存在僵化的可能。为何在同样的土地上,人民公社的大集体就难以提高粮食产量?而农民包产到户后却能显著增产?为何政府全力以赴的行政领导、各级党组织的思想政治工作以及全国树立的大寨典型都无法达到预期效果?

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与他们的利益并未直接挂钩。有这样一个生动的例子:一位农民在生产队铲地时,手握锄头,一边铲地一边念叨:“这一锄是给队长铲的,这一锄是给会计铲的,这一锄是给保管员铲的,这三十锄是给那三十户铲的,最后这一锄才是给自己铲的。”这句话,道出了当时农民心中的无奈与期盼,也从一个侧面诠释了包产到户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邓子恢,这位深谙农民运动与农村工作的共产党领袖,他的足迹遍布田野乡间,用一颗真挚的心去倾听农民的声音,去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在整个农业合作化的浪潮中,他坚持实地考察,将保护农民利益不受侵害视为开展一切农村工作与合作化运动的金科玉律,这成为了确保合作化平稳推进的坚固基石。他深刻洞察到农民心中那份对私有财产的强烈依恋,以及他们思想上的保守与落后,这些都与合作化的理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因此,他反复强调:“我们必须谨慎行事,既要积极引领,又要稳步前行。”同时,他特别强调要尊重农民的自主选择,保护他们土地财产的私有权利,认为“无论是互助组还是合作社,都是建立在私有基础上的合作,如若不加以保护,侵犯了他们的私有权,他们便会失去积极性。”邓子恢的这番言论,无不透露出一位老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既尊重又引导农民走向共同富裕道路的赤诚与智慧。
1953年7月,邓子恢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更是将他的思考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他从改善农民生活水平与推进农业机械化的双重维度出发,深情回顾了解放前农民生活的艰辛,他们依靠地瓜、糠菜勉强度日,饥饿如影随形。解放后,特别是土地改革之后,农民们渴望生活有所改善,能够吃饱穿暖,有余粮以备不时之需。同时,随着工业的发展与城市人口的增加,对粮食的需求也日益迫切,因此,增产粮食成为了农业发展的头等大事。

然而,当时中国的农村经济还停留在畜力耕种、人工灌溉、自然肥料的传统小农经济阶段,这种模式既不利于机械化作业的推广,也难以满足现代农业发展的需求。为此,邓子恢提出,必须通过互助合作的方式,逐步改造农民的土地私有制,引导其向农民自愿的土地集体所有制过渡。
他还从政治的高度阐述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指出:“小农经济要么向社会主义的大农业发展,要么向资本主义的大农业发展。而我们坚决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能在土地改革完成后,让农村经济长期停滞在小生产、小私有的个体经济层面,更不能让基于小农经济自发滋生的资本主义势力肆意扩张。因为这将重蹈覆辙,使中国农民再次陷入少数人富裕、多数人贫困的两极分化困境。”基于此,邓子恢强调,对小农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是坚定不移的,任何动摇都可能危及国家的未来。

邓子恢所倡导的以包产到户为核心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无疑是他责任制思想中的璀璨明珠,不仅在当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更为后来的农村改革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包产到户,将家庭作为基本的承包经营单位,极大地降低了劳动监督的成本,几乎消除了内部消耗,激发了家庭成员前所未有的积极性与责任感,这是以往任何承包制度都无法比拟的。同时,以家庭为生产单元,充分发挥了其灵活性、机动性以及精耕细作的优势,为农业生产注入了新的活力。
然而,我们也应理性地看到,包产到户这一制度并非完美无缺。其局限性主要体现在:农产品的最终分配权并未完全掌握在农民手中;农民报酬的计算过程复杂繁琐,投入与收益之间的关系不够透明;生产队内部仍存在平均主义的残留现象;包产到户的权力实际上仍集中于干部手中。

值得庆幸的是,随后兴起的包干到户(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些不足,农民们“缴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真正实现了权力的下移,让农民成为了自己命运的主人。这一变革,不仅是对包产到户制度的超越,更是中国农村改革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