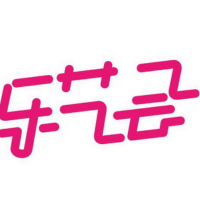综上所述,我们大致可以了解以下信息:
第一、在北宋中叶苏轼时代
北宋熙宁年间苏轼苏辙兄弟已经泗州水路中咏叹镇水大神僧伽,在祷雨时也需咏叹供奉水神僧伽,而且分别已经提到了泗州的镇水大神僧伽,与泗州龟山下被锁着的水妖无支祁,但是,大致由于那时僧伽降服无支祁的传说还没有成型。所以镇水大神缺乏一个契机与舞台,去顺手降服就在山下的水妖。而与苏轼同时代的蒋之奇虽然竭力传播僧伽神迹,但是在其三十六化中也没有僧伽降水母的故事。由此可见,在北宋的苏轼时代,佛家治水大神僧伽已经作为祈雨、水路平安的护佑者存在于官民观念之中,而且僧伽圣地泗州塔附近的龟山下,锁着被大禹制服的巫支祁的观念,也同样根深蒂固,但是那个时候,僧伽与巫支祁之间,还缺乏一个触发因素,双方没有发生直接关联。大致是佛家对于僧伽制水母的说法还没有完全成型。第二,北宋后期张耒饶节时代这个时候,经过佛家的持续推动,张耒已经可以脱口而出,在僧伽道场的泗州,是由佛家的神灵制服着龟山的水妖巫支祁,而当时在泗州的佛教大神,治水大神就是僧伽无疑。而同时代的饶节,在诗歌中已经将龟山下的水妖称为了水母,也提到了僧伽塔下的老和尚,而且身为佛家和尚的饶节,也没有去提及制服水母的就是佛家的僧伽,可见,佛家推动的水母传说获得了阶段性的成功,但是以僧伽取代大禹的努力还没有展开,还缺乏契机。而同样在徽宗时期,黄河也埋下了无支祁的铁像。佛家推动的将降服无支祁的传说纳入佛教系统的努力得到了有效的成果。虽然佛教派去降服无支祁的神灵的面目到底是否就是僧伽还不够清晰。第三、南宋中叶朱熹罗泌时代直到南宋中叶,大文人罗泌终于开始张口去引述了佛家的僧伽镇压水妖水母的传说。但是他也特别强调了自己的立场,就是以佛家僧伽治水母之事为非。而大知识分子朱熹的态度就更加鲜明,他引述僧伽镇压无支祁,就是为了否定这个离经叛道的传说。这个时候,僧伽所制服的到底是水母,还是巫支祁,已经在社会传播中互相客串,彼此替代混淆了。第四,南宋中叶的王象之时代王象之已经反复将僧伽降水母的观念牢牢地记住而且作为地理文献加以认真的记载了。也就是说,王象之已经接纳了佛教推动的僧伽降水母的创造,佛教所创造的僧伽降服水母的传播运动彻底成功。
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宋代社会上、佛教文化中存在着鼓吹僧伽镇压了无支祁的神迹传说的强大动力,而且这种传说愈演愈烈,北宋初年的苏氏兄弟、苏门学士张耒也许只要闭口不谈降服无支祁的是僧伽(假设那时已经有此传说),就能洁身自好,而南宋时期的罗泌、朱熹已经无法回避这个传说,而不得不先引述,再加以自证。可见僧伽降服水母(无支祁)的说法,非常可能就是肇始于北宋,而盛行于南宋,虽然一直没有获得士大夫阶层的认可接纳,但是却在社会基层流播甚广的佛家传播景点案例。
南宋洪迈的《夷坚志》立意第三方叙述立场,专一转述他人叙述,在如此鸿篇巨制中,虽然有若干篇幅涉及泗州大圣的叙述,但是极少叙述到泗州大圣降服巫支祁。
当然,南宋洪迈在《夷坚志》不提泗州大圣制水母,可能也有别的因素,因为《夷坚志》这个书名出自《列子.汤问》:《山海经》为"大禹行而见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坚闻而志之。"大意是指《山海经》中的故事是大禹看到的,伯益取的名,夷坚听说后记载下来了。可见洪迈是以夷坚自谓,将其书比作《山海经》。那么,既然洪迈将自己的书比拟为山海经,将自己比拟为记载大禹见闻的夷坚,又怎么能够帮助佛家去将僧伽取代治水妖的自己崇拜的大禹呢?直到元代陶宗仪,他在《南村辍耕录》卷 29“淮涡神”中陈述说“泗州塔下,相传泗州大圣锁水母处,缪也”。到了明代的胡应麟,也还坚持认为:“罗泌 《路史》辩有无支祈,世又讹禹事为泗州大圣,皆可笑。”可见正统的士大夫主流意识中,只有大禹降服巫支祁才是正经,其他皆为荒诞不经。这种文化传统一以贯之。
第五、其实,争夺对治水、制水妖话语权,是儒释道三家共同的目标。
三家互相竞争博弈,运用历史机遇为我所用。而且盘根错节,此消彼长。
道家对佛家的压制在崇道为国策的北宋是十分明显的。所以佛道之争是北宋时期的基本底色。
作为儒家以及此后理学家,他们遵守儒家王道的大禹治巫支祁的经典话语,而视其他的说法为怪力乱神,比如,朱熹不仅认为佛家的僧伽制水母为荒诞不经,而且对道家的许逊斩蛟,道家水神二郎神都嗤之以鼻。
但是儒生、士大夫们批评得最多的,还是佛家的僧伽制水母,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佛家在因势利导运用淮泗水患推出僧伽制水母的战略获得了巨大成功,而优先成为了社会舆论的高地,所以被士大夫们也最为优先地焦虑、警惕和反感。而道家并没有成功地利用这次水患的历史机遇。
早在北宋早期,著名理学家程颢(1032年—1085年)就曾经对佛家的僧伽信仰信徒不以为然,统称为”兴妖之人“,他曾与人有这么一段对话:
“某常至泗州,恰值大圣。见及问人曰如何形状,一人曰如此,一人曰如彼,只此可验其妄。兴妖之人皆若此也。昔有朱定亦尝来问学,但非信道笃者。曾在泗州守官,值城中火,定遂使兵士舁僧伽避火。某后语定曰,何不舁僧伽在火中,若为火所焚,即是无灵验,遂可解天下之惑;若火遂灭,因使天下人尊敬可也,此时不做事待何时邪?惜乎定识不至此。”
到了南宋,不仅朱熹对僧伽制水母不以为然,理学家黄震也在《黄氏日钞》中,记载了张栻对待僧伽的态度,他视僧伽信仰为无义理者,而且将僧伽组合造像直接投到江中了事:”旧祈祷无义理尽除之,只到社坛、风雷雨师坛及于湘南楼,望拜尧山漓江。遣官奉祝版瘗山投江,而雨大集。庶使邦人益信土偶之非所当事,而山川是为神灵也。又云舜庙堂庑有库之神在焉,武后亦剿。入庑下又僧伽一部亦在焉,即日投畀江中。庶几,一庙之内四门穆穆耳“。
第六:从佛家角度,非常可能,佛教的策略就是,以治水大神僧伽出面,在其保佑水运,祷雨治病的传统神格之外,去新塑造一个制服水妖的新神格新传说
开始的时候,并没有与传统传说中根深蒂固的大禹制服巫支祁去正面对抗,而是先让僧伽去制服一个叫做水母的水妖,等条件成熟,传播有了根基,然后逐渐将水母迭代融合无支祁,开始去冲击原有的旧传说,最终以僧伽制无支祁取代了大禹制无支祁。所以苏轼张耒们既然在嘴巴里说的是巫支祁而不是水母,而饶节就算说出了水母,但是他们都没有去关连僧伽,也许那时僧伽还真的没有开始去制服无支祁的具体推动,到了南宋,僧伽制服水母已经成了一种广泛的社会传说,南宋中叶,罗泌提到的是僧伽制水母,同时代的朱熹说的是僧伽制服巫支祁,南宋中叶,王象之一面将无支祁称为水母,在同一本书中也称其为圣母,可见,南宋中叶,乃是僧伽制服无支祁传说的融合、过度、纠缠期。各种说法正在迭代、变形、发展之中。由此我们大致可以设定,佛家所推动的僧伽制服巫支祁的传说,大致在南宋中叶逐渐成型。从这个角度,僧伽制服巫支祁的主题花钱,其早期模板,其大致时间范畴也或可以呼之欲出。



僧伽制巫支祁的历史契机
综上所述,僧伽在唐代就是水运的护佑神,到了北宋,也一直成为航运保护神,被祷雨的水神,到了南宋,编刊于绍兴二十四年至二十七年(1154 ~ 1157) 间的《能改斋漫录》中提到“僧伽居泗,以制潦水之冲”。南宋时期,许多桥上供奉僧伽像以祈求水流安澜。胡锉《舍步修泗州阁疏》曰:“地名舍步,江面阔远,渡水者多溺,众议欲造泗州佛阁以拯救者。“所以僧伽作为水神的基本神格是稳定而延续的。同时,至少在两宋时期,佛家存在推动僧伽制巫支祁传说去迭代大禹治巫支祁的持续动力,但是光靠佛家单方面的一厢情愿的推动,也不容易去改变多年固有的大禹治巫支祁的根深蒂固的儒家王道传统观念。况且,在北宋后期的张耒饶节时代,就算佛家已经成功地传播了金仙制服巫支祁的泗州传说,也已经推出了龟山水母,强化了泗州水妖与佛家的关系,但是也没有一举成功推出镇水妖传说的主人公就是近在咫尺的佛家大神泗州大圣。同在泗洲的镇水大神僧伽与兴风作浪的水妖巫支祁,还在冷静地互相凝视,那么,是通过什么动因,让一个天然大正派与天然大反派彼此接驳上的呢?要促使佑国佑民的大神灵与祸国殃民的大妖精对上戏,最完美的契机,就是大灾难,只有大的灾难,才能既体现妖怪的难以制服的祸害能力,以及由此造成的灾难之深,又让政府小民都将此归于妖怪作乱,由此凡间众生苦苦哀告,人间帝王束手无策,这才给了大神灵大英雄一个合适的舞台,大英雄的出场才具备必要的前提。而且这个灾难一定要具备地理上的对应性,这样才能使得大家把该地发生的灾难理所当然地归罪于当地的大妖精,同时,对本地大神灵的祈祷也才变得如此正当和必要。那么,是什么动因撬动了泗州大圣与龟山巫支祁对战的齿轮呢?南宋以前,淮泗水患时多时少,但是总体上还没有致命的洪灾。常见的只是通过水路航运路径此处所遇见的风浪的风险,这种风险在所有的内河航运中都会存在。所以苏轼苏辙兄弟祷告的就是作为保护航运水神的僧伽。大致说来,先秦至北宋时期,黄河下游东北流注海。其河道迁徙,主要发生在今黄河以北地区,其间虽有南泛入淮过程,但对整个淮河水系尚未构成严重致命影响。但是,到了南宋高宗建炎二年的时候(1128),为了阻止金兵南下,东京留守杜充于河南李固渡西决黄河,造成了历史上第一次黄河南流夺泗入淮。从此打开了淮泗潘多拉洪水水患的惊悚魔盒,河水经鲁西南金乡县由泗入淮,洪水滔天,人为鱼虾,接着,金明昌五年(1194)河决阳武故堤,灌封丘而东,经汴水合泗水入淮,“一由北清河入海,一由南清河夺淮入海”,再一次形成黄河侵泗夺淮之变。金代末年,因人为决口,黄河更趋南徙。1232年,黄河全线夺睢合泗入淮;1234年,黄河干流又南下夺取涡水入淮水。而1234年,大家都知道,金国就在这一年亡的国。这样惊怖的世界末日现实,让人们从逻辑上顿时应该将灾情联想到水灾本地龟山下锁着的水妖,而面对如此惊骇的人间末日,人们自然期盼就驻锡在灾区泗州本地的、专治水患的佛家大神泗州大圣的就近施法镇妖救民。无论是泗淮在南宋的版图,还是在金国的版图,这些推理都是合理的。因为南宋与金国本来就是以淮水秦岭为界,泗州大圣与巫支祁所在的泗洲,时归南宋,时归金国,反复拉锯。所以,我们所说的南宋时间坐标,也只是一个层面的说法,因为在这个时空中,假设说铸造泗洲大圣降巫支祁的花钱的政权,也可能是金国。总之,在淮泗的特大水灾面前,佛家也有了充分的依据与需求,推动淮泗水神僧伽去制服淮泗水母传说的迅速登场与传播。而成为制巫支祁传说的新型时代读本。成为救灾救民的光辉大神,也是顺理成章的。时势不仅造了英雄,时势同样也在造着神灵。



比如南宋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浙江湖州飞英塔 僧伽三圣石雕,第一层北面与第二层南面,泗州大圣菩萨圣像,共两龛。第一层北面僧伽像无题记,浮雕三像,中为泗州大师,顶部烟气缭绕,右手持锡杖,左手托钵,从钵中放出朵朵云雾,两侧亦各有一弟子 (左侧弟子浮雕被后人凿去)均站立流云之上,其下水浪涛涛。见下图示:
































僧伽制水母的唐宋文本梳理已经告一段落,那么元明清时期,僧伽与巫支祁之间的对峙又有什么新的态势呢?请继续关注下期。
原创版权,违者必究
本文已经获得作者授权乐艺会发布
感谢玄商拍卖资料支持
欢迎转发
谢绝不经同意擅自拷贝图文至自己公微号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