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全面抗战打响后,清华、北大和南开三所高校为躲避战火,集体搬迁到长沙,组建了长沙临时大学。到了1938年,由于战局恶化,学校不得不再次迁移,最终在昆明落脚,并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这所大学一直坚持办学,直到抗日战争取得最终胜利。
在战乱时期,教育界普遍认为教育不能因战争而中断。作为西南联大的校务委员,胡适多次强调:“国家教育应着眼于长远发展,满足国家的基本需求,而非仅仅应对眼前的紧急情况。”1939年,国民政府制定了“战时应作平时看”的教育政策,并大力支持高等教育。尽管面临通货膨胀的挑战,教育部对西南联大的拨款持续增加。1938年拨款为26万元,到1940年增至138万元,1945年更是达到了2000多万元。

教育部在抗战期间对高校教职员工实施了多项补助政策。1943年5月至12月,西南联大的一批教授获得了不同金额的奖助金,其中闻一多、朱自清等12人各得600元,杨武之、郑天挺等获500元,另有15人领取200元。到了1944年11月,教育部又为经济困难的27名教授,包括朱自清、闻一多、冯友兰等,每人发放了1万元的研究补助费。此外,西南联大的员工及其家属也享受到了相应的经济支持。

在战争的特殊环境下,中国的高等教育不仅没有萎缩,反而实现了逆势增长。大学数量从108所增至145所,在校生规模翻了一番。当时的社会观察指出,抗战七年间,大后方的科研水平和学术成果,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都超越了此前三十年的总和。这一点,在西南联大的办学成就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联大师生在战时面临了极大的生活挑战。物资极度匮乏,日常所需的食品、衣物、燃料等基本生活用品都难以获取。由于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师生们的经济状况日益窘迫。许多学生不得不依靠微薄的助学金或兼职工作来维持生计,而教授们也常常需要兼职或变卖家产以补贴家用。住宿条件同样恶劣,校舍简陋,拥挤不堪,甚至有些学生只能借住在附近的民房或寺庙中。医疗资源短缺,疾病频发,但药品和医疗设备却难以获得。尽管如此,联大师生依然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教学与学习,展现了顽强的精神与对知识的执着追求。
尽管政府提供了支持,但西南联大的师生在战争时期的生活仍然非常艰难。在北平时期,教授们的月薪能达到几百大洋,足以购买一套四合院。然而,战争引发的通货膨胀使得这些收入急剧减少。联大经济系教授杨西孟在一篇题为《几年来昆明大学教授的薪金及薪金实值》的文章中,详细描述了教授们的生活困境。他指出,“他们是如何维持生计的?这需要说明他们是如何耗尽之前的积蓄,变卖衣物和书籍,靠写作和投稿来维持生活。由于营养不足,他们只能消耗自己的资本,而最终剩下的资本只有健康和生命。”
在联合国大学教授政治学的张奚若曾在课堂上向学生讲解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即“人是政治的动物”。他指出,动物只追求“mere life”(基本生存),而人类则追求“noble life”(高尚生活)。然而,张奚若随即话锋一转,提到当时大米价格已涨至每担五千元,并感叹道:“连基本生存都难以保障,还谈什么高尚生活?”

在西南联大,张奚若的言论被无数事例所印证。费正清访问昆明时,目睹了联大图书馆馆长严文郁的困境:他蜷缩在皮匠店阁楼的床上,衣衫不整,因贫困和疾病而愁眉不展,为三个孩子的温饱问题忧心忡忡。闻一多在教书之余,靠刻印补贴家用,他的收费标准是:石章1200元,牙章每字3000元,边款按字数计算,尺寸过大或过小则另行商议,费用需预付,七天后取件。朱自清在昆明穿着一件水牛皮色的毛毡,外形酷似蓑衣,李广田在路上偶遇他时,几乎没能认出这位昔日同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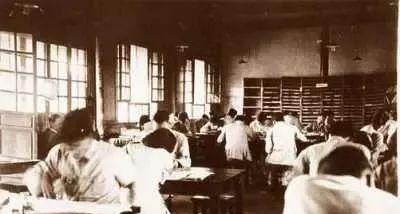
为了贴补家用,联大教授夫人们纷纷发挥所长。梅贻琦校长的妻子韩咏华回忆,当时联大的后勤主管赵世昌来自上海,教她和潘光旦的夫人制作"米粉碗糕"。她们将这种糕点命名为"定胜糕",由韩咏华提着篮子,步行四十五分钟到冠生园寄售。售卖时,她只说自己姓韩,不提梅姓。但尽管如此,梅校长夫人卖定胜糕的消息还是不胫而走,人尽皆知。
在联大读书时,一些学生的生活条件极为艰苦。比如,有的学生从1938年到1942年毕业期间,始终穿着同一件长袍,从未清洗,因为他们没有其他衣物可换。还有一位学生只有一套制服,那是他在完成一次任务后获得的奖励。即使是经济系的王民嘉,她的父亲是蒋介石的表兄、贵州省财政厅厅长,作为所谓的“高干子弟”,她依然和普通学生一样,住在简陋的草棚宿舍里,穿着朴素的蓝布袍,每天在食堂吃饭。
联大在学术表现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所大学以其卓越的教育质量和研究水平赢得了广泛认可。学生们在这里不仅获得了扎实的学术基础,还在各种学术竞赛中屡获佳绩。联大的教师团队由顶尖学者组成,他们不仅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还积极指导学生进行创新研究。此外,联大还与国内外知名高校和科研机构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资源和交流机会。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联大在学术上的显著进步,使其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的一颗璀璨明星。
在艰难的抗战时期,联大的师生们尽管生活困苦,但从未放弃学术追求。1942年春,雷海宗在云南大学首次公开了他独特的历史周期理论,得到了林同济的高度评价,称其为“历史学家的浪漫”。此外,联大在战争期间还成功设立了多个研究所,继续推动学术研究。
战争时期搞学术研究,总会碰上各种意外。有次空袭结束,社会学家李树青回到住处,发现屋里被小偷洗劫一空,连他写的20万字《关于中国土地问题的调查报告》手稿也不见了。金岳霖倒是早有准备,每次躲警报都带着他30年心血之作《认识论》的手稿。避难时,他就坐在书稿上保护它。可有一次,他还是把这宝贝忘在了避难的地方,等他回去找时,早就找不到了。金岳霖开玩笑说:“估计是被人拿去包花生米了。”
在1941年至1946年间,教育部连续开展了六次学术评奖,对获得一、二、三等奖的学者分别给予2000万至1亿元的奖金。西南联大的教师在这几次评选中表现突出,累计获奖超过30次,涵盖文理多个学科。例如,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周培源的《激流论》、吴大猷的《多元分子振动与结构》以及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均斩获一等奖。此外,王竹溪的《热学问题之研究》和李谟炽的《公路研究》等作品也获得了二等奖。值得注意的是,西南联大在理工科领域的成就尤为显著,这一点往往被当代读者所忽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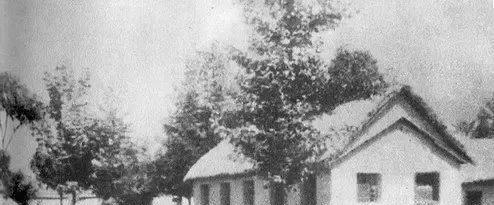
要拿到这些名师颁发的毕业证,可不是件容易事。1940年教育部立了新规矩,高校都得搞"毕业总考"这一套。学生除了最后一学期的课,还得把二三年级的主修课至少三门都考过才行。更麻烦的是,学农、工、商的学生还得拿出课外实习的证明,这才能顺利毕业。
在极其困难的办学环境中,联大师生们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所大学培养了超过8000名毕业生,其中包括两位荣获诺贝尔奖的杰出人才,174位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的科研精英,以及百余位在人文领域有重要建树的学者。这些成就充分展现了联大师生在艰苦条件下追求卓越的奋斗精神。
在专业领域里做到最易懂,在易懂的表述中保持最专业。
将历史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内容,同时让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广为人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