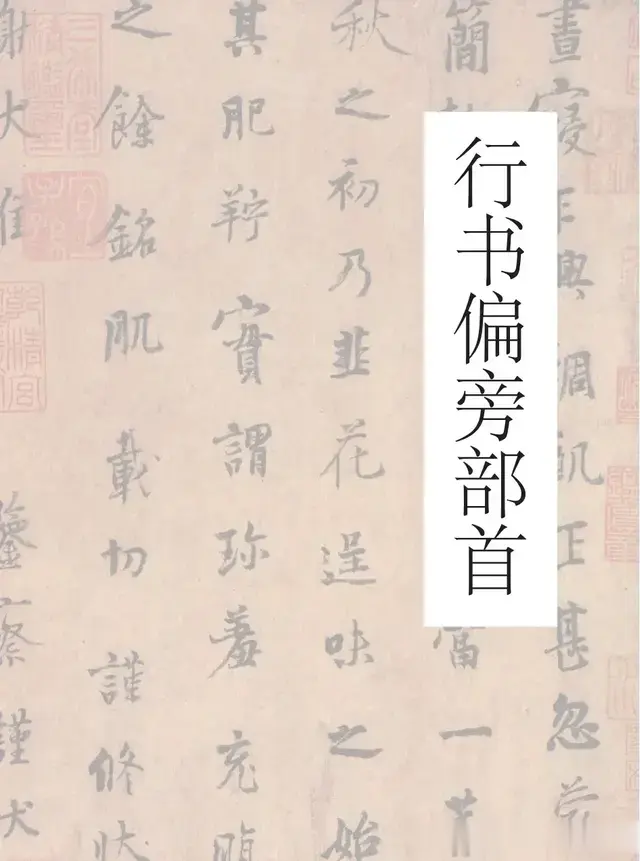文/王栩
(作品:《河边的错误》,余华著,收录于《河边的错误》,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12月)
河边,接连出现了三颗人头。奇特的作案现场让刑警队长马哲一开始便产生了一个认识,这个罪犯有些不正常。如果马哲相信跟着直觉一直走,总会走到正确的道路上,那么,他早就完成了对案件的侦破。可马哲并没将自己当初的认识转化成具体的行动,这让侦破工作从河边出现了第一颗人头时便偏离了正确的方向。
然而,这里提到的“正确方向”不过是一个人的直觉,它显然不能作为实践中的指导方针让众人信服。所以,如何完成案件的侦破,方法和步骤必然得遵循按部就班的一套。这一套属于经验的积累,在小李做案情介绍时有着教科书式的演示。
小李的介绍里,有第一个死者么四婆婆的个人历史,有么四婆婆的日常生活,还有小李对凶手行凶动机的主观认定。它们长篇大论,巨细琐碎,看似下足了工夫,却被马哲在犯罪现场附近拾到的一枚红色发夹击中了痛处。勘查了犯罪现场后,只有马哲回到河边做了进一步的复盘。这不是一种简单的对比,而是小说家在情节设置上对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社会生态环境的真实再现。它让纸上谈兵之人无所遁形,让真正的干才在这样的对比下尽显苍凉。
马哲无疑是个干才。但干才马哲也摆脱不了方法和步骤的支配。余华写出了规则的力量,它让马哲几乎是自动的在它的要求下走向农机厂,试图从这里找到蛛丝马迹。那是马哲又一次来到河边,在人与景物的互动中,规则牵引着马哲的视线落在了不远处一幢五层大楼上。马哲的调查仍然以凶手是正常人的方向展开,最初的直觉让他困惑,却也被他抛弃。
农机厂的集体宿舍楼离河边不远,也许会有人看见过行迹可疑之人。这是无法对其做出否定的定势思维,带着这种思维模式,马哲走向农机厂,也让小说的情节向传统侦破小说的模式继续推进。
按照传统侦破小说的情节推演,王宏出现在了办案民警们的视线里。可王宏表现的很愤怒。不仅仅是他,农机厂传达室的老头对马哲的问询表现出犹豫和搪塞。传达室老头害怕,却又对他人的正常形貌有着看客般的不解。当宿舍里的人都跑去看河边的人头时,王宏没去,这让传达室老头感到奇怪的同时,对办案民警掩饰不住内心恐惧的详细介绍了王宏的情况也就在情理之中。
王宏的愤怒,许亮的惶惶不可终日,丢失了红色发夹女人的恐惧,皆是社会生态环境的写照。他们都认为自己会被怀疑上,他们都去过河边。他们在接受问询时,对办案民警都有过抵触的情绪。而正是他们流露出来的或多或少的抵触,让案情呈现出复杂多变的特征。这种特征,正是传统侦破小说的重要元素。同时,也是一个人正常思维的重要落足点。
这就不难理解,小李劝许亮投案,以及小李向马哲建议,对许亮采取行动,为何不显得突兀。那不过是定势思维和规则要求小李作出的正常判断,在缺乏证据支持的情况下,以维护社会生态环境为纲目的必然结果。
小李的主张没有得到马哲的认可。疯子逐渐引起了马哲的注意,给案件的侦破引入了某种非正常思维。跟着当初的直觉走,案情并非那么复杂。马哲当初没有深入下去,后来又被他忽视了。待到马哲回过头来,“在心里已经认定罪犯是疯子了”,小说对社会生态中的荒诞性才有了一个可靠的展现。
这种展现没有落足于证据的寻找和凶犯的确认,在传统侦破小说里,它们是缺一不可的情节步骤,《河边的错误》里,它们是情节的铺垫,让位于对荒诞的社会生态环境的观照。
马哲决定抓捕疯子,这让小李显得犹豫不决。小李的犹豫不决表现出一种悄然的对抗,当定势思维受到了挑战,囿于规则之人必定对打破规则之人产生认识上的惰性。这种惰性的危害体现在小说里的具体情节上,即是第二颗人头在河边的出现。
疯子只关了一个星期就放出来了。法律对他无可奈何,公安局也拿他没办法。对社会生态环境的质问出自马哲,也不过是无关痛痒的一句“为什么没送他去精神病医院?”马哲的质问蜻蜓点水似的只触及到了社会生态的表皮,对更为本质的内容则由小说里的“那人”作了随意的应答。
“本来是准备送他去的,可后来……”那人犹豫了一下,又说,“后来就再没人提起了。”
马哲点点头,离开了河边。那人跟在后面,继续说:“谁会料到他还会杀人。大家都觉得他不太会……”他发现马哲已经不在听了,便停止不说。
这里的“那人”代表了社会生态中的群体意识,它有着坚实的生长土壤,在对肥沃的养分充足吸收下,会结出定势思维这一壮硕的果实。难以细究这样的果实是否苦果。两年后,因为镇上的民政资金不多,难以负担疯子的住院费用,加上精神病医院也不想卧床不起的疯子死在医院里,这让双方一拍即合的把疯子抬回了原来的住所。
疯子养好了身体,犯下了第三件凶案。河边的第三颗人头带给了马哲无尽的压力。法律对疯子失去了效力,马哲自己对疯子执行了结生命的私刑。当私刑执行完毕,马哲落入了社会生态的荒诞怪圈。马哲必须被追究刑责,正义的法律在维护正义者身上体现出正义理念的公平。但还有一个办法,可以合理地规避法律的追责。它由代表了权威的局长和代表了亲情的妻子共同策划,试图让马哲以精神病人的诊断结果逃脱刑罚。
权威和亲情,社会生态伸出的两只触手,它们缚住马哲的个人意志,马哲在这样的操控下,变成了一个被制造出来的“精神病人”。这个病人必须去住院,局长和妻子没有预料到会是这样的结果。这个结果无论怎么看,都体现出社会生态不可违逆的作用力。在它面前,马哲的笑并非开怀,反倒阴沉的可怕。他逃不过这荒诞的世事,合乎情理的被世事摧毁了他仅有的清醒。
2025.1.3
——文中图片均为网络配图,与正文内容无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