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广森,字巽轩,山东曲阜人。其于乾隆四十八年完成其代表作《春秋公羊经传通义》,自谓曰:“余生平所述,讵逮古人?《公羊》一编,差堪自信。”[1]但后世学者对其书的评价却存在着分化,赞誉者谓其“醇会贯通,使是非之旨不谬于圣人”[2],批评者谓其“不通《公羊》家法,其书违失传旨甚多”[3]。而最受攻讦的莫过于其“三科九旨”,实属孔广森在承继汉儒家法的基础上所做出的新裁,并非完全师心自是。至于其中的人情科,则体现了广森对于《春秋》改制以及辞例等方面的剖释。

孔广森(1751-1786),孔子六十九代孙
一、“三科九旨”新说孔广森是清代最早专门研究《公羊》的学者[4],著有《春秋公羊经传通义》十一卷。但后人对其公羊学研究却颇有微辞[5],认为他不遵《公羊》家法,尤其是其自立的“三科九旨”,更是饱受争议。就“三科九旨”而言,其作为《公羊》学的核心理论,最初见于董仲舒《春秋繁露》,后经何休总结而明确提出。何休作《文谥例》云:
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又云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二科六旨也;又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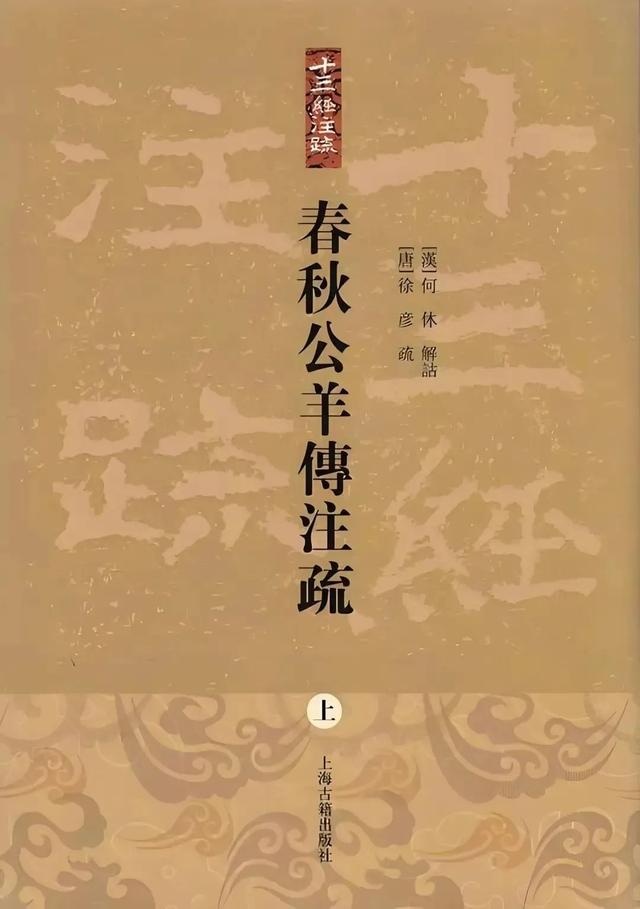
此处所言即公羊家之“三科九旨”,亦可名为“通三统”、“张三世”与“异外内”。然其中唯“张三世”与“异外内”之例,《公羊传》有明文。经由何休所总结条贯的“三科九旨”,对后世《公羊》学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清代学者刘逢禄极其推崇何休所定“三科九旨”在《春秋》学中的地位和意义,以为“无三科九旨,则无《公羊》,无《公羊》则无《春秋》”。[7]然而,孔广森却不遵何休旧传,而自立其“三科九旨”异说:
《春秋》之为书也,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不奉天道,王法不正;不合人情,王法不行。天道者,一曰时,二曰月,三曰日;王法者,一曰讥,二曰贬,三曰绝;人情者,一曰尊,二曰亲,三曰贤。此三科九旨既布,而壹裁以内外之异例 、远近之异辞,错综酌剂、相须成体。(《公羊通义》叙)
由此可知,孔广森以“天道、王法、人情”为三科;“时月日、讥贬绝、尊亲贤”为九旨。刘逢禄对孔广森这种标新立异的做法颇加批评,“乃其三科九旨不用汉儒之旧传,而别立时、月、日为天道科,讥、贬、绝为王法科,尊、亲、贤为人情科。如是,则《公羊》与《榖梁》奚异?奚大义之与有?”[8]刘逢禄显然认为孔氏新立“三科九旨”是对《公羊》家法的背离。但是,要准确评判孔广森此举是对《公羊》家法的承继还是背离?我们首先要厘清两个问题:其一,孔子之《春秋》究竟为何而作,孔广森是否准确意会?其二,《公羊》家法是否就等于何休所立的“三科九旨”?
广森于《春秋公羊经传通义》叙中述孔子作《春秋》之志,曰:
昔我夫子有帝王之德,无帝王之位,又不得为帝王之辅佐,乃思以其治天下之大法,损益六代礼乐文质之经制,发为文章,以垂后世,而见夫周纲解弛,鲁道陵迟,攻战相寻,彝伦或熄,以为虽有继周王者,犹不能以三皇之象刑、二帝之干羽议可坐而化也,必将因衰世之宜,定新国之典,宽于劝贤,而峻于治不肖,庶几风俗可渐更,仁义可渐明,政教可渐兴。乌乎讬之?讬之《春秋》。
孔广森这番解读,与董仲舒对《春秋》大旨的阐发颇为相似。董子云:
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天端,正王公之位,万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贤才,以待后圣。故引史记,理往事,正是非,见王公……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为见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 ……假其位号,以正人伦,因其成败,以明顺逆,故其所善。(《春秋繁露·俞序篇》)
董仲舒乃西汉《公羊》先师,其《春秋繁露》是解读《春秋》的代表著作,对于《春秋》中的微言大义多有阐发。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将《春秋》的核心主题以“科”、“旨”这样的名目进行条陈总结,也最早见于董仲舒《春秋繁露》:
《春秋》,大义之所本耶!六者之科,六者之旨之谓也。然后援天端,布流物,而贯通其理,则事变散其辞矣。(《正贯篇》)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文,天下之大,事变之博,无不有也,虽然,大略之要,有十指。十指者,事之所系也,王化之所由得流也。(《十指篇》)
董仲舒将《春秋》的要略表述为“六科十指”,包括天道王法以至人伦政教等各方面内容。[9]董仲舒对这一思路多有论述:
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汉书·董仲舒传》)
孔子明得失,见成败,疾时世之不仁,失王道之体,故缘人情,赦小过。(《俞序篇》)
可见,董仲舒阐发《春秋》要旨,强调取法天道,顺应人情而达于有治之世。而孔广森上承董仲舒,将三科的总纲设为天道、王法、人情,可以说是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杨济襄认为孔广森《公羊通义》在内容上大幅偏向董仲舒,可谓“私淑董氏”[10]。
另一方面,在何休之外,还有宋均的“三科九旨”。据徐彦《公羊疏》所载:
三科者,一曰张三世,二曰存三统,三曰异外内,是三科也。九旨者,一曰时,二曰月,三曰日,四曰王,五曰天王,六曰天子,七曰讥,八曰贬,九曰绝。时与日月,详略之旨也;王与天王天子,是录远近亲疏之旨也;讥与贬绝,则轻重之旨也。
显然,宋均所说的“三科九旨”不同于何休。徐彦认为,“何氏之意,以为三科九旨正是一物,若总言之,谓之三科,科者,段也;若析而言之,谓之九旨,旨者,意也。言三个科段之内,有此九种之意”。[11]可见,何休不别“三科”与“九旨”,以为“正是一物”,而宋均则于“九旨”别有他说。可以说,孔广森的新说颇有取于宋均。对此,曾亦先生指出,“宋氏说于例为长,是以后世治《公羊》例者,多取宋氏说,至有重九旨过于三科者。至清孔广森,则别创‘三科九旨’,即杂用宋氏说也”。[12]
从上所述可见,刘逢禄对孔氏“其三科九旨不用汉儒之旧传”的批评,其实并不能成立。盖孔氏所立“三科九旨”乃渊源有自,其中,“三科”盖取于董仲舒,而“九旨”则颇取于宋均,均属对汉师家法承继基础之上所作的新裁。《公羊》学在传承过程中有家法和师法之别,董仲舒和何休在解经方法上则有以义说经和以例注经的不同。所以,不能仅因孔广森未尽守何休所立“三科九旨”就指责其不通《公羊》家法。可以说,孔广森的新说体现了他对于《春秋》“上本天道,中用王法,下理人情”的卓见。尤其在其对人情科的具体论述中,一方面阐发了《春秋》折衷文质忠恕与尊亲贤齿的改制面向;另一方面也展示了《春秋》通过“讳”这种辞例,制《春秋》之义的立义面向。
二、人情科与《春秋》改制孔广森所设人情科,其内目为“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此说最早见于《公羊传》闵公元年:
【春秋经】冬,齐仲孙来。
【公羊传】齐仲孙者何?公子庆父也。公子庆父,则曷为谓之齐仲孙?系之齐也。曷为系之齐?外之也。曷为外之?《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
庆父弑闵公畏罪出奔齐国,至此时还鲁,《春秋》在此处称庆父为齐仲孙,表明他不该再次回到鲁国,鲁国也不当接受他。但事实上,对于庆父返鲁,闵公和季友作为尊亲贤者[13],却没有对此加以制止,而是接受弑君之贼庆父回国。对此,《春秋》非之,所以《春秋》为闵公和季子讳。而孔广森在此条传文下,将《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内涵揭橥更加明白,广森注曰:
为尊者讳,讳所屈也,内不言败、盟大夫不称公之类是也;为亲者讳,讳所痛也,弑而曰薨,奔而曰孙之类是也;为贤者讳,讳所过也。讳与讥之为用,一也,其事在讥之限,其人在尊、亲、贤者之科,然后从而讳之。(《公羊通义》闵元年)
在广森看来,《春秋》为尊、亲、贤所讳的内容各不相同。所谓为尊者讳,乃于尊者之屈处讳之;为亲者讳,则讳其伤痛处;至于贤者,一般有尊王攘夷、定国安邦的贤行,则讳其小过。广森还认为,从作用上来看,讳与讥是一样的,但因为所讥者在尊亲贤的范围,所以变讥为讳,以体现对这些人的优遇厚待。广森的这番解释,与其对世情人心的见解相关。
广森更直言“天下惟情出于一,故义者必因人之情而为之制”。此说见于《公羊通义》对于文公十五年“齐人来归子叔姬”一条的解释。《公羊传》曰:“其言来何?闵之也。此有罪,何闵尔?父母之于子,虽有罪,犹若其不欲服罪然。”子叔姬因淫佚有罪而被弃绝,《春秋》站在父母之心的角度,而讳其淫佚之罪。广森就此讨论了人情与恩义之间的关系,曰:
《春秋》有以义治,有以恩治。恩不本义,私恩也;义不本恩,则亦非公义也。虽有法度,不足以一天下,天下惟情出于一,故义者必因人之情而为之制。君臣以义合者也,然而曾子曰“孝子善事君”,子思子曰“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良以父子天性犹不致其爱,朋友等夷犹不得其睦,将于君乎何有?故《春秋》葬原仲无讥,而子叔姬之罪不尽其词焉,盖于季子见朋友之至,于子叔姬见兄弟之至。
案,广森以为,《春秋》之道恩义兼治,而非仅强调其中一端。而公义的实现也必须以顺循人情为前提。君臣之间固然强调义合,但其中的义也正是父子天性之爱和朋友等夷之睦的延伸。广森将父子兄弟天性之情作为现实人伦政治的起点,和儒家“孝悌为仁之本”的一贯主张是相合的。孟子讲良知、良能,同样是立足于“爱其亲,敬其亲”之情,而推广到君臣、夫妇、朋友等人伦和社会关系中。而公羊家言“亲亲”之情,常与《春秋》改制相关联,认为乃是由于周文疲敝,故《春秋》救之以质,尤重亲亲之情,广森于此详论曰:
《春秋》承衰周之敝,文胜而离,人知贵贵,莫知亲亲,开端首见郑段之祸,将大矫其失。非因人情所易亲者而先示之亲,则其教不易成。盖由父言之,凡我兄弟,岂有同异;由母言之,虽爱无差等,亦施由亲始。特拨乱之渐,不得已之志耳。故至所见之世,且録责小国杀公子,以广亲亲之义,明非专厚于同母也。(《公羊通义》隐公七年)
可见,在广森看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的记载中,有承衰救弊、拨乱反正之志,而最重要者,莫过于彰显“亲亲”之情,以救衰周“贵贵”之失,此《春秋》所以“损文益质”也。因此,《春秋》首先从一体之亲之父子、夫妇、昆弟处以示人情之端,而于君臣、朋友相交接之际以见其有根本,从而使古代社会呈现出由家庭以至社会、国家之间的先后同贯关系。
三、文讳而实讥孔广森认为,“讳与讥之为用,一也”,因此,其所谓“人情科”,既是本乎人情而讳言尊、亲、贤三者所犯之过错,同时,讥亦在其中。可见,讳并非就等于文过饰非,对此,孔广森说道:
“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恶如可讳,何以瘅恶闻之?有虞氏贵德,夏后氏贵爵,殷、周贵亲,《春秋》监四代之令模,建百王之通轨,尊尊亲亲而贤其贤,尊者有过,是不敢讥,亲者有过,是不可讥,贤者有过,是不忍讥,爰变其文而为之讳。讳,犹讥也,传以“讳与仇狩”为讥重是也,所谓“父子相隐,直在其中”,岂曲佞饰过之云乎?(《公羊通义叙》)
在此,广森明言“讳,犹讥也”。因此,广森以为,孔子作《春秋》以改制,乃是损益虞夏殷周四代之制,以“著尊亲之道,垂贤齿之教”。而对于尊、亲、贤三者之过,若是径直讥刺,自有不敢、不可、不忍之情,故表面上虽为讳辞,其中仍含有讥的意味。
此外,《公羊传》中又有“壹讥”的说法:
【春秋经】庄公四年,冬,公及齐人狩于郜。
【公羊传】公曷为与微者狩?齐侯也。齐侯则其称人何?讳与仇狩也。前此者有事矣,后此者有事矣,则曷为独于此焉讥?于仇者将壹讥而已,故择其重者而讥焉,莫重乎其与仇狩也。于仇者则曷为将壹讥而已?仇者无时,焉可与通;通则为大讥,不可胜讥,故将壹讥而已,其余从同。
案,《春秋》所载“公及齐人狩于郜”,实指鲁庄公与齐侯一同狩猎之事。根据“父母之仇不共戴天”的伦理要求和狩猎的性质来判断,因为齐侯于庄公有杀君父之仇,故一同狩猎实属大恶。《公羊传》对此事从讳与讥两个层面发明经义:首先从讳的层面来看,《春秋》“内大恶讳”,故此处《春秋》称齐侯为“人”,从而达到讳“与仇狩”的大恶。其次,从讥的层面来看,虽然鲁、齐两国前后多有交接往来,但与杀父仇人一同狩猎这件事性质最为严重,故《春秋》仅在此处“壹讥”而已。
此外,广森认为《春秋》此处的书法可称为“等讳”。其言曰:
等讳,不没公言齐侯,而必贬齐侯称人者,没公则但有讳义,人齐侯兼以恶齐也。诸侯以国为体,虽据哀録,庄犹有仇襄公之心焉。仇之,则其言贤之何也?贤其可贤,贬其可贬,以直报怨,《春秋》以之。(《公羊通义》庄公四年)
盖广森以为,《春秋》在此处如果将公隐没不书,直接写作“及齐侯狩”,也能起到讳内恶的目的。但是,如果不没公,且将齐侯贬称为“齐人”,则可以同时达到内讳和恶齐的结果。在广森看来,《春秋》中的讳辞往往是“文讳而实讥”,故须在文与意之隐微处察其“微辞”。
又,哀公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阳归。《公羊传》云:“曹伯阳何以名?绝之。曷为绝之?灭也。曷为不言其灭?讳同姓之灭也。何讳乎同姓之灭?力能救之而不救也。”《通义》云曰:
灭邢不讳,灭曹讳者,所见之世为内耻尤深也。此同事而异辞,所以各见其义,彼主责卫灭同姓,此主责鲁不救同姓之灭,直书宋灭则责内意无所讬,变灭言入,乃得起其微辞,故曰:讳与讥之为用一也。
案,《春秋》深恶灭人之国的行为,但此处却不是将批评的重点放在宋灭曹上[14],故“变灭言入”。《春秋》表面上为宋国讳灭人之国的恶行,实则是责鲁国不救同姓之灭。在广森看来,此处讳即是讥。
此外,在宋公和陈侯的卒葬之事上,广森对于讳与讥的关系也有一番详论。据《公羊传》隐公三年载:
天子记崩不记葬,必其时也。诸侯记卒记葬,有天子存,不得必其时也。
这是因为天子至尊无敌,其丧葬不会受到其他人的影响,故下葬一定能按时完成。但诸侯则不同,因为屈尊于天子,故若同时遭遇天子、王后之丧,则其下葬不免会受到影响。综合来看,《春秋》所言卒葬之例,天子记奔不记葬,诸侯则记卒记葬,其中,大国诸侯卒日葬月,小国诸侯则卒月葬时。但《春秋》于此亦有变例者,见于以下几条:
僖公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说卒。
僖公二十三年,夏,五月庚寅,宋公慈父卒。
僖公二十八年,夏,六月,陈侯款卒。
文公十三年,夏,五月壬午,陈侯朔卒。
以上四位诸侯的卒葬,《春秋》均记卒不记葬。《公羊传》认为,宋公御说和宋公慈父不记葬,乃为宋襄公讳;而陈侯款和陈侯朔不记葬的原因,《公羊传》没有明说,何休认为是为晋文公讳。《春秋》为宋襄公讳,是因为宋襄公在父丧期间自行背殡出会,有不子之恶,不过,此后宋襄公有征齐、忧中国、尊周室之功,且足以覆背殡出会之恶,所以《春秋》为宋襄公讳背殡出会之恶。至于晋文公之恶,乃“行霸不务教人以孝而强会其孤”,但因同样有尊周室之功,所以《春秋》也为其讳恶。
《春秋》所记载的这几件事,牵涉到人子为父守丧期间的相关礼制。据《白虎通·丧服》记载:
诸侯朝而有私丧,得还何?凶服不入公门,君不呼之义也。凶服不敢入公门者,明尊朝廷,吉凶不相干。[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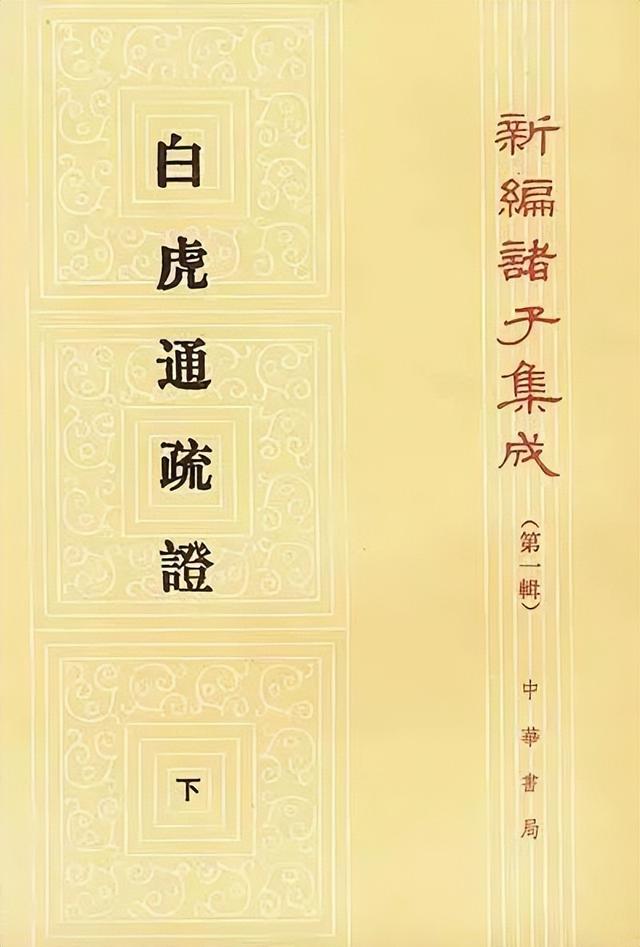
又据《公羊传》宣公元年云:
古者臣有大丧,则君三年不呼其门。已练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
按儒家礼制的规定,君王不能使居父母之丧的大臣服事。据此,宋襄公参加葵丘之盟,虽然是自行背殡出会,但齐桓公作为葵丘之盟的盟主,不应该接受居父母之丧的宋襄公与会。所以,孔广森认为:“此亦兼为齐桓讳,与陈侯款同意。”[16]刘逢禄在此事上也从孔广森之说,曰:“《春秋》托齐桓为二伯,宋有大丧而强会其孤,故不书葬,兼为齐桓讳,与陈侯款同例。”[17]而《春秋》为了讳宋襄公和晋文公之恶,所以一并对宋公慈父和陈侯朔不记葬,好像宋国和陈国的国君去世时一贯是不记葬的。这种书法,何休称为“盈讳”。
但是,仅从伯者有功的角度出发强调功恶相覆,以功掩过,又似乎使得讳的书法成为了一种褒奖,似于实际情况有失。孔广森在此颇有卓识,其论曰:
桓、文,《春秋》所善也。若葵丘之致宋子,温之致陈子,乃其未尽善者也。令宋桓、陈缪自如常文书葬,则责伯者之意不见,故为之讳其葬,使若既葬而后会其子者为愈,文讳而实讥也。款本篡立,不当葬,今为文公讳去葬,篡罪尚未显,故复略其卒日以见义。(《公羊通义》僖公二十八年)
可见,广森以为齐桓、晋文虽为《春秋》所褒善之贤君,但是与人孤会盟到底还是有未尽善之处,所以《春秋》在记载这件事的时候,记卒不记葬,仿佛旧君下葬以后新君才去参加会盟(主动或是被动),《春秋》用了比照常书葬更甚的讳笔,所以表面上是为宋襄、晋文讳,实际上是讥。对此,陈立也认为:“《春秋》为宋襄、晋文讳,讳之,正以刺之也。”[18]这正是孔广森反复提到的,《春秋》中虽然对尊亲贤者之过不显白直书而代之以讳言,但讳中也仍有讥,甚至所讳越深,所讥就越重。
 四、讳文不没实
四、讳文不没实《春秋》记人记事多有避讳,盖如董仲舒所言“《春秋》之书事,时诡其实,以有避也;其书人,时易其名,以有讳也。”[19]所以为尊、亲、贤三者诡实易名以讳,主要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缘人之情,二是功过相除。然而,在孔广森看来,《春秋》中“诡易委曲”的讳笔,实际上“讳文而存实”、“假讳而立义”。孔广森在《公羊通义》中对此义多有发明。

在《春秋》中,除了将取邑视为恶行以外,更将灭人之国、覆人之社视为大恶,因此,如果鲁国犯灭国之大恶,出于内大恶讳的目的,在书法上则言取或入。例如,隐公二年,无骇帅师入极。《公羊传》云:
无骇者何?展无骇也。何以不氏?贬。曷为贬?疾始灭也。始灭昉于此乎?前此矣。前此则曷为始乎此?托始焉尔。曷为托始焉尔?《春秋》之始也。此灭也,其言入何?内大恶,讳也。
《公羊传》认为,《春秋》就此事的记载中,同时包含了贬和讳。展无骇去氏为贬,灭而言“入”为讳。孔广森进一步从《春秋》对灭人之国的批评中对无骇帅师入极作出解释,曰
侵、伐、围、入都无讳文,独灭讳恶者,诸侯有得专征伐之道,不得专灭国,覆人之社,绝人之世。令诚有外内乱、鸟兽行者,当以九伐之法正之,非可攘土地以自广。汉李固曰:“《春秋》褒仪父以开义路,贬无骇以闭利门。”君子恶兵以利动,故取邑为小恶,灭国为大恶也。赵匡难此传云“灭而言入,实入者将如何书之?”广森以为,实入将书“展无骇率师”矣。内讳弑言薨,固与实薨者同辞,则讳灭言入,则与实入者同辞,亦何不可?况贬去氏者,正起其非实入乎?(《公羊通义》隐公二年)
此处广森特别强调,与侵、伐、围、入相比,灭人之国、覆人之社的行为一般带有贪求别国土地和财力的目的,所以《春秋》将出兵灭国的行为视作大恶,或讳或贬。广森进而认为,此条所载展无骇帅师灭极的事实,若只是讳灭言入,将与实入无法区分开来,故《春秋》又将展无骇贬去氏而称“无骇”,表明这不是真入,而实为灭极。可见,变灭为入的文辞体现出了内讳之意,而同时展无骇去氏却将贬责之意存留下来。从这条可以看出,《春秋》对于取邑、灭国此类贪利行为的憎恶。
不过,《春秋》中所褒进成善者也不免有取邑灭国之恶,而于此等大恶的记载,就要具体通过功过相除的办法来权衡。齐桓公因有尊王攘夷、存亡继绝的功绩,在《春秋》中被褒为贤君,却屡有取邑灭国之恶,孔广森认为,《春秋》对齐桓公取邑灭国之恶的记载是“文微而实不没”。齐桓公取邑之事,见于庄公三十年“齐人降鄣”一条。《公羊传》云:
鄣者何?纪之遗邑也。降之者何?取之也。取之则曷为不言取之?为桓公讳也。外取邑不书,此何以书?尽也。
何休认为,按照《春秋》功过相除的原则,齐桓公的霸功足可以除去此处的取邑之恶,所以为桓公讳“取”言“降”。对此,广森注曰:
纪之亡,二十余年矣,而鄣犹孤存,盖其守邑大夫抗节未降,若安陵不入于秦,莒、即墨不下于燕者也。桓公必将胁之以威,屈其志而穷其力,以取其土地,故不曰“鄣降于齐”,而曰“齐人降鄣”,闵鄣而甚桓,见乎辞矣。是所谓讳其文,不没其实者也。齐称人者,贬也。虽不言取而斥齐人,是时未有存亡继绝之功,与之未醇,故讳不若“灭项”之深也。(《公羊通义》庄公三十年)
孔广森进一步从征实和书法的角度对“齐人降鄣”作出解释。首先,孔广森指出,鄣乃是纪国灭亡之后残存下来的遗邑,而齐桓公为了获取鄣邑的土地将遗留的民众胁迫殆尽。其次,《春秋》对齐桓公这种图利而取邑的行为持责备的态度,在书法中有两处体现:一是《春秋》将齐人取鄣讳言为“降鄣”,体现了齐国强取的意味,而非鄣邑自觉臣服而归,所以降鄣与鄣降相比,明显带有谴责齐国而怜悯鄣邑的意味;二是《春秋》虽为齐桓公讳恶,此时齐桓公的功绩尚未卓著,所以《春秋》对他的赞与尚有保留,并没有将他所犯之恶完全讳去。《春秋》中称“人”常为贬辞,而此处称“齐人”,正是贬意的体现。总之,在孔广森看来,此处虽有讳笔,但是并没有将所犯恶行的事实完全掩盖,正如其言“讳其文,不没其实也”。
此后,齐桓公又有灭项之恶。《春秋》对此事的记载,为“僖公十七年,夏,灭项。”《公羊传》云:
孰灭之?齐灭之。曷为不言齐灭之?为桓公讳也。《春秋》为贤者讳。此灭人之国,何贤尔?君子之恶恶也疾始,善善也乐终。桓公尝有继绝,存亡之功,故君子为之讳也。
《公羊传》在此处说明了两点。其一,齐国灭项发生在齐桓公在位的晚期,此前齐桓公已有诸多功绩,《春秋》本“恶恶始,乐善终”的原则,为齐桓公讳灭项之恶,使得齐桓公为善而终。其二《公羊传》还明确指出桓公之前存亡继绝的功绩正好可以覆盖此处的灭项之恶[20]。孔广森在此进一步引萧楚之言曰:
襄公十年,诸侯会吴于柤,“夏,五月,甲午,遂灭偪阳”,今“灭项”不言遂,知其讳文也。为贤者讳,非以其贤而讳之,将以成其义,全其功,以垂训后世,此拨乱之志也。齐桓之功著矣,齐桓之事终矣,而又昧此一举,故不斥著其恶,而为之有逊避之文者,以其有卫中国之功,且示善善乐其终也。呜呼!非实为桓公讳也,欲后人睹圣人于此有逊避之辞,以见不善焉,而为善者勉之令终也。然文微而实不没也。(《公羊通义》僖公十七年)
这段话在善善乐终和功过相除原则之外,还讲出了讳避之外的另一层深意:从文辞来看,《春秋》将齐国灭项仅书为灭项,为齐桓公讳恶;但实际上正是通过这层逊避之辞我们才看出齐国所犯之恶行,讳辞在讳恶的同时也起到了劝善规过的作用。所谓“因其所讳,达之于所不讳”。
又,庄公四年,纪侯大去其国。《公羊传》认为,齐襄公虽有种种恶行,非贤德之君,但是在为先祖复九世之仇这件事上,以襄公为贤,故而将“齐灭纪”的恶行,用讳笔书为“纪侯大去其国”。就此事来看,《春秋》对襄公的复仇之心是予以肯定的,但对他复仇的具体做法却颇有非议,广森注云:
襄公他事不足贤,独复仇之心有取焉,故为之讳恶,以成其善。俗儒疑于襄公利纪,不得为贤,此未明讳之所设也。假令襄公不贪土地,醇乎令德,更复何讳?唯贤其复仇,而又病其利纪,是以存其可法,没其不可法,而假以为后世法耳。
可见,学者对“襄公复仇”之惑,大抵在于齐襄公复先祖之仇与灭人之国之间的价值冲突上:一方面,复仇之心值得肯定;另一方面,贪求纪国土地的行为又理应憎恶,二者统一在齐襄公灭纪为先祖复仇一事上。孔广森以为,俗儒有疑于此乃是“未明讳之所设”,其所言《春秋》“假讳而立义”,意为《春秋》在讳恶的同时,也在立义树则。就齐襄灭纪来说,《春秋》用讳文写作“纪侯大去其国”,而非照实写作“齐灭纪”。其深意并不在于为齐襄公讳恶,而在于张大《春秋》所褒扬的“复仇”之义。段熙仲有言:“复仇之义深入人心,则贼必讨矣。知贼之必讨无所逃也,则乱臣贼子惧矣。”[21]段氏所言,颇合《春秋》大义在诛讨乱贼以戒后世之说。[22]故广森以为,《春秋》对于此事的记载并无不可调和之处,即于齐襄公复仇之心自当贤之,而于其贪利之心也当病之。后人当于《春秋》讳笔之处,识得《春秋》所要昭示的义旨以及对治世之良好价值的向往。
 结语
结语孔广森认为“《春秋》重义不重事”,故在解经方法上,乃会通三传以直趋经义。广森本于《春秋》“上本天道,中用王法,下理人情”,而立“天道、王法、人情”为三科,“时月日、讥贬绝、尊亲贤”为九旨。孔氏此说虽有别于何休,但亦颇取于董仲舒和宋均。盖其三科侧重义旨,而九旨则侧重辞例,并且每组科旨之间,有相互对应的关系,可谓“以义驭例”[23]。关于这一点,无论在何休还是宋均那里,都是未曾突出的。并且,将“人情”与“尊亲贤”列入“三科九旨”之内,也是孔广森的新裁。今寻绎《公羊通义》,我们发现,广森此论并未偏离《春秋》之大旨。可以说,广森于“人情科”下,昭示了《春秋》监虞、夏、殷、周四代而为后世制法之微言。盖孔子作《春秋》而改制,损益四代,故而尊尊、亲亲而贤其贤。同时,广森认为《春秋》虽然“为尊、亲、贤者讳”,但在讳的文辞之下,并没有完全饰非掩过,而是在事例的比附中保留实情,并且做出合理的批驳。更重要的是,在隐微的讳辞背后,又从更深的层面树立正向价值以求补弊起废。
本文原刊《复旦政治哲学评论》第11辑,此为原稿,刊发时有编辑修改,引文请以纸质版或知网下载的PDF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