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阅读此文前,诚邀您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与分享,又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引言现如今,不论是在农村还是城市,结婚要彩礼已经是一个普遍现象。然而这种现象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普遍存在,且婚礼之奢华比之现代有过之而无不及。

尽管在历史上,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大混乱的时代,底层社会民不聊生,但这并不影响上层社会的奢靡,“财婚”就是这一时期所盛行的一种婚礼习俗。
而引发这种习俗的原因以及所造成的社会影响,也与魏晋南北朝所处的混乱时代息息相关。
及时行乐助长财婚风气魏晋南北朝时期,世事多变的复杂处境致使世人消极避世,许多名人志士选择隐居山林,眼不见为净,如陶渊明。

然而并不是所有窥探到世事无常的人都能避世不出,他们无法改变现状,于是选择了及时行乐。
这与隐居山林不同,及时行乐需要雄厚的经济实力作为支撑,所以门阀士族是这一部分人的代表,也是助长财婚风气的领头羊。
门阀士族的婚姻,讲究门当户对的同时,还要彰显自己的地位,所以往往排场极大。

如南齐武帝永明七年(234年)四月诏书,描绘了南朝行同牢之礼时美食毕设、合卺则金银玉器盈前的奢华景象:
“乃闻同牢之费,华泰尤甚。膳羞方丈,有过王侯。”
可见当时的门阀士族婚礼之奢华,直接引起了皇帝的注意。
除了婚礼现场的奢华布置,魏晋南北朝在聘礼一事上格外重视,女方父母往往漫天要价,并把这笔聘娶资金当做家庭的储备用金。

如《宋书·庾登之传附弟炳之传》 记载:庾氏本身钱财不薄,家门地位皆属上层,而庾炳之在将女儿嫁给刘道锡时,却公然索要
“嫁女具及祠器,乃当数百万”
可见时人嫁女所获钱财,堪称“卖女”。且这种现象通过传播,逐渐蔓延到民间。
南朝以后,许多士族没落,族中子弟为了娶亲,将目光放到了平民阶层,原本以为能轻易娶妻,却还是免不了要准备丰厚的聘礼。
可想而知,为了筹备这些聘礼,即使是颇有经济实力的人家,也是沉重的负担,甚至因此倾家荡产。

如《三国志·蜀书·董和传》记载:
“蜀土富实,时俗奢侈,货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倾家竭产。”
可见情况之严重。
男娶妻如此,女陪嫁亦然。如《南齐书·王思远传》记载:宋建平王刘景素之女因其父被杀受诛连而废为庶人,王思远代为抚养,
“年长,为备笄总,访求素对,倾家送遣。”
为了嫁养女,王思远几乎倾家荡产给其准备丰厚的嫁妆,可见陪嫁方亦受到了财婚风气的波及。

这不免让人联想到现代的娶妻嫁女。普通人家为了筹得高昂的彩礼,几乎举全家之力,有的甚至为了买房买车而贷款结婚。
魏晋南北朝的借贷还没有发展出现代所谓的“婚贷”,要想顺利的完成终身大事,非财力支撑不可。
这不免让人觉得本末倒置。为了躲避现实的混乱,开始及时行乐,沉迷于金钱堆砌的快乐里,然而要想娶妻,往后用来行乐的本金至少要减少一半,还有何快乐可言?
当然,这并不代表那个时期的婚姻是不必要的,而是抨击以此而引发的“财婚”风气负面影响。而由此风气所引发的问题,可谓当世婚俗之写照。

婚姻的陪嫁和聘礼自古以来就有,究其起源,与我国传统的小农经济脱不开关系。农业经济引起的财富分配不均,是每个落后家庭都要面对的问题。
因此,为了防止家庭财物不足,父母在嫁女时就会有意的向男方索取财物以备不时之需。同时,这也是女方父母为了让女儿在男方家庭中拥有一定的经济地位而不至于受欺负。
而男方索要陪嫁,也是其父母为了儿子即将建立的家庭能拥有一个好的经济条件而考虑的。所以,男女双方的父母,为了这笔钱四处奔忙。

这种由财婚引起的家庭负担重的情况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尤其多,最终导致的就是小康之家负重累累,贫困之家难以成婚。如《吴书·吕范传》记载:吴国的吕范
“少为县吏,有容观姿貌。”
然而由于社会地位低下,家境贫穷,成为他婚配的障碍,
“邑人刘氏,家富女美,范求之。女母嫌,欲勿与。”
可见,在美男横行的魏晋南北朝,没有经济实力,即使你长得再有姿容,也难以娶妻。

除了贫富之家难以嫁娶外,有财之家为了积攒婚娶资金,为官之人不惜贪污受贿。如《萧惠开传》记载:萧惠开妹当嫁桂阳王刘休范,其女亦当配宋孝武帝之子,
“发遣之资,应须二千万”
为筹得这笔嫁资,刘宋朝廷乃以萧惠开为豫章内史,“听其肆意聚纳,由是在郡著贪暴之声”。
可以说,为了筹备这笔钱,许多为官清廉的人走上弯路,致使清廉名声不在。

最严重的问题,则是由财婚引发的杀女婴现象。在魏晋南北朝的人眼里,养个女儿吃力不讨好,不能养老送终不说,在她嫁人时还要备上诸多陪嫁,许多生女之家因此不堪重负。
久而久之,为了免除这笔嫁妆,魏晋人们不再想要女儿,一旦发现生了女婴,就会当场杀死,实在不忍心的则会寻个时机丢弃在野外。这显然是由财婚而引起的社会悲剧。
女性的减少,更加使得成年男性难以婚配,周而复始,必将引起社会男女比例失调。

当男女比例失调到一定程度后,又会导致人口下降,这会直接危及到封建社会统治者们的权威。因为这意味着他们无法从增加税收方面充盈国库。
所以,为了解决由财婚引起的一系列问题,封建统治者们下令禁止婚嫁奢华,划定婚配年龄。如如北周武帝于建德二年(573年)下诏:
“顷者婚嫁竞为奢靡,牢羞之费,罄竭资财,甚乖典训之理。有司宜加宣勒,使咸遵礼制。”
次年又下诏:
“自今以后,男年十五,女年十三已上,爰及鳏寡,所在军民,以时嫁娶,务从节俭,勿为财币稽留。”

但是这些诏令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相反还引发了“早婚”问题。究其原因有二。
一是魏晋南北朝时局混乱,封建政府颁布的法令朝令夕改,自相矛盾,所起到的约束力极其微弱。
二是魏晋南北朝各代政府赋役繁重,已婚者和未婚者的税额是极为不平等的。
据《隋书·食货志》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成家立室之人,其赋役负担远远超过单丁家庭,普通百姓难以承担,更加不敢娶妻生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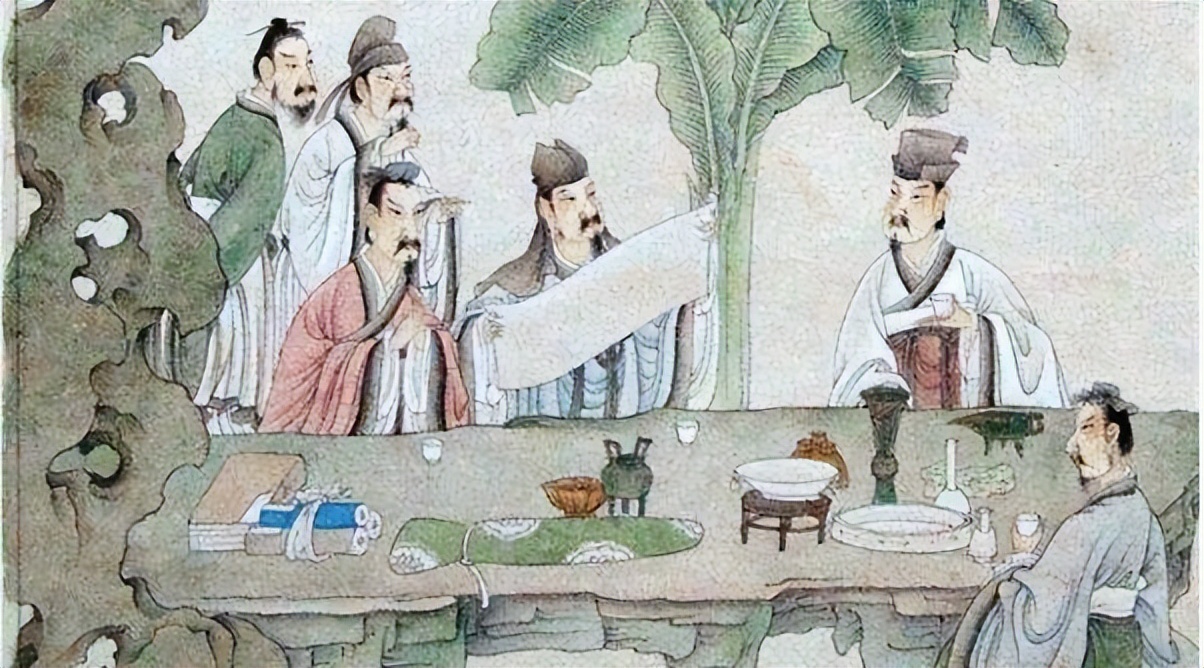
封建统治者为了让人口快速增殖,一再将婚配年龄下调,以至于女子十三岁就得承担生儿育女、家庭赋税等问题。
由此可见,魏晋南北朝的财婚风气,直接影响着社会的各个层面,由个体的失婚早婚,到家庭的负重累累,再到封建国家的男女比例失调、人口增殖缓慢。
而这些问题都能从现代社会里窥探到一二,只不过对个体的影响,分成了两个极端。
农村贫困地区早婚仍在,然而城市里却逐渐趋向了晚婚晚育,甚至不婚不育。究其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定有财婚的影响。

显然,魏晋南北朝的财婚影响之深刻,直到今日也依然存在。这是无疑是传统婚俗的遗留。
不过任何文化习俗,都有积极或消极的影响,我们应当辩证看待。
财婚所引发的问题固然值得后人深思,但若放在魏晋南北朝那个极其混乱的时代,它又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其一,对婚姻制度产生了影响,并冲击门阀士族的择婚原则。
魏晋时,门阀士族阶层为了保护自己特殊的政治和经济权益,把婚姻的范围局限在有限的几个门阀家族之中,奉行门当户对的择婚原则,以维持与庶人分隔的社会结构。

这不仅对于整个社会进步不利,对于门阀阶层人口素质的优化也是不利的。于是,在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不少门阀家族日渐没落,生活窘困。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士庶通婚的情况出现了。前文已述这是门阀士族不得不降低标准的无奈举措,虽然因为财婚风气的蔓延,依然要准备嫁娶资金,但相比同一阶层,庶人所要的明显更少。
这对于推进阶级融合,甚至民族融合,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其二,财婚风气的盛行,也为人们营造热闹欢乐的婚姻氛围,提供了经济基础。由于财婚风气所导致的用费铺张,初步奠定了求欢乐求热闹的婚俗基调。这一基调,也是现代婚俗里所追求的欢乐、热闹。
另外,婚礼上音乐大作、宾客盈门,也符合中华民族追求喜庆的情感需要,切合婚礼喜庆的氛围,故而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很强的生命力。如《周书·崔猷传》记载:
“时婚姻礼废,嫁娶之辰,多举音乐”。
说明只要是投合人民情感需要的习俗,就有着十分旺盛的生命力。以乐贺婚,自此成为中华民族一种世代相传的婚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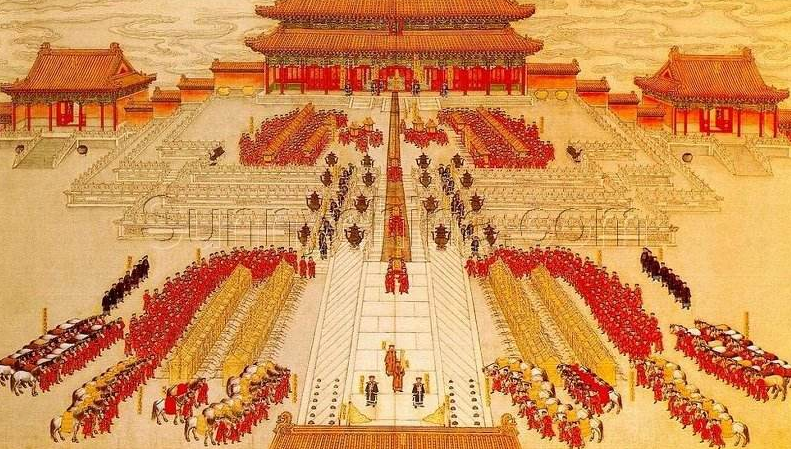
由此可见,在经济实力雄厚的基础上,财婚所引发的的负面问题可以忽略不计,甚至可以达到宾主尽欢的目的。
结语魏晋南北朝的财婚风气,由门阀士族走向平民阶层,直至蔓延至今。无论是聘礼还是陪嫁,都对当时的家庭和个体乃至国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同时,由于财婚风气的盛行,也使得这一时期的人们通过金钱的魔力,努力忘记所处乱世,从而营造一种愉快的情绪氛围。

在婚姻大事上体味到人生的欢乐,冲击了中国传统礼法的庄重和压抑,使得婚姻基调趋向铺张和欢乐,并对此后的婚姻礼俗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对于后世而言,从中吸取教训,并提取出积极乐观的一面继承发扬,才是当世正确看待财婚问题的应对方式。
参考文献:
《周书·崔猷传》
《萧惠开传》
《吴书·吕范传》
《宋书·庾登之传附弟炳之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