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典是这样一种著作,
它不断引生批判它的种种论说的云朵,
而又不停地将其摆脱,
它永远不会完结它所要叙说的东西。
——伊塔洛·卡尔维诺
全球票房仍在攀升的《无名》,是国产文艺片票房天花板。这业绩的背景是严肃电影遭遇浅阅读时代,业界与大众口碑撕裂,票房成为席卷一切的暗流,而文艺片因不符合浅表娱乐心理,被嗜血的粗暴评价预测的小众性,提前扼杀于排片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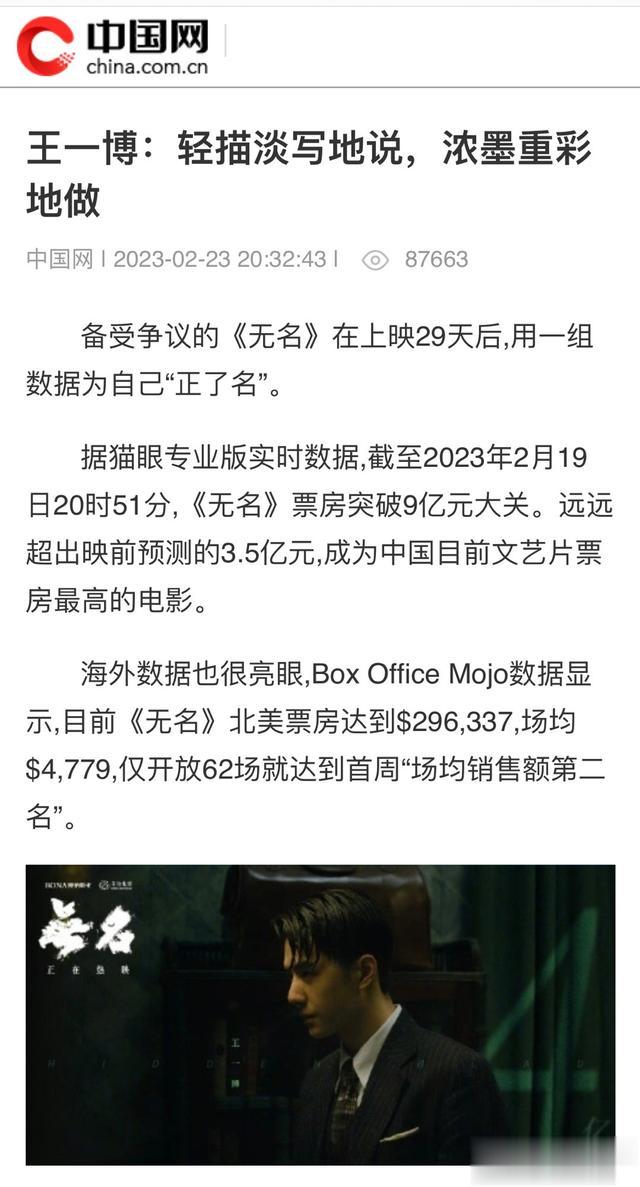
 电影的真正的使命︱使文化成为可见的东西
电影的真正的使命︱使文化成为可见的东西宏大视野里的波诡云谲,血色,多少与贺岁档的喜庆违和。大年初一上映,本身就是种行为艺术……就很程耳,与超级商业片的自嘲如出一辙。作为一部谍战文艺片,《无名》实现了中国电影创新表达的突破,其异质性在国产片中独树一帜。
太多电影的戏剧张力完全依托场景与特效,一旦走出影院便荡然无存。而《无名》营造的是巨大的心理磁场,即使脱离视听环境依旧令人意兴犹酣。《无名》的腔调门槛,不是对观众的某种轻慢,恰恰是对观众、对历史、对电影的极致尊重。
文艺片是相对于商业片概念的电影类型,它注重艺术表现和文化内涵,试图追求更高度的审美价值和文化意义。其制作也与商业片有别:商业片追求商业利益或大众娱乐性,以电影票房为主要目标,而文艺片则注重电影艺术性和文化内涵。
僭越规范,冒犯常识,艺术电影是电影的拓荒者,多有落败却拓展了电影的疆域。世界影史上有两部文艺经典《肖申克的救赎》《大话西游》,上映之初票房惨败,通过后期影像传播积累大量铁杆粉丝,经历岁月沉淀才成为不可磨灭的经典。




两作价值逆袭的内核依然是金子总会发光。前者对人性和社会制度探讨铸就现代电影里程碑,后者后现代解构主义意识流在颠覆传统的时代赢得共鸣。
电影作为文化载体,是时代思想最直观通透的价值体现。尽管大多数传世经典并非思想家所处时代的真实认知,而是经历岁月沉淀才得以被大众接纳。经典因此而随历史进程不断增值,这就是经典的力量,也是我们对经典怀有敬意的缘由。
而程耳早在《罗曼蒂克消亡史》便借台词明心迹,“电影是拍给下个世纪观众看的”。瞧,突破时代语境的艺术家,时代对他们的回馈多是滞后或错位的,尽管这错位本身恰恰是先锋的内涵。没错,文艺片向来在业界是票房惨烈的弱势群体。
而与票房惨烈情势对比的,是文艺片在电影艺术奖项上的野心与强势。这也是最近《无名》横扫第36届金鸡奖,8项重磅提名再引舆论争议的原因。

影评领域大势出圈,实则票房惨淡的《燃冬》《不虚此行》才引发全网热议不久,《河边的错误》同样在拉高观众期待值后遭遇口碑分化。回顾这些年的文艺片宣发,又何止 “卖惨文学”、“诈骗文学”、“歹毒文学”、“撕X文学”和“发疯文学”!
《无名》的存在,的确是国产文艺片的孤例。9.31亿票房,不仅是程耳导演生涯最卖座电影,甚至是其过往作品全部票房总和的数倍!过于惊艳以至《无名》从来都被坊间野生表格,以“去掉一个最高分”的名义默认开除出文艺片的阵营!
“你的名字无人知晓,你的功勋永垂不朽”。《无名》无名英雄的宏大命题,比程耳过往任何作品都要更具家国情怀。而这种主旋律的“伟、光、正”,与艺术电影对“世界、社会、生命”之于个人的原创认知以及电影语言的作者性表达,合拍吗?


有人说《无名》初期口碑被错位营销拖累,说它尝试商业片营销路数,用谍战定位忽悠观众进影院,何况档期本身也与影片内容格格不入。在春节档这种合家欢时刻,观众的刚需不是韦编三绝的深度思考,而是老少皆宜的大剂量廉价笑料。
但文艺片借鉴商业营销并非《无名》首创。当年《白日焰火》以爱情悬疑片宣发,同样口碑票房双收。可见,只有真文艺才敢开“超级商业片”的玩笑。
程耳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回应过这个梗,“那天我在剪片子,然后他们拿着手机进来给我看,说好像大家还是觉得太文艺了,我说那咱们就直接打一行字出来——超级商业片。这是一种玩笑,确实也没人往预告片里打这样的口号。”
他说,只是觉得有趣,并没有什么可叛逆也不值当去叛逆。自信且松弛,往往是搞艺术的特质,特质会令人像黑夜里的萤火虫那样出众,让大众从人海中迅速get到。而程耳为一部严肃电影缓缓打出“超级商业片”的title,就是i人的幽默。
 电影不止光影艺术︱还是能陶冶人的艺术
电影不止光影艺术︱还是能陶冶人的艺术票房少并不是文艺片标准。“当艺术穿着破旧衣衫时,最容易让人认出它是艺术”,可这并不是艺术的本质表征,而是受众素质的有待提升。而《无名》面临的吐槽与文艺片整体遭遇如出一辙,那就是电影的作者性表达与大众接受度的悖逆。
但文艺就一定小众吗?就活该晦涩难懂节奏慢?想来,没有谁会比把滔天黑水熬成泼天富贵,以小众艺术引领大众审美的《无名》,更有资格来回答!
程耳电影最具代表性叙事风格就是“闪回式叙事”,这树立了他独特的创作和影像风格。它邀请观众参与,依靠脑补共筑,获得解码快感,是真正的“懂自懂”,不懂就容易蒙圈。这样的影片追求审美和思考,通常面向更为成熟和文艺的观众。

电影是文化工业产物,本质是被消费的文化产品。而在资本热钱涌入电影市场,电影文化工业化大生产的背景下,商业片固然是为观众量身定制的高回报率文化快餐,就连文艺片创作者,也很难不被“唯票房论成败”的观念影响甚至绑架。
文艺片卖不到500万稀松平常。从陈哲艺软语问苍天“儒雅温柔为何被骂”,到黄旭峰怒呛网友“老夫没功劳有苦劳”,世无解药。而文艺片被吐槽,往往是因为文艺片在浅阅读的快餐时代,为追求票房不得不拥抱下沉市场,招惹非目标受众。
但电影只是产品?不,还是文化表达式,是社会的价值观载体。把电影比作产品,那文艺片显然不是快消品,在面对资本与市场时,如何既契合大众性又不失作者性?程耳说,“好看的艺术片也是很好的商品,优秀的商业片也是一种艺术。”

谈到艺术,大多数人可能觉得艺术就是曲高和寡,高高在上,远离日常生活的。而事实并非如此。余华在《河边的错误》路演说,看懂是什么意思?其实是能不能和我们自己的生命经验产生重叠。有重叠就能懂,没重叠就不懂,就很正常。
在这个解释里懂与不懂并不高深。而程耳也一直说,观众不该被低估。看电影的人牵动自己的爱憎,感受到什么就拥有什么,懂或不懂并不那么重要。
要观众别苛求懂不懂,艺术家也要接地气,为艺术而艺术并不真正艺术。《无名》不仅是文艺电影,更是中国电影的文艺注脚,就是因为它既真实表现历史残酷却仍充盈艺术之美。程耳对民国历史非常熟悉,对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了如指掌。


《无名》正是由细密如匝线的真实历史细节构成。说看不懂的咱不是认知鄙视啊,但身在中华,通晓五千年文明史困难,掌握抗战史却绝无门槛!审美差异欣赏不了叙事手法可以理解,为五毛出卖灵魂玷污影片主题的网络暴行却不可饶恕。
世间并无一套通用审美法则,但艺术家试图为审美立法。每个时代都有带着烙印的教条,直到下一代艺术家另立山头,所以贡布里希为艺术驱魅,说“没有艺术只有艺术家”,希望世人别把艺术供上神龛,用神秘和神圣感使自己和作品隔离。
文学领域也有类似“作者之死说”,指作者在作品诞生时如同死了,作品解读和评价由读者说了算。即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没有标准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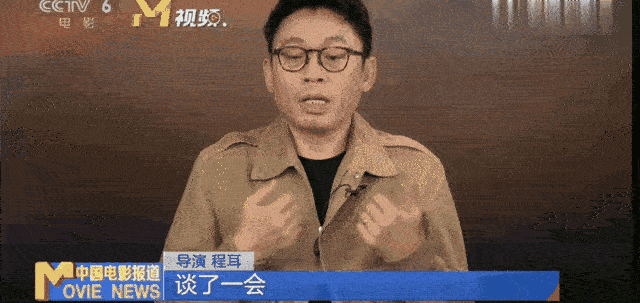
就像我们不能要求每部电影都能直奔国际电影节大奖,都能直击观众心灵经典永流传。我们也不能要求每个电影观众一开始就具有高电影素养,都能get到创作意图心灵共鸣。电影和电影人、电影观众的成长,都需要更宽容的土壤和空间。
当然,现在院线排片留给文艺片的空间实在是太小了!不论国内还是国外,当大众一致认同“文艺片就活该低票房”时,请懂得的业内给文艺片留出一些探索空间。允许它们不解风情,只有在包容的土壤上面,才能开出有生命力的艺术之花。
《河边的错误》能三天过亿夺日冠,至少得益于近30%的连续排片率!而《无名》呢?“当初我无某人,仅靠个位数的排片率苟到9.31亿,全靠命硬!”
 社会审美价值取向︱电影的目的和推动力
社会审美价值取向︱电影的目的和推动力“一条瘸腿的狗,穿过被轰炸后的街景。”某天,程耳拿着灌满墨水的钢笔,在纸上写下了这么一句话。那时候,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所有人都还不知道,它正在成为一部名叫《无名》的电影的起点,而这个残酷美学的瞬间成为电影名场面。
个人审美自由但社会审美有范式。教育与社会文化会耳濡目染规范审美,塑造审美取向。不同时代与不同环境有不同审美取向,而不同审美取向令人做不同价值选择。也即,审美再自由价值观再多元,但凡种下的是稻子就绝不会长成稗子。
倘若单纯以“产品”思维运营电影市场,那么现在就该全都去拍《东成西就》,让《东邪西毒》自绝于市;全都拍《三枪拍案传奇》,让《坚如磐石》自绝于市……真这样,那电影就放弃了社会文化的担当,成了罐头笑声与爆米花的文化荒漠。
艺术和商业是电影两条腿,艺术电影充沛气血,商业电影活络筋骨。当文艺这条腿瘸了,中国电影从国际电影节颁奖台常客沦为红毯常客,也就不冤。


是的,的确有以艺术之名的“银样镴枪头”,当艺术良知被欲望边缘化,所谓艺术就只剩贫瘠苍白的花架子,经不起推敲论证。但《无名》能够让我们看见,一部精致的文艺电影是如何打磨成型的,甚至是简单的电影打板都蕴藏着拍摄门道。
一般导演习惯都是先场记打板,演员再表演,摄影师跟着运镜推轨,但程耳的片场不是。王一博就提到过剧组特别尊重演员,拍摄现场很安静,情绪进入状态后摄影师直接拍摄,演完场记再打尾板,绝不会因打板而打断演员酝酿好的情绪。
后期时程耳直接睡在工作室,每天只有一件事,剪剪剪!得益于近乎狂热的工作状态,去年程耳竟然没阳过!七年磨一剑,只为一部不一样的中国电影。把主旋律揉入类型电影,以类型电影的语言和视听节奏,实现主旋律题材的创新表达。
“真正的好电影一定比商业更商业、比艺术更艺术,对我来说,我一直希望做的事,就是比商业更商业,比艺术更艺术”,程耳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



程耳影像充满精妙隐喻。伪满洲国、上海、香港,《无名》中关于城市的精神叙事方式,渗透在荣宅、76号、霞飞路567号、中环街市、文武庙的建筑物语中;隐藏在日语、上海话、洋泾浜与粤语的杂糅中,引发观众情感共鸣和深层思考。
只存在于渡部与叶先生对白中的伪满洲国,如阴魂带着白日梦魇般的寒气;占据全片主要篇幅的孤岛上海,精致中散发穷奢极欲且表里不一的颓废;而身为国际抗日统一战线枢纽的香港则一派人间烟火,揭示了一个朴素而慰藉人心的世界。
乌云压顶,疮痍满目,隧道尽头,时局意象里的历史信息被压缩进极简叙事,等待解压。直到漆黑的影院虫洞里,谍战叙事中的历史话语扑面而来……



抗日神剧消费苦难,抗战题材扎堆复制,屠杀惨烈心理不适……以往民族苦难史的表达式常常遵循揭露残暴、曝光血腥,甚至以暴易暴规则。而《无名》令人震撼的是以美御丑,令人拍案叫绝:原来苦难可以被冷静而有温度、有厚度的诠释!
只有不识时务的程耳,才能拍出不识时务的好电影。成功的“新主流”电影,《战狼》《长津湖》,硬汉程式与红色经典珠玉在前,而程耳偏偏走了少有人走的路,那就是历史逻辑的艺术叙事。“画框之内,不能染指”,是幕后操刀手的霸气笃定。
轻盈而厚重,冷酷又温暖,文艺的主旋律没有国家交易层面的妥协,完成了现实中未完成的对一个国家侵略罪恶的灵魂审判。《无名》在文化输出意义上,把被孤立的中国抗日史融入了二战大历史的世界叙事——这就是雷霆手段,菩萨心肠。
是时代对时代的寄语,《无名》站着把钱赚了,我辈与有荣焉。在影院,它令你知道什么是文艺的力量。走出影院,你自然会懂得什么是无名者的功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