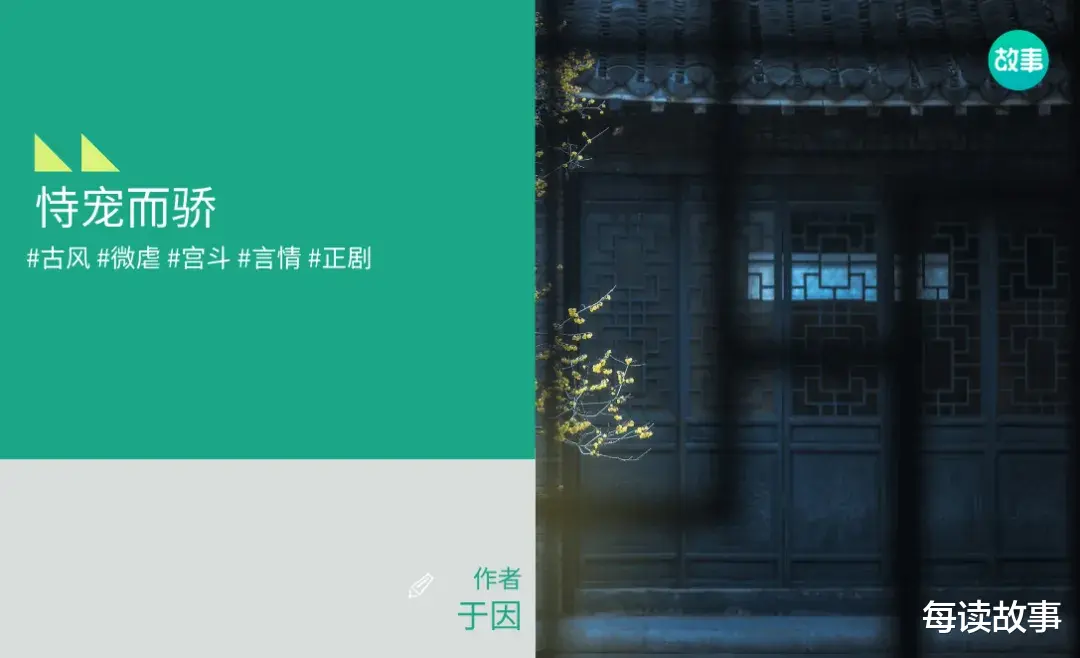
皇上对婉媛的宠爱来得那么轻易,那么令人嫉妒。
她低着头笑,看宫人们跪在她的面前,谄媚地叫她“贵人”。
只有皇上身边的公公叹了口气。
世人只知道皇上喜欢媛贵人这样的女子,却不知道他为什么喜欢。

婉媛入宫那年正值初春,北京城里还冷,下着雪,她被人从马车上扶了下来,雪花簌簌地落在她发上的浅青色绒花上,嬷嬷替她披上斗篷,婉媛便踏着薄薄的白雪一步步走进了宫门。
这一年,她十六岁。
嬷嬷们都说婉媛生了一张得宠的脸,正因当今皇上最喜欢柔弱娇小的女子,她的一双凤眼含着泪,微微蹙眉,我见犹怜的模样果然一眼就被皇上瞧中了。
又是落雪的一个夜晚,婉媛第一次侍寝。
那晚的雪下得很大,屋里火盆烧得暖烘烘的,婉媛坐在床边头都不敢抬,瞧见明黄色的鞋子一点点靠近,好闻的香料味弥漫开来。
“抬起头来。”皇上说。
皇上的声音不大,却带着一种不容置否的威严,她慢慢地抬起头,第一次窥见天颜,婉媛竟没有像她料想中的腿软,她瞧着皇上的脸,脑袋里胡思乱想,“皇上与阿玛好像啊。”
一样的高大,一样的胡子,可面容不像,阿玛没有皇上这样一双眼睛……她就这样仰头看着,连行礼都忘了,回过神来时才“扑通”一声跪到地上。
婉媛吓坏了,她生性胆小,生怕自己被斥责不懂礼数,可皇上却没有责备她,他伸出来了手,婉媛看着那只手,最终还是把自己的手放了上去。
他拉着婉媛从地上起来,皇上的手好暖,她半天都舍不得放开。
那夜的蜡烛燃了许久,自那之后,婉媛就得宠了。
这是许多人都能料想到的。
皇上一连几天都宠幸她,册封了她为答应,没几天,又升为贵人,宫里的闲言闲语不少,都说这一切都得益于她生了一副好容貌。
有一同进宫的在背后悄悄称她是一朵“小白莲”,言语间颇为不屑。
其实婉媛并不明白,她这算什么好容貌呢?
她虽长得标致,但常年服药,气色远没有同岁姑娘鲜活。她的性格也不够好,阿玛总不喜欢她畏畏缩缩的样子,平日里见了也是多加斥责,婉媛眉间凝着愁绪,哪里算得上美貌。
要说美人,她的妹妹明艳动人,像极了草原上热烈盛放的花,从小到大只要有妹妹出现的地方,没有人能忽视她。
阿玛很宠爱妹妹,小时候学字也是阿玛手把手教的,妹妹性子活泼,阿玛也从不拘着她,骑马射箭样样都会,可以不用费力学女红,也可以毫无顾忌地放声大笑……
相比较婉媛,妹妹活得可比她自在多了。
然而嫡庶有别,妹妹再受宠,也仍比不过婉媛才是正儿八经的嫡小姐。所以到了选秀时,她见到了数日未见的阿玛。
婉媛乖巧地跪在堂下,父亲坐在那里,手指一下一下点着桌子,屋子里十分安静,她也不敢抬起头去看。只听着阿玛的声音带着一贯的威严,他语气平淡地说,“你入宫去吧。”
婉媛吓了一跳,心惊地抬起头,她的心脏怦怦直跳,掩不住自己的兴奋连谢了阿玛好几句。
她瞧着父亲的脸上仍然和往常一样的冷淡表情,妹妹站在阿玛的身边,她的眉眼弯弯,眼睛里没有丝毫的难过。
不能入宫,妹妹似乎并不遗憾。
那又如何,婉媛真的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
她在这府里十几年吃穿不愁,不过只是……不受宠罢了。
入宫的那天京城下雪了,额娘十分伤心,她的身上弥漫着一股佛堂的香火味,泪眼婆娑地摸着婉媛的脸说不出话,最后只叮嘱了一句,“傻孩子,照顾好自己。”
她欢欢喜喜地进了宫,所有人都说她能受宠,于是她真的得宠了。

婉媛的宠爱来得那么轻易,那么令人嫉妒。
她低着头笑,宫人们跪在她的面前,谄媚地叫她“贵人”,眉眼间的热切与讨好是她这辈子都没见过的东西。
她便不在意那些隐藏在角落冰冷的眼神。
皇上身边的公公很会察言观色,几次提点下面的人,为此替婉媛挡去了明枪暗箭。
公公明白皇上需要什么。
皇上喜欢她,因她美貌,因她年幼不谙世事,所以,他并不介意给她足够的荣宠,来让婉媛脸上的红晕更加浓烈。
他赏给她珠宝与绫罗,赏给她独一无二的院子,特准她拥有私厨,就连婉媛平日里吃的药,都要好几个太医配。
婉媛得到了很多,她内心的风雪似乎被春风拂过,开出了千树万树的花。
她想,她是很好的,她是值得被珍视的,她也会成为让父亲骄傲的女儿。
夏天去行宫避暑时,除了皇后之外,皇上只带了婉媛一个。
这无疑让她成为了眼中钉。
从行宫回来时,常有妃子把她揪去参加无聊的活动,莺莺燕燕们聚在一起,婉媛总会因各种由头受罚。
有一夜她抄写着经文,边抄边落泪,正巧被皇上看见,皇上替她擦了眼泪,手掌托着婉媛的下巴,沉思了好一会儿。
婉媛觉得皇上的眼神有些奇怪,明明在看她,思绪却不知飘到了何处。
皇上的眼里透着怜惜,“不用抄了。”
后来,再没有妃子来找过婉媛的麻烦。
这一举动,无疑给了她莫大的安慰,也消除了她的瑟缩。
婉媛日渐活泼起来,她越来越喜欢躺在皇上的怀里撒娇。
皇上问她为什么性子变了那么多,但是婉媛还没回答,皇上就笑了。
婉媛不知道,皇上看到了婉媛的那双眼睛闪着点点星光正瞧着他,她总藏不住那满眼爱慕的神色。
婉媛只有十六岁,她动情了。
皇上喜欢那双眼睛,单纯的,属于少女的眼睛。
他看到过许多这样的眼睛,却仍然是爱的。
只有这样的眼睛,才能让他忘却政务的繁忙与垂垂老去的身体。
少女的真心与深情,永远是一味最好的良药。
初秋,凉风渐起,婉媛的咳病有些严重,皇上让太医为她细心调养,但为了避免沾了病气,皇上好一段时间没去她那里。
一直等到婉媛的病好了,皇上也没有来。
婢女穗儿悄悄告诉她,有位答应很会弹琴跳舞,皇上最近都去她那里。
婉媛隐约记得那个名字,在选秀时,那是个容貌艳丽的美人,有些张扬,有些娇纵。
嬷嬷们还曾敲打她,叫她别老是这样咋咋呼呼,一来没有规矩,二来皇上不喜欢。
当时她还反驳,她说她本来就是这样的,变不了。
果然,婉媛夺走了皇上所有的宠爱,大家都只能守着冰冷的宫室,那个女子也不例外。
想来她也是付出了许多努力,趁着婉媛生病,夺回了皇上的注意力。
婉媛很失落,终日落泪,眼见着又要病了,穗儿还有几分聪慧,将婉媛引到了公公那边。
婉媛眼睛泛红,悄悄递过去一个盒子,又向他行了一礼,“烦请公公告诉皇上,媛儿的病好了。”
公公连忙扶她,东西没收,说话滴水不漏,叫人听不出一句不好,就是不知道他答应了没有。
穗儿安慰她,“小主莫怕,我听说那位答应进宫时太过娇纵,得罪了不少太监宫女呢!”
婉媛勉强地笑了笑,可那位答应貌美又热烈,如同她的妹妹一样,她最是惧怕,也最是羡慕。
那天晚上,婉媛固执地等着,已是深夜,蜡烛的烛花一跳,如同她的心一般。
突然,她听到了熟悉的脚步声,虽没有人通报,但她认得这个声音。
婉媛险些落下泪来,她的声音低沉又委屈,小声地诉说着。
“臣妾还记得小时候额娘总彻夜点着蜡烛等阿玛过来,可每一次蜡烛燃尽了,阿玛也没有来……”
婉媛痴痴地看着桌上的蜡烛,突然眼睛被一只手捂住,皇上温热的呼吸吐在她的脖颈,“朕不是你阿玛,你不用学你额娘点灯。”
她的背靠在皇上的胸膛上,心里涌出一股暖流,驱散了深秋的凉意,婉媛窝在他的怀里娇滴滴地问,“那皇上明晚还来吗?”
耳边是皇上含笑的声音,“来。”
她也跟着笑了。

院子里的那棵梅树长了许多年了,满树繁花,因为它,冷清的宫墙里多了鲜艳的色彩。
殿里放着火盆,暖烘烘的,雪停了,婉媛便让人打开了窗,于是皇上刚坐在塌上,就瞧见了院里一枝独秀的梅树。
“皇上。”
婉媛轻声唤着他,皇上正看着那梅花愣神,也不知在想些什么,她垂下头,把自己今天亲手做的糕点小心地往皇上那边推了推。
他一回过头,刚好就撞见了婉媛的这一番动作。
小心翼翼,又充满了想要掩盖的讨好。
自从秋日里的那场病后,婉媛就有些变了,她的眼睛里多了几分愁容,这个眼神,皇上再熟悉不过了。
他捻起那块糕点,杏仁的滋味在他的舌尖漫开,这是他喜欢的味道,亦如婉媛含羞的笑容。
“朕很喜欢。”
于是少女眼底的笑意更浓了,足以划破冬日的苦寒,皇上有些出神。
那天皇上离开时,公公敏锐地觉察到主子有些不太对劲。
“皇上?”
公公见皇上又在辇边停下了,他还是看了看那棵梅树。
“皇上,媛贵人院儿里的这棵树有什么不妥当?”
皇上没有说话,一直到了晚上就寝时,他才想起什么似的吩咐他。
“明日多送点花草给媛贵人,就一棵梅树,怪冷清的。”
公公点头称是,立刻着人挑些花草,又让人去暖房捧了几盆珍稀的花亲自送去。
这样的殊荣,婉媛受宠若惊,自秋日后,她的心总这么七上八下。
公公瞧着这位年轻的小主,将她的家世以及入宫之后的交集捋了一遍,仔细想来,她还算乖顺妥帖,又不生事,是个合适的苗子。
“贵人,这些花可珍贵着呢,都是要留到年底祭辰时才搬出来的,连皇后娘娘那儿都没有,这赏赐可是独一份啊。”
婉媛惊的手都颤了几下。
公公起身就要告辞,临走前提点几句,“皇上疼贵人,贵人更要保重身体,莫要忧思,才能与皇上长长久久啊。”
独一无二的宠爱,这几个字对于一个后宫女子来说,到底代表了什么,婉媛很明白。
她望着院中的梅花,悄悄落了泪。
公公走在红墙之下,又下了雪,身后的太监替他打了伞,公公叹了口气,突然想起了一桩子旧事。
从前皇上年幼时,皇上的额娘不受宠,连跟着先皇也不喜欢他,那时候额娘住的院子也是冷冷清清,却不知什么时候突然长出来一株红梅,开得鲜艳夺目,那年冬天,这梅树的枝头探出了墙,竟吸引了先皇。
先皇子嗣多,尤爱宠妃的孩子,皇上幼时并不突出,且身体不太好,对比其他皇子稍显柔弱,所以除了宫宴,先皇一年也见不到几回,因着那株梅树,皇上也得以见到了父亲。
也许只是几句无心的赞叹,却在皇上的心里埋下了种子。
年幼的皇上精心伺候那棵树,先皇却再没来过。
后来皇上出宫建了府,府里也没栽种过梅花。
恐怕,因为媛贵人院子里的那棵树,让皇上想起了他幼时期盼父亲来看看自己而伺候的红梅吧。
公公叹了口气,世人只知道皇上多喜欢媛贵人这样的女子,却不知道他为什么喜欢。
在小院子里翘首盼望的媛贵人,那瑟缩又渴望的眼神,不正是像极了曾经的皇上吗?
公公又叹了一口气,皇上已是九五至尊,当年在腥风血雨的夺嫡之中胜出,早已不是那个在宫墙下苦等的幼子……却仍然忘不了儿时的遗憾。
他只希望,媛贵人能懂事一点,莫要再让皇上看到一丁半点的愁容。

很快便到了年底,正值皇上的寿辰,这在后宫可算是大事,到时所有的妃嫔都会参加宴席,没人敢轻视。
婉媛也做了很多准备,也许是因为那个能歌善舞的答应让她有了危机感,婉媛也让人请了位善舞的老师,每日偷偷练习,十分辛苦。
婉媛十六岁,骨子里有一种无畏。
少女的勇敢总会驱使她做出令人意想不到的反应。
所以在宴席上,她看到那个疯魔的女人向皇帝扑过去的时候,她下意识地替皇帝挡了下。
匕首刺穿了她的脊背,巨痛让婉媛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
侍卫将那女子拖开,拔刀守在皇上身边,人声嘈杂之间,是公公尖锐的嗓音,高喊着传太医。
婉媛穿着一身雪青色的衣裳,是很珍贵的布料,总共没多少匹,皇上却赏给她做了身衣裳。
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婉媛特意学了舞,很难,她准备了好久,还没跳给他看呢,她希望能讨心爱之人开心,哪怕一个笑容呢?
皇帝抱着她,身体是发抖的,她的血浸透了两人的衣裳,她被皇帝抱在怀里,皇上抚摸着她的脸说,别怕,没事的,朕会救你。
那一刻,她身上的疼痛感似乎消减了许多,皇上的身上很暖,婉媛艰难地扯出一个笑容。
她分不清,到底是她救了皇上,还是皇上救了她?
太医来得很快,她被抬着回到宫里,太医们跪了一地,谁也不敢瞧坐在外间脸色阴沉的皇上。
所幸,伤口并不深,且没在要害,刺客并未用多少力,处理了伤口,休养一段时间便好了。
太医们松了口气,庆幸保住了自己的脑袋。
婉媛盛宠更浓了。
她躺在榻上,总管又派了一些宫女太监来她的宫里,其中有一个大宫女叫春儿,十分细心,婉媛还感叹穗儿有了帮手。
皇上也常来,陪她说说话,喂喂药,婉媛担心的像去年秋天那样的情况再没有出现,她内心的忧虑彻底放下,明明受了伤,脸上的笑意却更多了。
她娇嗔道,“还好皇上没有受伤,这伤口愈合呀,真是难受。”
皇上抚摸着她的一头秀发,语气温和,“等你好了,天气就暖了,朕带你去南巡。”
婉媛眼里亮晶晶的,高兴得差点从床上坐起来,还是皇上按着她,眉眼间带着笑意。
所以虽躺在床上很是难受,她便期待着即将到来的春天。
新来的春儿替她捶着腿,说起她的伤,又说起那个行刺的女人。
春儿显然是知道那个女人的,听说入宫十多年了,曾经也受宠过,不知道后来犯了什么错,便被皇上厌弃了。
春儿叹到,那女人是被逼疯的,后宫总能逼疯一个女人。
婉媛有些失神,随即又是庆幸深受宠爱,且十分规矩,怎么也走不到她的那一天。
不过,那女人胆敢行刺皇上,这可是诛九族的大事,为家族招来这样的祸事,婉媛十分不齿,想来那女子性格也不太好,皇上厌弃也是应该的。
等她伤好得差不多时,她听宫女说,那个女人竟是没死。
这不合常理。
婉媛没有问皇上,只是私下里旁敲侧击,听说皇上替那疯子找了个说辞,免了她的罪。
行刺竟无罪,婉媛的心里涌起了无限的好奇。
等她能下地活动时,她鬼使神差地找去那女子居住的宫室。
比起婉媛住的地方,女子的宫殿虽不破败,却十分冰冷,空荡荡的,冷风一吹,就让人打了个激灵。
女人的宫里只有一个年老的婆子,似乎对她的到来并不稀奇,请她进了房间。
穗儿扶着她,眼神有点打退堂鼓,婉媛心一横,就走了进去。
女人坐在榻上,披头散发,房间里四处遮着帘子,女人手持一根蜡烛,烛光照在她的脸上,她转过头,吓了婉媛一跳。
她的右脸靠近耳朵的地方有一片可恐的疤痕,一直蔓延到锁骨处,婉媛想起皇上寿辰那日女人还梳了个别致的发型,精心打扮,遮住了伤疤,所以当时所有人都没注意到她脸上有伤。
想不到她竟是如此的面容,很难看的一张脸。
女人笑得疯癫。
她说,她知道婉媛为什么要来,女人说,“皇上当然舍不得责罚我了,我可是,皇上的宠妃啊!”
穗儿拉着婉媛向后退了一步,想劝主子离开。
婉媛却按住了穗儿的手,她的心里莫名涌起怒火,女人差点伤了皇上,却这么嚣张。
“你为什么要行刺?”
女人放下蜡烛,似乎平静了下来,她摸着脸上的伤疤,思绪不知飘到了何处,突然,她看着婉媛,眼神渐渐炽热。
“我进宫的时候,也是如你一般的年纪,也是情窦初开,貌美如花啊!”
她说,“我也不想行刺,可是,我明明精心打扮了,皇上却一眼都没瞧我。”
女人指着她的脸,“当年,我也救过皇上,行宫被歹人放了大火,是我扶着醉酒的皇上逃了出来,可火却烧了我半边脸。”
她的声音绝望又凄厉,“我救了他,他却嫌我丑!”
女人想要扑过来,却被婉媛躲开了,她眼里含泪,“你看,多大的恩宠,也不过因着你漂亮罢了,你当你有多特殊?”
穗儿再不想多待,拉着发愣的婉媛就往外走,身后是女人的声音,带着无限的悲凉。
“后宫佳丽三千人,何谈一人情与爱?”
如同魔音一般,让婉媛夜里做了好几个噩梦。
婉媛不服气,她不信,她觉得自己在皇上的心里有一席之地。
公公都说了啊,独一份的宠爱,况且,皇上还说要带她去南巡呢。
她安抚了自己的内心,沉沉睡去。

皇上没让婉媛失望,她期盼着南巡,宫里也在做准备。
少女总是不够沉稳,这一年间,她被皇上养得太娇了,总是掩盖不住言语间的向往。
皇上也纵着她。
她洁白的背上多了一道疤痕,婉媛照过镜子,很丑,很突兀,然而侍寝的时候,皇上摸着她的伤痕,眼里有些疼惜。
婉媛想,看,那女人说的不对。
然而春天到了的时候,南巡却突然耽误了。
消息传到婉媛的宫里时,她正笑着与穗儿聊衣服的新花样。
太监通传,婉媛的父亲徇私枉法,证据确凿,已下大狱。
她的心猛地一沉,不可置信地瞧着那小太监,连问了好几遍,“你说什么?”
并不难查,婉媛很快便了解了情况。
她虽是嫡女,却因母亲不得宠,父亲也不喜欢她,所以她生得畏畏缩缩。送她入宫,也是因为选秀时府里有两个适龄女子,得出一人。
她的父亲本不指望她在宫里能得到皇上的青睐,然而婉媛受宠,连带着父亲也在朝堂上水涨船高。
尤其婉媛救驾之后,皇上奖赏了她的父亲。
其实,她的父亲并没有在之后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只是他突然成了红人,朝堂之上,风云莫测,他便被人翻了旧账,抓住了把柄,在皇上那参了一本。
这是皇上最不能容忍的事。
案子查得很快,确实证据确凿,罢官流放是免不了的。
婉媛在后宫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却听说父亲已经认罪,只求不累及家人。
婉媛虚弱地瘫倒在地,穗儿哭着说,她的父亲还是惦记她的处境的。
婉媛笑得奇怪,她很清楚,父亲活不成了。
流放之地苦寒,更何况,父亲年事已高,若一人去,定会死在那里。
夜里,皇上没有来,公公说,皇上近日公事繁忙,宿在偏殿了。
公公给她带来了赏赐的点心,临走前,望着婉媛湿漉漉的眼睛叹了一口气,又是提醒:“贵人,保重身体,没什么事,就先不要打扰皇上了。”
婉媛苦笑着缩在榻上,她暗暗下了决定,她想去再见一次父亲。
许是上面授意,她得以顺利进到大牢。
父亲花白得头发凌乱,老态龙钟,强大如父亲,竟有这样的一番模样。
她哭着喊了声,“阿玛。”
父亲抬起头,见是她,“娘娘,您来了。”
她将提盒里的酒菜摆了进去,父亲没有动,婉媛带着哭腔问他怨不怨自己,父亲摇了摇头,竟向她行了一礼。
“臣,跪谢娘娘大恩,臣是个俗人,最惦记的还是臣的妻儿老小,流放之后,望娘娘不要忘记往日的情分,多多照顾他们。”
婉媛的身体一阵冰凉。
她擦去了脸上的泪痕,眼神趋于冷漠。
“果然如此,果然如此啊,阿玛,您真是偏心啊。”
她愤愤离去,以往压抑的情感再也压抑不住。
什么还惦记着她,父亲认罪,是怕祸及子女,姨娘的子女,他这一生最爱女人的子女。
她入宫,也是妹妹不想入宫,父亲心疼妹妹,他很清楚骄傲张扬的妹妹并不适合宫廷,便让她入了宫。
若是妹妹想来,是不会轮到她的。
她的母亲,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明媒正娶的妻子,成亲前并未和父亲见过面。
所以他们并没有料想到他们会感情不和,这对于这个后宅女人来说,便是莫大的悲哀。
她出生之后,父亲很快便纳了一房妾,那是父亲选中的,合他心意的女人。
从此,他们琴瑟和鸣,生儿育女,而与母亲保持着十分客气的疏远。
母亲被困在后宅了,连心也困住了。
婉媛的记忆从未这样清晰过,她记得父亲从来不在她面前笑,婉媛原以为父亲是不会笑的,直到她看见阿玛怀里抱着弟弟,愿意让妹妹骑着他的脖子,父亲与他们在院子里嬉闹,笑得眼睛都弯起来了。
原来,她是不配看到父亲的笑脸的。
她看着紫禁城高高的朱墙,“阿玛,你总要抬头看看你的大女儿。”
穗儿出去了,春儿给她倒了杯茶,她小声说,“贵人不如去求求皇上。”
婉媛苦笑,“后宫不得干政,这种事,我去又有什么用?”
春儿摇了摇头,“贵人受宠,哪怕是脱不了罪,也好歹让大人好过一点,为人儿女,怎么忍心亲眼看着父亲受苦。”
她的心猛地一颤,婉媛痛苦地抚着额头。
“贵人,莫要担心,皇上疼您,最差,也不过维持原判罢了。”
婉媛猛地坐了起来,穗儿端着托盘进来,却见主子风风火火地出门去了,她连忙放下托盘,问春儿,“主子怎么了?”
春儿摇了摇头,满脸的担忧。
然而,穗儿还是晚了一步,等她追过去时,婉媛已经跪到了皇上的步辇之前。
婉媛很明白,她过不了自己这关,她这一生都在期待父亲的目光,她必须求皇上,她希望阿玛能看看她,她希望自己是让父亲引以为傲的女儿。
然而这世上的事就是这样,她一直没有得到的东西始终都没能得到。
皇上默不作声,昔日温情的眼睛里此时全是冰冷。
公公瞧了眼跪在一边的婉媛,抬手吩咐步辇接着走。
没有人回过头看她。
婉媛的额头抵在地上,硌得生疼。
那天晚上,婉媛得到了消息,她的阿玛在牢房里自尽了,她送过去的饭菜,阿玛一口没动。

春末,公公带着旨意来到婉媛的宫里。
皇上洋洋洒洒写了一堆,大意是婉媛“恃宠而骄”,罚她在宫里禁足。
确实,她拦下皇上步辇跪地替父亲求情的行径,可不是恃宠而骄吗?
婉媛沉默地接了旨。
公公恨铁不成钢地叹了口气。
他想,到底年纪小,不懂事,被宠坏了,没有一点眼力见儿,皇上最忌讳后宫干政,哪怕是皇后也不能纵容外戚,怎么这点道理不懂?
皇上年纪大了,就希望身边有个乖顺的可心人,公公对婉媛也是寄予希望的。
这宫里有过许多的“婉媛”,公公瞧着皇上的新鲜劲,以为她会是最后一个。
可惜。
婉媛坐在桌前,春儿替她倒了杯茶,“贵人,喝茶。”
婉媛托着下巴瞧她,“你好像从来都没喊过我主子?”
春儿扑通一声跪下。
婉媛笑着说,“那么,你的主子是谁呢?”
现在想来,那毁容的女人也好,还是现在这事也好,春儿总是有意无意地引导。
不过,这是春儿的错吗?不,是春儿刚巧说中了她的内心。
她只不过适时地推波助澜。
婉媛无声地笑了,“滚吧,别让我再看见你。”
在父亲死的那一刻,她已经没有力气再想其他事了。
父亲自尽,还保留一分颜面,总好过死在流放的路上。
父亲根本没指望她能救他。
她的阿玛看不见她,到死都看不见她。
而皇上对她失望了,他拒绝了她的请求,连同一起失去的,还有她那短暂的荣宠。
一直到了深秋,宫里的炭火呛得婉媛头疼,她抱着自己的膝盖,望着摇晃的烛火,突然间笑了起来。
她终于明白了那个疯女人。
婉媛知道,她的宠爱……也已经没有了。
她只能等着,正如去年秋天生病时,她巴巴地等着皇上能想起她,然而,如今却比从前痛上百倍。
一天又一天,无人问津。
她越来越绝望,心想,皇上就这么绝情?只因她做错了事,便能把从前的情意一笔勾销?
穗儿不忍主子终日坐着发愣,低声告诉她,皇上早已又有了宠幸的人,仍是娇滴滴的,和她从前一样。
她院子里的树叶子落光了。
婉媛的心冷了。
她十七,尚且不懂得处理情爱,只觉得瞧着了苦,就蘸着那些苦一天天地活下去。
皇上再见婉媛时,婉媛的娇已经消失了,她沉默着,哪怕映着院子里开得艳丽的梅花,那抹红却染不到婉媛的脸上。
她还是我见犹怜的样子,眉间带着愁绪,可皇上知道有什么不一样了,她眼底的光不见了。
婉媛进宫的日子短,还是不懂事。
她瞧着好不容易来看她的皇上,竟笑了,“皇上当时问我性子为什么变了那么多,因为婉媛不够聪明,以为得了皇上的爱便得了一切,婉媛心里很欢喜,日日都想着皇上,如今这欢喜……已经没有了,我想,我不爱皇上了。”
她是赌气的话,她怨他这么久不来看她,她怨他的宠爱是最虚幻的东西,诱得她一步步踏入深渊。
皇上看了她良久,连屋子都没有进,然后转身离开,再也没有来过了。
她还太小了,她想,她可能需要一生在深宫里徘徊,像一朵花儿一样慢慢凋零。
她尝试恨皇上,越恨,越想,痛苦难忍。
她想,再等等吧,等到几十年几年过去,便淡了。
如后宫里那些形形色色的女人一样。
可婉媛没等到几十年。
第二年隆冬,她在梦中惊醒,院里的梅树开得满树繁花,婉媛记起来了,这是她来宫里的第三年,而今年,她也不过是十八岁而已。
穗儿慌慌张张的跑进来,婉媛恍惚中听到远方传来的钟声,在雪中发出低沉的悲鸣,她看着天空中簌簌落下的雪花愣了神。
穗儿跪在地上磕了个头,她哭着说,“主子,皇上驾崩了!”
婉媛转过头,穗儿哭哭啼啼的,抬起头却瞧见她的主子双眼无神,怔怔地盯着她。
“主子……”
婉媛终于动了,她的眼神找回了焦距,宫墙那头不知什么人在喊,吵吵闹闹的。
她笑了,“你胡说。”
仿佛听到了天大的笑话,她摇着头,嗤笑着,“我不信。”
婉媛眼睛睁得极大,“他怎么会死。”
丧钟鸣了许久,久到匆匆来宣旨的太监还没有走进婉媛的院子,就听见穗儿的尖叫声从墙里传了出来。
皇上已死,她爱过恨过,不等时间将爱恨消化掉,就这么突如其来地终结了。
婉媛哭了,她哭得很伤心,这一年她才十八,情窦初开的好年华。
院里的那口井,她跳了下去,她的一生,没有几十年。
后记
太医院的病历里有记载,先帝死于一场突如其来的风寒。
也许那个冬天太过寒冷,先帝勤政,彻夜批改奏折,等到天亮时,他便撑着额头久久没有起身。
风寒而已,然而先帝上了年纪,那一年,前朝后宫都不安宁。
先是皇子们党争激烈,先后死了不少大臣,再是后宫里一位原先受宠的贵人不知做错了何事,很是突然地失宠了。
先帝忧思过度,风寒断断续续的不好,当时正值皇子争储激烈,病情不敢声张,之前都瞒着。
直到隆冬时,先帝躺在床上拟了几份圣旨,交代完后事,溘然离世,后由总管太监宣旨,选定了下一任皇帝,朝堂上的混乱这才平息了。
在先帝留下的几份圣旨中,还有一份有些奇怪的。
圣旨上说命后宫里的一位贵人即刻出宫,褫夺封号,贬为庶人。
后宫女子,一旦入了宫,除非死,这一生也出不去,这份圣旨说是罚,实际上却是奖。
这独一份的荣宠,可真是不得了。
新帝翻着这份圣旨,询问身边的总管太监,公公服侍了先帝一辈子,如今又开始服侍新帝。
“这圣旨怎么还在这儿?”
“回皇上,那贵人福薄,还不等圣旨到,却已经投井自尽了。”
皇上点了点头,“也算忠贞,后事怎么办的?”
公公的声音低沉,“事发突然,正值先帝大丧,只简单地办了,后随先帝葬于西陵。”
他的记忆里突然浮现出那位贵人的音容笑貌,可能是时隔不久吧,他还记得清清楚楚。
真是个倔强的姑娘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