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伴随资产阶级维新改良、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小说被作为新民救国的利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他们从欧美、日本重视小说并以小说助推社会政治改良的成功经验中受到启发,充分意识到要想变法,必须新民;要想新民,必须启蒙;要想启蒙,则必须运用小说作为导愚启蒙的工具。

《新小说》所载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可是,由于传统小说思想陈腐,无法承担新民的使命,因而梁启超大声疾呼:“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1]那么如何通过“新小说”来“新民”呢?维新派认为,最便捷、有效的办法就是用小说来传输“域外新知”,开启民智。而他们所谓的“域外”,主要是指当时比较发达的欧美和日本,“新知”主要是指“西学”,内容包括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政治学说等。
目前,学界对于清末新小说、翻译小说的研究,或多或少都会涉及西学东渐的问题,但尚显不够系统、深入。有鉴于此,本文拟对清末小说传播域外新知的动因、内涵、方式以及造成的影响等进行较为系统的观照和研究。

一、以小说传播域外新知成为时代潮流
在梁启超竭力倡导的以小说来新一国之道德、宗教、政治、风俗、学艺、人心、人格的影响下,中国小说开始进入传播域外新知、启迪民智的新时代。
当时,那些“相率求学海外”的青年学子,如雨尘子、韩文举、冯自由、郑贯公、罗普、麦孟华、麦仲华、梁启勋、卢藉东、方庆周等,追随在梁启超左右,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为主要阵地,积极翻译外国小说,不断创作“新小说”,并以“小说丛话”的形式对小说创作进行理论探讨。一时间,新小说的著译、新知识的传播,蔚然成为一种时代潮流。
1902年8月10日,横滨新民社出版冯自由编译的《女子经国美谈》,书首有“杞人”之序云:“然自甲午而后,志士仁人之欲文明吾国也,敝唇舌以抵抗时流,标新说以号召天下,卒至赴汤蹈火,不惜身命以为我国民者,其苦心亦至极矣。然上下懵懵,今犹熙然。其殆人民智识程度未及此,不足以容斯高义也乎?”他反思维新变法失败,乃在于国民不开化。那么如何开化国民?他鉴于泰西、日本均曾利用小说来启蒙国民,认为编译小说,传播新知,“必能开民之脑机,导之以文明之前路”,因此他呼吁“我邦人士,多集小说而编译之”,则其“裨益于民智民气,较报章典籍必百倍其功矣”。

《新小说》
“小说界革命”运动兴起后,一时间凡著译“新小说”者,几乎无不以传播新知、开通民智相号召。略举几例,以见一斑。
1903年9月12日,上海《国民日日报》开始连载《我有我》,篇首“引子”云:“外国人的小说,有说读书的,有说种田的,有说手艺的,有说生意的,有说人情风俗的,样样都说的实在道理,叫人打起精神,可以照著他做事。”
1905年2月15日,上海《中外日报》刊载“理想小说《千年后之世界》”广告云:“是书材料丰富,趣味浓郁,其中包孕有关物理学、伦理学、心理学之精微,及宗教的、社会的、世界的观念。……吾知是种小说为吾国所未有,必大裨于今日社会,迥非寻常说部之可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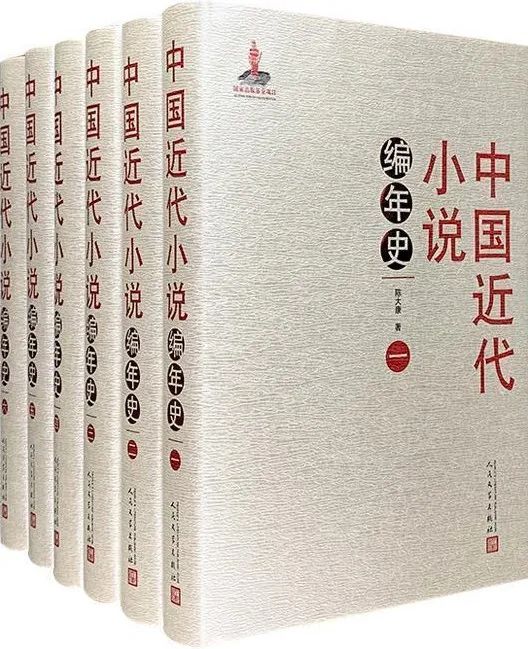
《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
1905年5月28日,上海《新闻报》刊载小说《回头看》广告:“是书以小说体裁发明社会主义,假托一人用催眠术致睡,不死亦不醒,沉埋地下石室之内一百余年。经人发掘,一觉醒来另是一番景象。其所纪述之工艺队、公栈房、电机乐部、公家膳堂、免除关税、改良诉讼一切组织,即欧美自号文明,其程度亦相去尚远。试展读之,真不殊置身极乐世界也。”
1906年4月,上海务本图书社出版《环游地球旅行记》,声称:“是编面目虽仅仅小说家言,而卷中所述如山川风土、名都胜迹、各埠商业、地球形势、各国政治等,无不言之綦详,号为小说,实含有天文、地理、航海、测绘,以及农工商业等专门学数十种。读此一部,如读专书十册,修科学三年。”
1907年8月,上海小说林社出版《黄金世界》,指出:“书中政治、学校、风俗、社会诸端无不悉具。”
1910年5月9日上海《时报》刊载改良小说社“新才子书出现”广告:“本社出版各种新小说,类皆词旨浅显,议论明通,可以启发心思,可以增长识见,可以洞达世情,可以研究学理,不特官商学界皆宜购览,即妇女童蒙,亦当手各一编,藉收开卷之益。”
由此可见,以著译“新小说”传播域外新知识,吸引广大受众,以期启迪民智,已成为时代新风。
不仅如此,有不少文人还专门著文从理论上阐述以小说传播新知的重要性。如1905年7月10日,上海《时报》刊载“冷”(“冷”是《时报》主编陈景韩的笔名)《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下)》,内云:“中国之社会,其于小说宜提倡之点,究当如何?……其一,当补助我社会智识上之缺乏。夫我社会所以沉滞而不进者,以科学上之智识未足故也,以物质上之智识未有经验故也。因之而安于固陋,入于迷信者,大半以此。若提倡小说者,而能含科学之思想、物质之经验,是则我社会之师也,我社会之受其益者当不浅。……若提倡小说者,而能启发国家之思想,振作国家之精神,是亦我社会之指导者也。我社会之受其益,亦必不浅。”他积极提倡用小说来传播科学知识,启发国人的国家思想。

《黄世仲小说创作研究》
1907年8月9日,香港《中外小说林》第六期刊载“老棣”(“老棣”是《中外小说林》创办者黄世仲的笔名)《文风之变迁与小说将来之位置》,认为:“且以今日为知识竞争时代……尤注重夫知识问题者,合上中下三流社会于一炉而冶之,庶足以启民智,壮民气。”这也是以世界眼光来看小说传新知、启民智的重要性。
1908年1月28日,《中外小说林》第十八期,“老棣”又发表了《学堂宜推广以小说为教书》,提出学堂应当以小说“开学生之知识为要”,认为“读政治小说者,足生其改良政治之感情;读社会小说者,足生其改良社会之雄心;读宗教小说者,足生其改良宗教之观念;读种族小说者,有以生其爱国独立之精神。其余读侦探小说生其机警,读科学小说生其慧力,有以使之然也”,因此以小说为教科书,可以“使之增其知识,开其心胸,底于速成,则于智慧竞争时代,小说诚大关系于人群者也”。
至于清末一些小说期刊的创办,也无不将传播新知、开启民智、改良社会作为办刊宗旨。如1903年5月3日,《绣像小说》在上海创刊,创刊号发表了《本馆编印绣像小说缘起》,声称该刊物“远者摭泰西之良规,进挹海东之余韵,或手著,或译本,随时甄录,月出两期,借思开化天下愚,遑计贻讥于大雅”。

《绣像小说》
1906年8月9日,上海《小说七日报》创刊,其发刊辞云:“凡可以开进德智,鼓舞兴趣者,以之贡献我新少年,以之活泼其新知识,又奚不可?”
1907年12月,上海《月月小说》第一年第十号出版,刊载《<月月小说报>祝辞》,声称《月月小说》旨在“发㧑新理想,以激进国民;搜求新智识,以饷遗国民”。
总之,清末由于小说被作为新民之利器,因而以小说传播域外新知,开化民众,遂成为一种时代潮流。诚如1915年陈光辉、树珏在《关于小说文体的通信》中所言:“因其民情风俗之有异于我,今以小说输入,使我民阅之,渐有世界智识,诚盛举也。”[2]

二、“新小说”传播的域外新知
那么,清末的“新小说”究竟传播了哪些域外新知呢?实际上,我们从“新小说”的类型与名目即能窥见一斑。
彼时文坛出现了很多中国小说史上从未有过的一些新小说类型,诸如“政治小说”“社会小说”“哲理小说”“冒险小说”“航海小说”“科学小说”“侦探小说”“军事小说”“理想小说”“商业小说”“教育小说”“家庭小说”……,它们将政治立宪、域外奇闻、科学幻想、侦探推理、实业救国、婚姻自主、女权女学、教育改革等这些陌生而令人新奇的知识,源源不断地传输给中国读者,让读者大开眼界,以实现其开智、启蒙的预定目标。以下,择其荦荦大端者,略说一二。
先说政治小说。梁启超起初倡导“政治小说”,创办《新小说》,其目的“专在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厉其爱国精神”[3]。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整理本《新中国未来记》
如他在《新中国未来记》中说:“凡做一国大事,岂必定要靠着政府当道几个有权有势的人吗?你看自古英雄豪杰,那一个不是自己造出自己的位置来?就是一国的势力,一国的地位,也全靠一国的人民自己去造他,才能够得的;若一味望政府、望当道,政府、当道不肯做,自己便束手无策,坐以待毙了,岂不是自暴自弃,把人类的资格都辱没了吗?”[4]像这样的小说、这样的议论,显然旨在于激发、培养中国人的国家思想与爱国情怀。
又如1901年10月,林纾在其所译《黑奴吁天录》的跋语中声称:“今当变政之始,而吾书适成,人人既蠲弃故纸,勤求新学,则吾书虽俚浅,亦足为振作志气、爱国保种之一助。”[5]《经国美谈》出版后,有论者马上强调指出:“能读是书,其所得之结果,必能养其国家上之思想,世界上之感情。”[6]
对于以小说激发国人爱国思想的必要性,天僇生(即王钟麒)《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所说颇中肯綮:“夫欲救亡图存,非仅恃一二才士所能为也。必使爱国思想普及于最大多数之国民而后可。求其能普及而收速效者,莫小说若。”[7]

《清末民初小说理论资料》
一些新小说家对此也深有同感,如“晓耕”在《二十世纪新国民》开头就说:“看官,你道此书为何而作?因为我们中国百姓不晓得国家为何物,向来没有半点儿爱国的思想,专取家族主义。所以国家近来弄到这样衰败的地步,还不肯大家齐力,出来扶持扶持,只为肆口漫骂政府没中用,不晓得自己尽国民的义务。……作者所以编出这部小说来,给列位看看,借几位英雄豪杰的作为,给我百姓当个模范,使我百姓个个有爱国思想,扫除脱从前种种的陋习私见,如重造过人的模样,所以取名曰‘二十世纪新国民’。”[8]
可见,政治小说的著译,其主要宗旨就在于,唤醒国人的家国情感,激发国人的爱国主义精神。
次说冒险小说。成之(即吕思勉)在《小说丛话》中指出:“此种小说,中国向来无之,西人则甚好读之。如《鲁滨孙飘流记》等,其适例也。此种小说,所以西有而中无者,自缘西人注意于航海,而中国人则否……今既出现于译界,可藉以鼓励国民勇往之性质,而引起其世界之观念。”[9]
管达如《说小说》也认为:“若《鲁滨孙飘流记》之类是也,最足激发人民冒险进取之思想。中国近日,民之委靡,尤须以此种小说药之。”[10]
《鲁滨孙漂流记》由上海商务印书馆1906年出版,其广告云:“此书故泰西名构,振冒险之精神,勗争存之道力,直不啻探险家之教科书,不当仅作小说读。”
由于该小说译本面世后,反响甚大,上海商务印书馆又接着推出了《澳洲历险记》,其广告云:“小说写一十六龄童子抱殖民志,远迹澳洲,历种种危险劳苦,几濒于死,卒能坚忍激昂,于困厄中增长智识……想青年励志者,尤必以早观此编为快也。”
《冰天渔乐记》也是写少年历险,其广告云:“此书叙少年彼得以习航海事往北美洲历经险难,知识愈出,于冰天雪海中捕鲸猎兽,极困苦中能得至乐,读之令人神往,为青年炼骨丹,端推此种。”

《冰天渔乐记》
1906年5月上海广益书局也推出了《绝岛英雄》,编译者从龛在序言中说:“自海通以来,国民皆当有海事思想,故教育之始,必以有关海事者,使先系诸童子之脑蒂。无论为家庭,为学校,或间接,或直接,总宜扶植此海事思想……而童子之脑最易人者莫若小说,则欲诱掖使盎然于海事思想者,小说之效为尤捷也。英美不必言,我国方力图奋发,伸长海权,则任教育之责者,于此尤不可不加之意,余故亟译此书。其间波澜突兀,皆可惊可喜可泣可歌,洵足以振荡精神,扩张智略。”
1908年8月6日,北京《大同白话报》也开始连载《幻岛探险》,译者在小引中说,他鉴于中国“柔弱之风,日甚一日”,而“欧美商人远涉重洋,不怕路远艰难,都有冒险的性质”,觉得“我们大家何防学上一学”,所以译了《幻岛探险》这部小说,“好振起大家冒险精神”。
尽管冒险小说传播的知识,多半带有“虚幻”的性质,但是它们在思想观念上也的确有助于培养国人的“海事思想”与“冒险精神”。
再看科学小说。成之在《小说丛话》中说:“科学小说,此为近年之新产物,借小说以输进科学智识,亦杂文学也。较之纯文学,趣味诚少;然较之读科学书,则趣味浓深多矣。亦未始非输入智识之一种趣味教育也。”[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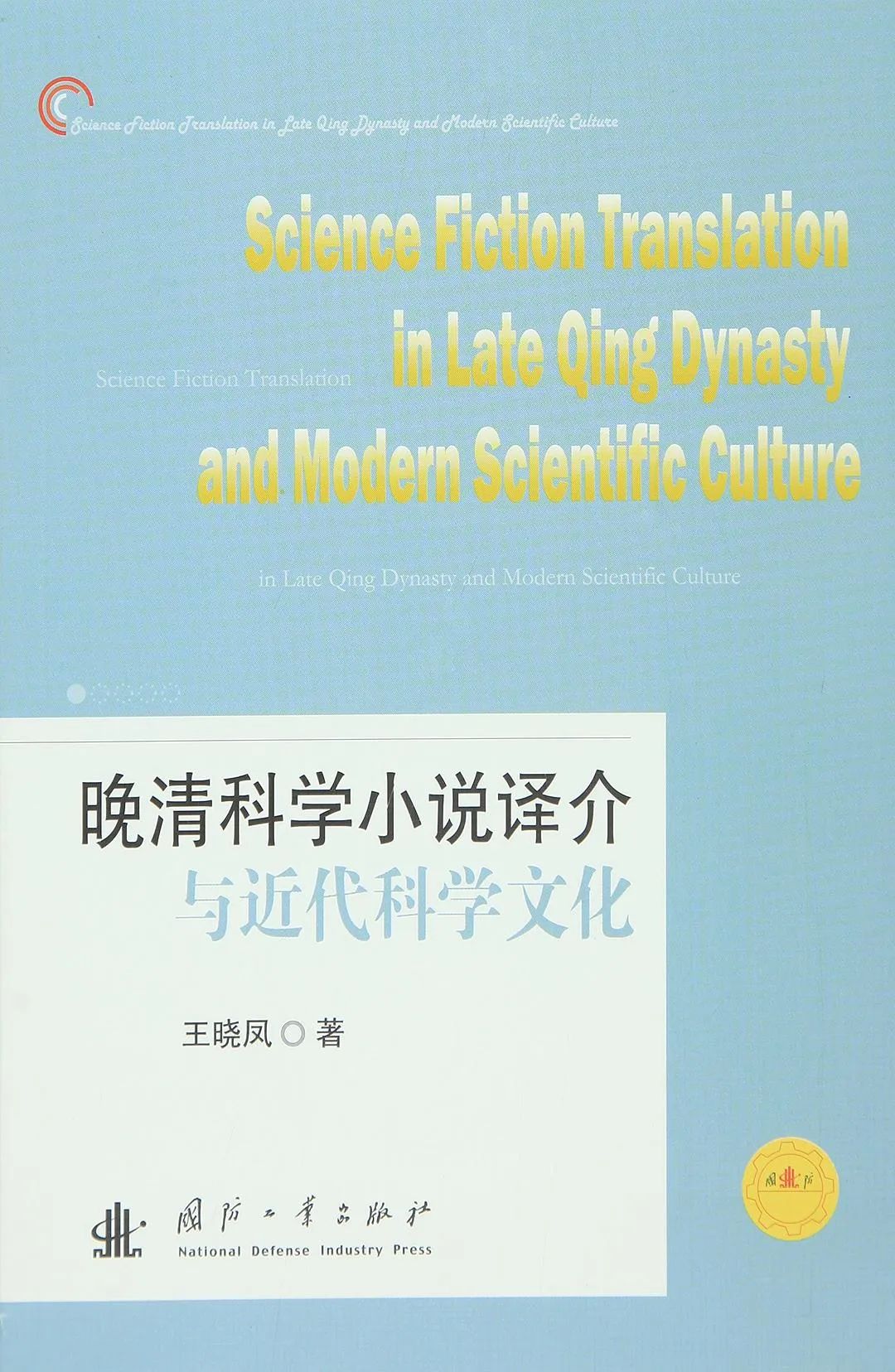
《晚清科学小说译介与近代科学文化》
科学小说的译介,反映出中国对西方工业文明、科学技术的推祟和对现代化的渴望。梁启超在《新小说》杂志专门设置了“科学小说”栏目,“专借小说以发明哲学及格致学,其取材皆出于译本”[12]。
1903年8月包天笑在《铁世界·译余赘言》中云:“科学小说者,文明世界之先导也。世有不喜科学书,而未有不喜科学小说者,则其输入文明思想,最为敏捷。”
1903年10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空中飞艇》,译者“海天独啸子”在书首“弁言”中也强调:“我国今日输入西欧之学潮,新书新籍翻译印刷者汗牛充栋,苟欲其事半功倍、全国普及乎?请自科学小说始。”
可见,新小说家大都希望借科学小说的翻译来普及科学知识。哪怕翻译、著述的是科幻小说,带有大量的幻想成分,他们也认为可以在思想上启迪民智,促进文明进步。
如1903年11月,鲁迅翻译的《月界旅行》,在日本东京进化社出版,在《辨言》中他就发表了借翻译科幻小说使国人“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的观点。徐念慈不仅创作了科幻小说《新法螺先生谭》,而且明确指出:“月球之旅行、世界之末日、地心海底之旅行,日新不已,皆本科学之理想,超越自然,而促其进化者也。”[13]
另外,当时普及科学知识的,不仅是科学小说或科幻小说,那些标明为医学小说(或称卫生小说)、冒险小说、侦探小说的,实际上也都涉及了大量的科学知识,譬如医学、天文学、地理学、植物学、动力学、热力学、电学等,里边充斥着大量的新名词、新概念。
以医学小说为例,1908年6月28日《绍兴医药学报》第1期开始连载《医生本草》,该小说“写近来各科之现状,俾病家如医生立方选药然,而有所择焉”。
1909年8月30日,该报又开始连载《医林外史》,篇首云:“《医林外史》,以科学为经,社会为纬,两两组织,暗寓惩劝……为改良医社,灌输文明,并欲开通风气,使一般社会均有普通医学之智识,故凡卫生学、医药学、奇症治疗、简便良方,类皆采取古今典籍,并东西医博士之讲义。中西汇通,集思广益,登者确有来历,与寻常小说任意捏造者不同。”

《中国近代小说大系》
1909年1月2日,上海《时报》,刊载“廿世纪新创卫生小说《医界镜》出版”广告:“迩来各种小说皆备,惟关于卫生医界者尚付缺如。儒林医隐为儒、医两界名手,竭数年之力,易五次之稿,著成小说,以冀医界改良。且中有许多妙方,搜罗完备,于消闲之中,兼得卫生之益。凡官商学界欲讲求卫生者,不可不看。”
另外,上海《时报》还在1909年11月15日载《美人痨》、11月21日载《黑死病》等,均标“医学小说”,其意亦均在于普及医学知识。
至于侦探小说,则以案件发生和推理侦破过程为主要描写对象,其所展示的与中国传统公案小说不同的逻辑推理及科学断案过程,自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人进行了最初的现代法制与科学观念的启蒙。

《吴趼人全集》
如吴趼人在《中国侦探案·弁言》中即指出,读者为何喜爱购读侦探小说呢?“访诸一般读侦探案者,则曰:侦探手段之敏捷也,思想之神奇也,科学之精进也。吾国之昏官、聩官、糊涂官所梦想不到者也。吾读之,聊以快吾心。或又曰:吾国无侦探之学,无侦探之役,译此者正以输入文明。而吾国官吏徒意气用事,刑讯是尚,语以侦探,彼且瞠目结舌,不解云何。”[14]
后来,半侬在《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跋》(上海中华书局1916年出版)中也说:“柯氏此书,虽非正式的教科书,实隐隐有教科书的编法……言其于植物学则精于辨别各种毒性之植物,于地质学则精于辨别各种泥土之颜色,于化学则精邃,于解剖学则缜密,于纪载罪恶之学则博赅,于本国法律则纯熟。即言凡此种种知识,无一非为侦探者所可或缺也。”[15]
还有历史小说,明清时期称为历史演义,此虽为中国古代小说的一大宗,但以演义体演述国外历史的小说,却始自近代。
梁启超在《新小说》创刊时曾列举一些拟译著的外国历史小说,如《罗马史演义》,他认为“罗马为古代世界文明之中心点”,“其全盛也,事事足为后世法,其就衰也,事事足为后世戒”;《十九世纪演义》,他指出“欲知今日各文明国之所以成立,莫要于读十九世纪史矣”;《自由钟》,“读之使人爱国自立之念油然而生”;《洪水祸》“以极浅显之笔,发明卢梭、孟德斯鸠诸哲之学理,尤足发人深省”;《东欧女豪杰》“以最爱自由之人,而生于专制最烈之国,流万数千志士之血,以求易将来之幸福,至今未成,而其志不衰,其势且日增月盛,有加无已。中国爱国之士,各宜奉此为枕中鸿秘者也”。[16]
可见,以小说来演绎、传播西方历史知识,是希望从中获取有益的鉴戒,并以此激发国人爱国自立的精神。

《梁启超全集》
1903年4月30日,杭州上贤斋出版《万国演义》,沈惟贤序即说:“今学界日新,志士发愤,咸欲纵观欧亚大势,考其政教代兴之机,富强竞争之界;即横塾之师,用以发明事理,启牖来学,亦于是乎汲汲焉。”他不仅强调学习外国历史的意义,还指出可用历史小说来开启童蒙。
1908年8月,上海改良小说社出版《新列国志》,书内标“西史小说”,作者序云:“西洋史之足备我人考镜者,尤以近世史为最要,而近世史中,事变尤杂,记忆尤难,非得如《列国志》一书,为之发聋启聩,以牖童蒙,其何能省记忆力而纯熟史事乎?且何能知西洋近世之进化日异而月新乎?”
因为有此认识,所以他在“课徒之余,爰举近百年西洋各国之由野而文、由虚而实者,一一皆以浅近文理组织之,间下己意,与我国史事对勘,无非欲触类引伸,使童子有左右逢源之乐也”。
与历史小说相近的,还有以军事斗争为题材的军事小说。这类小说对军事斗争经验的描述,自然也不乏借鉴意义。
如1904年林纾在其所译《利俾瑟战血余腥记》序言中即说:“是书果能遍使吾华之人读之,则军行实状,已洞然胸中,进退作止,均有程限,快枪急弹之中,应抵应避,咸蓄成算,或不至于触敌即馁,见危辄奔,则是书用代兵书读之,亦奚不可者?”[17]

《林纾集》
1904年上海小说林社出版《军役奇谈》,译者陶叫旦指出此书“搜辑军事界之机括秘要,一片谈屑,可作兵家书读,可作军事史观。著者为英国文豪,译者复按比中国时势发挥之,洵军事界唯一之奇书也”。
1909年3月,上海中国图书公司出版《英德战争未来一记》,标“军事小说”,英国卫梨雅原著,东海觉我(徐念慈)译述。书首“绪言”云:“是书体裁虽为小说,而于地利上、战术上,其所记述实有非常之价值者也。”
1910年7月,上海东亚译书会出版《破天荒》,标“军事小说”,德国冒京著,徐凤书、唐人杰合译,声称“欲知现今及将来军事上、交通上、学术上之大变革,可于此中探索得之”。这些声明就旨在激发受众的阅读期待。
另外,晚清还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家庭小说。这类小说多以家庭婚姻生活为题材,侧重女性启蒙。如1906年小说林社出版的《闺中剑》,署“亚东破佛”撰,其卷首“弁言”云,“是书注意又重在开通妇人、稚子之智识”,“侧重女学”,并“独重算术”,附及“胎教之说”“卫生之学”。
1909年上海蒋春记书庄出版《情天劫》,署“东亚寄生撰”,封面题“文明新小说自由结婚”,小说开头即云:“夫妇之间,婚配之际,为生命始基,万福本原。一有不慎,则家室之内,勃谿时闻,必至门庭萧散。内而亲戚族党,外而国家社会,种种障碍,皆从此起,中国于夫妇一道,最为郑重,制嫁娶,正姓氏,通媒妁,用意立法,可算精密完美。乃夫妇反目,十有八九。推其原故,大半由于择配的时候,男女素昧平生,翁婿未经谋而,姑媳漠不相识,但凭媒人一面之词,便将亲事定下。无怪诟谇交谪,难期静好。欲矫其弊,舍自由结婚以外,别无他法。但中国礼节,内外隔阂,男女不通闻问,结婚万难自由,是可断言的。即有一二智识开通的子弟,知道自由结婚的好处,他的父母又生出无数的阻力,甚至将这爱情深挚的一对男女,生生拆开。所以近时便生出一件为情而死的故事来了。”

《情天劫》
作者由反思传统婚姻礼制存在的问题入手,自然引出小说所叙的一桩由“父母之命”干涉婚姻自由制造的悲剧;在小说结尾,他又出面说道:“合葬之日,有许多学堂里的学生,及有志的闺秀,无论远近,赶来送葬,江苏合省就将这故事传为美谈,从此风气一变,竟将旧日婚制改良了许多。将来自由结婚的制度能够行开,这余光中和史湘纹,岂不要算是自由结婚的开山始祖么?”
如此这般,小说倡导的“自由结婚”的思想便得到了充分的彰显与传播。
值得注意的是,晚清还有一些以外国工商界传奇人物故事为内容的小说,旨在倡导实业救国。如1902年杭州《杭州白话报》第二年第一期开始连载《三大陶工故事》,作者“白过日子人”在小说篇首云:“这桩故事从英国大名家斯迈尔斯做的一部《自助论》译出来的。这三个陶工为什么能够有这样大名呢?说出来甚是有理。诸君,请看现在西洋来的磁器,何等细巧,何等光滑,而且花样何等耀目,那个看了不欢喜呢?诸君,难道西洋人都比我们聪明么?况且中国的磁器,本来还狠有名呢,为什么到了现在不如从前了?咳!岂不又要被外国人夺一种生意去么?诸君,要晓得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提起精神,坚起心思,难道我们的制造,不好想个法儿胜过外人么?若说怕受辛苦,怕费工夫,便灰了念头,随便什么事不成了。我现在且把这三个陶工的事迹说给诸君做个榜样。”
1907年《农工商报》创刊于广州,不久改名《广东劝业报》,该报专设“讲古仔”栏目,旨在“将农工商中之本事人,讲明其发财原故,俾睇报者兴起其勇往之心。”

《晚清小说期刊辑存》
自1908年开始连载《制造瓷器大家巴律西小传》《美国大北铁路公司发起人占士比儿小传》《著名船商特琼司小传》《兽肉霸王亚模小传》《德国农业发达史演义》等小说,用粤语讲述欧美一些商业巨子创业发家的故事,以之激励国人开拓进取,发展工商,立国富民。
综上所述,可见清末新小说家通过译著各种类型的小说,向社会传播了在他们看来为民众所需的各种域外新知,以期开启民智,实现新民救国的目的。

三、“新小说”家传播域外新知的主要方式
“新小说”家们往往以启蒙者的身份,纷纷通过译述域外小说、自撰新小说来传播域外新知。其传播域外新知的主要方式有如下四种。
其一,有选择地译述域外小说,成为传输域外新知的捷径。
管达如在《说小说》中说:“生于今日,而无世界之智识,其将何以自存哉?欲求世界之智识,其道多端,而多读译本小说,使外国社会之情状,不知不觉,而映入于吾人之意识区域中,实最便之方法也。”[18]
天僇生《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也说:“宜选择事实之于国事有关者,而译之著之。”[19]
黄世仲《小说风尚之进步以翻译说部为风气之先》更明确地指出:“译本小说者,其真社会之导师哉!一切科学、地理、种族、政治、风俗、艳情、义侠、侦探,吾国未有此瀹智灵丹者,先以译本诱其脑筋;吾国著作家于是乎观社会之现情,审风气之趋势,起而挺笔研墨以继其后。观此而知新风过渡之有由矣。”[20]这些看法代表了当时人们的共识。

《黄世仲革命生涯和小说生涯考论》
例如,1898年梁启超基于政治改革的需要,特别看重政治小说,不仅带头翻译了日本政治小说《佳人奇遇》,还专门发表了《译印政治小说序》,强调“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因此“今特采外国名儒所撰述,而有关切于今日中国时局者,次第译之,附于报末,爱国之士,或庶览焉”[21]。
受其影响,周逵译述了《经国美谈》、郑贯公编译了政治小说《摩西传》、冯自由编译了《贞德传》(一名《女子救国美谈》)、忧亚子译述了《累卵东洋》等,梁启超称这些小说“以稗官之异才,写政界之大势”[22],“不徒小道可观,实国民政治思想发达之一助也”[23]。
而在翻译域外小说名著的过程中,译者常常会将所译小说与中国的实际情况关联起来,即兴发表一番自己的感想。
如1901年6月20日,《杭州白话报》连载“独头山人”翻译的《波兰国的故事》,译者在序中说:“我因为这件事体,同我们中国的情形有几分相像,所以把波兰灭国的故事告诉你们。要晓得你们再不明白,再不振作,恐怕别人家把我们的堂堂中国当作波兰看待。孟夫子说的,家必自毁,然后人毁之;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便是这个道理。”

《杭州白话报》
这是利用序言阐述翻译意图,译者有意将所译小说的内容与中国的政治现状加以对照,揭示该小说对中国人会有什么样的启发和教训。而最常见的,则是在所译小说的起首开宗明义,或是在篇末卒章显志。
如《杭州白话报》1901年11月5日第一年第十五期开始连载《菲律宾民党起义记》,作者林獬在篇首发表议论:“这部书名做《非律宾民党起义记》。非律宾是亚洲一个小岛,民党是一大股国民,个个相爱如同兄弟,结成一党……列位,你且想想,我们中国这辈人,不懂那合群的道理,要想像这非律宾民党,真正是万分艰难的。闲话休谈,如今我们演书人的意思,是要请你列位看看这非律宾不外一个小岛,尚且不肯受人压制,要闹自立,那比非律宾地大的国度,也好挺着肚皮谋振作了。”
这是寄希望于国人看了小说后,能学习非律宾民党同心协力反抗压迫、谋求自立的精神,好振兴自己的国家。
同一期刊载的《俄土战记》,其译者则在篇末发表议论:“如今土耳其且不要去管他,列位,我们都是中国人,照现在的景像比较起来,与土耳其也相去不远了。但是大家若果有志气,还可以救得转来。唉!我们演书的,虽然有了热心,究竟一个人济不得事,不晓得你们列位看了书后,到底是想把中国变做轰轰烈烈与各国争雄呢,还是仍旧听着他不痛不痒同这土耳其长病久病,始终没有药救呢?”这自然也是希望中国人能从土耳其的惨败中汲取教训,不要蹈其覆辙。
其二,新小说家们还常在翻译欧美小说的过程中加以删改、增衍,以使该小说更有助于警醒国人,启迪民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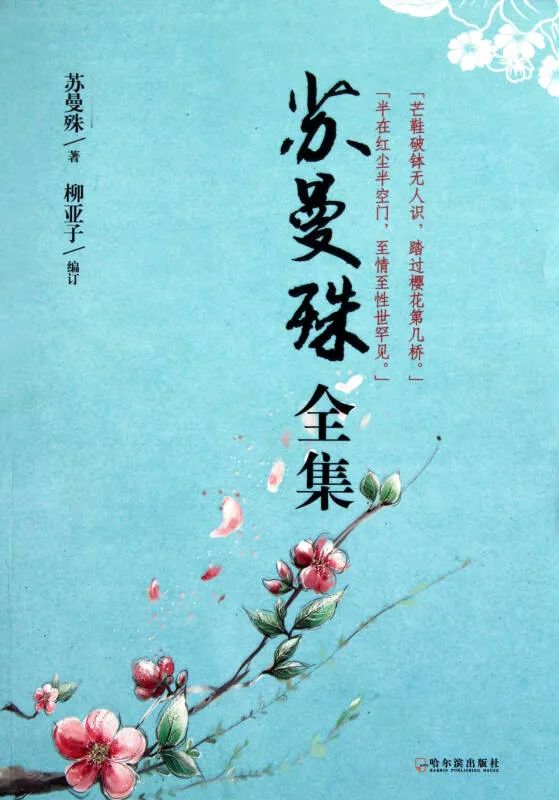
《苏曼殊全集》
如1903年10月8日,苏曼殊以《惨社会》之名在《国民日日报》上连载其翻译的《悲惨世界》,次年出版单行本更名《惨世界》。
不过,《惨世界》除了故事开头主人公因偷窃获罪,释放后无家可归被主教收留,反而再行偷窃等情节与原著一致外,后面任意增写了大量原著不曾有的情节,如小说中写一个姓明名白字男德的人,天生侠义,从报上看到华贱的悲惨遭遇,便代打不平,深夜持刀入狱,救出华贱,不料华贱却心生歹意,用刀捅伤男德,抢走其银两;后来,男德又杀死了欺诈百姓的恶霸满周苟,可被他拯救的女孩不但不感激,反而想乘机将男德交给官府,以得到五万赏银。
这些情节,包括书中人名,全是曼殊自创,从金华贱(华人卑贱)、范桶(饭桶)、葛土虫(割土虫)、满周苟(满洲狗)等一干人名,就可以看出曼殊对华人自轻自贱的痛恨,对满清政府割地赔款的郁愤,对满洲政府走狗的不屑,对国人愚昧无知的鄙薄。
另外,《惨世界》所涉及的地点,也是在法国与中国自由穿梭,法地巴黎、土伦、无赖村、色利栈、死脉路、忌利炉街,中国的“尚海”(上海)等,均充满寓意与暗示。明男德解救金华贱而反被劫杀的事件,暗示的就是革命者不被愚民理解的苦衷与沉痛。可见,《惨世界》名为翻译,实为译著,其借题发挥以开启愚蒙、改造国民劣根性的意图是一目了然的。

苏曼殊译《悲惨世界》
其三,新小说家们还喜欢选取外国人物故事作为小说题材内容,通过演绎外国人的故事来开导中国人。
如《杭州白话报》1903年第1至3期连载《日本侠尼传》,署“黄海锋郎演”。其篇首云:“列位,试掉头东望,那一字长蛇的三岛,可不是如火如茶、如花如锦的兴旺起来吗?回想从前那种内政不修、外邦欺侮的情形,却和中国现在相仿。恁么日本骤兴,中国愈弱,这莫非是古语说的天命枚归吗?唉!不是,不是。这多是他们国民的头颅掉换得来,志士的热血浇灌出来的呀。列位,试读日本维新史,便知那般维新豪杰、开国元勋,从前多是读书的、行医的、经商的、尤业的,无权无力,困苦流离,所依赖的,全是一条爱国的热肠、满腔忧时的血泪,人人都抱顶天立地的气概,个个都有成仁取义的精神。一人死,十人继;十人死,百人继。民智如此,民气如此,所以能把一个鼾沉沉的国度,变成一个簇新新的国度呢。这不算奇,还有那绣阁名姝、青楼丽质,脑筋里也有国家思想,也有国民精神。或是慷慨忧时,或是保护志士,那一般娇滴滴的闺秀儿,都想做一番烈轰轰的新事业。这还不算奇,更有一个出生入死、爱国忘身的巾帼英雄、佛门弟子咧。我且把他的事业,慢慢演来,愿我同胞,啼听谛听。”
作者在小说开头便将他创作《日本侠尼传》的意图讲得明明白白,也即有意借日本侠尼“出生入死、爱国忘身”的传奇故事激发中国人的“国家思想”与“国民精神”。
又如横滨《新小说》1903年1月13日第三号刊载《东欧女豪杰》第三回,该回中晏德烈云:“你说君权神授,你可说出什么凭据来呢?那个‘神’字,原是野蛮世界拿出来哄著愚人的话,如今科学大明,这些荒诞无稽的谬说那里还能立足呢?不通的政治家说君权神授,正如那宗教家说什么天父、说什么天使的一般见识,如今他们的迷信谬论都被人攻了去,再不能够辩护过来了,你还想靠著神权的旧议论,替那些民贼提出‘天子’两个字恐吓人,哄骗人,你也太不识时务了!”

《新小说》
这实际上是作者有意化身为人物,借小说人物的言谈来驳斥君权神授的谬论,以启迪读者。评点者就指出:“本回补叙德烈出身来历,内中在大学论政治原理,驳斥顽固教习一段,凡数千言,洋洋洒洒,将民权大义发挥殆无余蕴,又征引历史,上下千古,读此不啻读一部《民约论》也。”[24]
其四,新小说家们还喜欢在自撰的本土题材的小说中涉笔域外风情,叙述笔下人物在异域的见闻或历险,书写先进的科技文化等内容,以开拓国人的知识视野。
如吴趼人虽然未曾游历海外,但他对西洋科技文明也是耳濡目染。其所作《新石头记》,涉笔机器人、司时器、制冰机、脏腑镜、验血镜、验骨镜、助听筒、助明镜、千里镜、无线电话以及绕地球飞行的飞车、地下通行的隧车、水下行驶的猎艇等,林林总总,令人叹为观止,充分反映了作者渴望借助先进的科技文明实现富国强兵的梦想。
徐念慈所撰《新法螺先生谭》则生动地叙述了新法螺先生漫游月球、火星、金星等外星球的新奇见闻。

《中国科学幻想文学史》
黄世仲也在小说《宦海潮》中描述张任磐出使美国,参观博物院,考求西洋工艺的见闻感受。如张氏在博物院“暗忖中国若有此等堂院,实增人博物见识不少”;见到美国南北战争所用战船时又想:“南北美之战,至今不过数十年,战具进步已日新月异。若中国现时还始创海军,那里能够与人对敌?”[25]在公署听人说留声机辨冤的故事,又感慨道:“今有留声机能报出案情,我们中国人那里见过?可见西人考求技艺,没一件不精的了!”
谭荔烷在其所著“冒险小说”《片帆影》的开头即云:“哥仑航海,始获美洲,遂成今日之繁华新世界。足迹遍寰宇,眼界空古今,故西人富有一种冒险的性质。海外奇观,必有足多者焉。吾语吾同胞,为述《片帆影》。”
该小说写黄汉生冒险出洋游历,“先到香港,寓于某栈”,偶遇黄兴,黄对之曰:“吾国人囿于浅见,出门百里,家常惘惘,是岂足与语环瀛之大哉?某虽经游不远,然就所历之南洋群岛而论,觉山岳之出产,洋海之奇幻,海岛上居人之自由逸乐,已迥非惨受专制之种族所得而问也。况乎为吾足所未历,目所未观者?吾更何能揭彼情状哉?”
于是深受鼓舞,只身乘船赶往“新嘉坡”,此后不久,又“附轮入缅”,不料遭遇飓风,漂至一海岛,“俯视山岩,现一皮壳,如龟背模样。生检视之,有明光光的宝珠数粒,大如鸽卵”,因他将随身所带面包饼干给予岛民,又获“大珠二颗”,后来脱险,“复抵新嘉坡后,将珠贩卖,骤变巨富,开张商店。即命亲信人汇单返里,挈家同往新嘉坡之山巴(即园口)居住”。
总之,新小说家们主要就是通过上述这些方式来传播域外新知,广纳先进文明,从异域风光、风土人情,到先进的科学技术与制度文明,乃至科学幻想、政治乌托邦等,均络绎于他们的笔端。

《片帆影》
这些丰富多彩的域外新知识,对于已在“严夷夏之大防”的社会里度过了数千年的中国人来说,无异于打开了一扇通向外部世界、感受西洋文明新风的窗口,吸引了大量趋时好新的读者。

四、“新小说”传播域外新知的影响
就“新小说”传播域外新知的影响来说,当时那些五花八门的小说“体裁”,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启迪了民智。
如上文所述,政治小说能唤醒中国人的家国情感,冒险小说可以激发中国人的冒险精神,科学小说有效地普及了科学知识,侦探小说则启迪了中国人的司法意识,历史小说增进了中国人对西方历史的了解,而军事小说也可以让人从中汲取一定的军事斗争经验,家庭小说对女学与婚姻自由的倡导也有助于女权意识的培养,至于描写工商业的小说也可以对实业救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如孙宝瑄1903年6月1日在《忘山庐日记》中就这样总结他读新小说的心得:“观西人政治小说,可以悟政治原理;观科学小说,可以通种种格物原理;观包探小说,可以觇西国人情土俗及其居心之险诈诡变,有非我国所能及者。故观我国小说,不过排遣而己;观西人小说,大有助于学问也。”[26]

《忘山庐日记》
“新小说”对域外新知的传播,不仅拓新了中国人的知识视野与知识结构,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的政治思想观念。在“新小说”兴起前,中国人多半缺乏国家思想与民族意识,“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之弊,深中于人心”,“有能富我者,吾愿为之吮痈;有能贵我者,吾愿为之叩头,其来历如何,岂必问也”,以致英法“联军入北京,而顺民之旗,户户高悬”[27]。
而“新小说”则“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厉其爱国精神”[28]为己任,以传播域外新知“谋开吾民之智慧 ”[29],因此不仅使爱国保种的意识逐渐深入人心,而且使“专制”“自由”“平等”“民主”“革命”等观念不胫而走,开始喧腾众口。
例如,1903年,“醒狮”读了《黑奴吁天录》,赋诗慨叹:“专制心雄压万夫,自由平等理全无。依微黄种前途事,岂独伤心在黑奴?”[30]金一也赋诗云:“花旗南北战云收,十万奴军唱自由。轮到黄人今第二,鸡栏豚栅也低头。”[31]他们从美国黑奴惨遭奴役、为自由而战的命运播迁联想到中国人的前途,由此表达了中国人反对专制、争取自由平等的愿望。
1905年,包天笑在《<身毒叛乱记>序》中说:“今日平等、自由之谭嚣国中矣,倾心彼族者,方以为白种之民德高越地球,足为世界文明之导线。”[32]可见,“平等、自由”等观念已借“新小说”的传播而尽人皆知。
1907年,黄摩西《<小说林>发刊词》也说:“狭斜抛心缔约,辄神游于亚猛、亨利之间;屠沽察睫竞才,常锐身以福尔、马丁为任;摹仿文明形式,花圈雪服,贺自由之结婚;崇拜虚无党员,炸弹快枪,惊暗杀之手段:小说之影响于社会者又如是。”[33]这说明“新小说”对中国人的影响已达于日常行为层面。

《小说林》创刊号目录
1908年,燕南尚生在《新评水浒传·叙》中也说自己“年至弱冠,稍阅译本新书,而知一国家也,有专制君主国、立宪君主国、立宪民主国之分;又稍知有天赋人权、物竞天择等学说”[34]。
可以说,影响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一些重要的新概念、新思想,如“变法”“改良”“立宪”“专制”“平等”“自由”“人权”“民主”“共和”“革命”“女权”“科学”等,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新小说”的传播,才逐渐被普罗大众所接受,并进而影响其思想和行为的。
“新小说”对域外新知的传播,还对中国人的精气神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当时,有不少读者就曾写下自己阅读某部“新小说”而产生的精神变化。
如1900年12月31日,上海《中外日报》“专件”部分刊载“《经国美谈》书后”,署“毗陵周君雪樵来稿”云:“惟《经国美谈》为日本前使中国矢野文雄所著,纪其起讫,最为详尽。仆得而读之,觉志气为之激昂,神采为之飞舞,盖日本侠士尊攘之先声也。”可见,《经国美谈》有力地激发了他的英雄气与爱国情。

《黑奴吁天录》
1904年,《觉民》第七期刊载了灵石的《读<黑奴吁天录>》,灵石说他“于灯下读之,涕泪汍澜,不可仰视,孱弱之躯,不觉精神为之一振,且读且泣,且泣且读,穷三鼓不能成寐”,他觉得:“此书不独为黑人全种之代表,并可为全地球国之受制于异种人之代表也。我黄人读之,岂仅为沈醉梦中之一警钟已耶?”
这种刻骨铭心的阅读体验以及由此激发的强烈的爱国保种意识,使他情不自禁地发出这样的呼吁:“我读《吁天录》,以哭黑人之泪哭我黄人,以黑人已往之境,哭我黄人之现在,我欲黄人家家置一《吁天录》。”[35]
1905年2月21日,《新小说》第十七号刊载了“松岑”(即金松岑)的新小说读后感:“吾读《十五小豪杰》而祟拜焉,吾安得国民人人如俄敦、武安之少年老成,冒险独立,建新共和制于南极也?吾读《少年军》而崇拜焉,吾安得国民人人如南美、意大利、法兰西童子之热心爱国,牺牲生命,百战以退虎狼之强敌也?吾读《秘密使者》而崇拜焉,吾安得国民人人如苏朗笏、那贞之勇往进取,夏理夫、傅良温之从容活泼,以探西伯利亚之军事也?吾读《八十日环游记》而崇拜焉,吾安得国民人人如福格之强忍卓绝,以二万金镑,博一千九百二十点钟行程之名誉也?吾读《海底旅行》《铁世界》而亦崇拜焉,使吾国民而皆有李梦之科学、忍毗之艺术,中国国民之伟大力可想也。吾读《东欧女豪杰》《无名之英雄》而更崇拜焉,使吾国民而皆如苏菲亚、亚晏德之奔走党事,次安、绛灵之运动革命,汉族之光复,其在拉丁、斯拉夫族之上也。吾又读《黑奴吁天录》而悲焉,谓吾国民未来之小影,恐不为哲尔治、意里赛而为汤姆也……其他政治、外交〔去年《外交报》,译英文多佳者〕、法律、侦探、社会诸小说,皆必有大影响、潜势力于将来之社会无可疑焉。”[36]
松岑不仅读“新小说”而生崇拜之心,而且热切地希望中国人也能像那些小说中的主人公那样,发扬“冒险独立”“热心爱国”“勇往进取”“从容活泼”“强忍卓绝”等精神,拥有“科学”“艺术”之素养,敢于“奔走党事”“运动革命”,从而使“汉族之光复”的梦想能够早日实现。
“新小说”对域外新知的传播,不仅启迪了民智、改变了民心民意,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

《洪秀全演义》
以黄世仲为例,其所作《洪秀全演义》《宦海升沉录》《宦海潮》《大马扁》等,即以抨击封建专制、反对“君主立宪”、传播域外文明、助推民主革命为宗旨,曾在清末畅销一时,影响甚巨。
冯秋雪曾回忆说:“《洪秀全演义》一书发表之后,省港澳门风行一时,几于家喻户晓,在鼓吹民族革命作用上,可与甲辰间东京出版之《太平天国战史》,后先辉映”[37]。罗香林也说:“尝闻于陈树人、高剑父诸公及先君幼山公、罗群冀兄,称颂黄世仲氏于港主持《公益报》《少年报》……于穗则《南越报》等报刊以宣传革命外,兼撰小说互为推广,灌输种族革命、民主主义以感导国民,同反满清政权于南中国,收效至巨。”[38]
另外,“新小说”在思想启蒙上也沾溉了此后发生的新文化运动。如前文所述,梁启超倡导的“小说界革命”与“新小说”传播的域外新知识,早在新文化运动发生前,就已对“民主”与“科学”等思想进行了广泛的传播,因此实可谓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民主”与“科学”之声的前奏。
而从文学发展的角度来看,“新小说”对域外新知的传输,不仅赋予了中国小说以现代性的内涵,拓新了小说的题材领域与叙事艺术,带给了读者以种种陌生化的新奇感受,从而有效地革新了传统的小说观念,促进了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型,而且也对“五四”文学革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域外小说集》
周作人曾说,当年他和鲁迅读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颇觉震撼,认为梁氏“主张以文学来感化社会,振兴民族精神,用后来的熟语来说,可以说是属于为人生的艺术这一派的”[39]。而鲁迅弃医从文,想借小说著译来改造国民性,并翻译出版《域外小说集》,也无不透出梁启超思想的折光。
钱玄同更指出,“梁任公先生实为近来创造新文学之一人”,“鄙意论现代文学之革新,必数及梁先生”[40]。
至于创造社的陶晶孙,在谈及苏曼殊的“新小说”时则说:“在这个雅人办的五四运动之前,以老的形式始创近世罗曼主义文艺者,就是曼殊,而曼殊的文艺,跳了一个大的间隔,接上创造社罗曼主义运动。”[41]
因此,“新小说”通过域外新知的传播,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启迪了中国人的民智民心,助推了中国近代的社会变革与文学转型,沾溉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了现代文学革命的先声。
注释:
[1]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第一号,1902年11月。
[2] 载《小说月报》第七卷第一号,1916年。
[3] 梁启超:《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新民丛报》第十四号,1902年。
[4]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十七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9页。
[5] 陈平原、夏晓虹编:《清末民初小说理论资料》,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53页。
[6] 见《中外日报》1902年11月20日刊《经国美谈前后编》广告。
[7] 载《月月小说》第一年第九号“论说”栏目,1907年。
[8] 载宁波《朔望报》第一期,1911年7月10日。
[9] 载《中华小说界》第一年第五期,1914年。
[10] 载《小说月报》第三卷第五号,1912年。
[11] 载《中华小说界》第一年第五期,1914年。
[12] 梁启超:《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新民丛报》第十四号,1902年。
[13] 觉我(徐念慈):《小说林缘起》,《小说林》第一期,1907年。
[14] 吴趼人《中国侦探案》,上海:广智书局1906年版,第3页。
[15] 陈平原、夏晓虹编《清末民初小说理论资料》,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527页。
[16] 梁启超《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新民丛报》第十四号,1902年。
[17] [法]阿猛查德著,林纾、曾宗巩译《利俾瑟战血余腥记》,上海:商务印书馆1904年版,第2页。
[18] 载《小说月报》第三卷第九号“论说”栏目,1912年。
[19] 载《月月小说》第一年第九号“论说”栏目,1907年。
[20] 载《中外小说林》第二年第四期,1908年。
[21] 载《清议报》第一册,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1898年12月23日)。
[22] 梁启超:《<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载《清议报》第一百册,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1901年12月21日)。
[23] 横滨《清议报》1901年12月21日刊载“政治小说《佳人奇遇》《经国美谈》合刻”广告。
[24] 见横滨《新民丛报》1903年1月13日刊载“《新小说》第三号要目”。
[25] 黄世仲《宦海潮》,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35-136页。
[26]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762页。
[27] 梁启超:《新民说》,《梁启超全集》第二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547-548页。
[28] 梁启超:《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新民丛报》第十四号,1902年。
[29] 邱炜萲:《小说与民智之关系》,陈平原、夏晓虹编《清末民初小说理论资料》,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56页。
[30] 载《新民丛报》第31号,第106页,1903年。
[31] 金一:《读<黑奴吁天录>》,《醒狮》第1期,1905年。
[32] 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93页。
[33] 载《小说林》,第1期,1907年。
[34] 朱一玄、刘毓忱编:《水浒传资料汇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44页。
[35] 载《觉民》第七期,1904年,第29--31页。
[36] 松岑:《论写情小说于新社会之关系》,《新小说》第十七号,1905年。
[37] 冯秋雪:《辛亥前后同盟会在港穗新闻界活动杂忆》,文见方志强《黄世仲大传》,香港:夏菲尔国际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589页。
[38] 罗香林:《乙堂劄记》,引自郭天祥《黄世钟年谱长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35页。
[39] 周作人:《关于鲁迅之二》 ,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25页。
[40] 钱玄同:《通信·寄独秀》,《新青年》第3卷第1号,1917年3月。
[41] 陶晶孙:《急忙谈三句曼殊》,《牛骨集》,上海:太平书局1944年版,第8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