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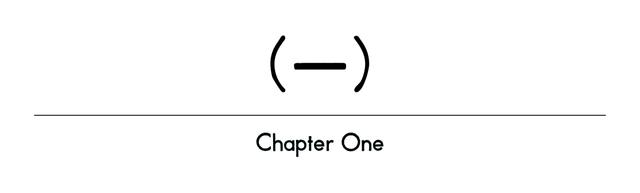
酆都乌鹊门外,老槐树上挂着一个人,麻绳被绷得极紧,明明瘦得麻秆儿似的。眼睛闭着,吐着殷红的舌头,脸白得像沾满了面粉。
一群青白黑黄的鸟雀,围在树下喧闹起来:
「又挂一个吗?」
「嗯。」
说话的分明是人!穿黄衣服的「黄雀」以手遮日,望了望瓦蓝色的太阳,日头挂在高耸的女墙上。戌正,酆都的早高峰 —— 和阳间是刚好相反的。
最繁忙的时刻,老文手里的活当然不能停,给面饼抹上糖稀,沾上油芝麻,啪叽一下,拍在猪肚子大的炉壁,很快烤出面与糖的焦香。
等他这口的魂儿们,已然排起了长队。这是一群老实的企鹅,又不肯错过那边的热闹,都朝对过望去。
树下的人更稠了,像粥。

「为什么挂?」
「哼!等投胎的呀。等了 36 年,着急要号,叫狐狸埂的人骗了。诸位想,狐狸埂的都是些什么东西?都是些割腰子的主呀。有个叫王德发的小赤佬,给他一张假票,同他讲是特殊渠道弄来的。他也是傻,居然相信。拿了票,请三日豆腐饭,把钞票花光光。揣着假票去报道,酆都的门都没让他进。他不服气,天天像根桩子在大门外面立,劝也劝勿听。就这样僵持不知道多少晨光,昨天下半日,一位公爷说了句重话。他大闹起来,教夜叉插透了腿,一时想不开,就挂了。」
细看树上的鬼,腘窝上三寸的裤腿,果然贯穿一个窟窿。
「说什么了教他这样气?」
「两句话讲得辣手辣脚!『侬这种人,就是投胎也是牛马』『侬这戇大,是鬼都想骗。』教他赶紧到更下头去。」
「更下头」是鬼都不想去的地方,一个更加阴森恐怖的存在。
「话重了。」
「可不。」
众人听了,一阵唏嘘。

穿的确良,戴近视镜的小年轻,看起来才二十二三岁,望着挂者的裤腿叹道:「何苦咧?」
身边是个穿粉红旗袍,牡丹盛开在腰间的女人。瞟了一眼的确良手里的票,眼珠翻成了白面:「小孩儿,才来没几年吧?当着这些老少爷们儿造口业,都跟你似的,一下来就能出去?」
眼镜对着太阳亮了亮,并不敢接话,他环顾四周,乌泱泱的人,天南海北的,年轻人不少,可像他一样打扮的确实没有几个,绝大多数都穿着上一个,或上上个时代的衣裳。尖下颏、死鱼眼的旗袍女,旁边就是两个民国的兵痞,眉眼都撇到土里去了。要不是怕脚巡看见,恐怕早就揍他一顿。
他自知无趣,朝众人做了个揖,又笨拙地拜了拜树上的鬼,灰溜溜走了。
此时,树上的人突然打了个饱嗝,吓得兵痞「哟」地一撤,见众人都站着没动,才稳住身子,佯装镇定。
人群发出一阵嗤笑。

老文,还有他的妻子秋娟,并不知道对面吵嚷什么。和这群鬼一样,他们也是等票中的一员。等到票就可以上去,就可以再见儿子一眼。虽然那时候他们和孩子肯定早已忘记了前尘往事,可是万一呢?听说还是有办法哩!
实际上也确实有这样的事:西南三省交界的某个地方,阴司管理混乱。忘情水(也就是孟婆汤)兑了水,魂魄新生以后,就能记得许多往事。所以临死前,老文在自己和秋娟的手心都写了孩子的名字,生怕下来就不记得了。
等了几十年,鬼也要生活,就卖起了火烧。
挂了的这位,就是买头锅的那个。这些天每天都来,一次买两个,要一碗水,见他杵的久,秋娟还趁着不忙送水给他喝,就这样过日子。今日一口气要了 8 张饼,转眼啖尽。谁知他竟是想不开呢?又是什么时候挂上去的?
悄无声息!

沿乌鹊大街一路向北,就是转投中心。到转投中心签到,排号进入转票大厅,确认身份,就能取到鬼生中最重要的票据 —— 转投票。
酆都是地府的中心,承担着分配幽灵再生的重任。人死之后,由地方初审,叙定一生功德,有异议者提出申诉,可以换个地方重审。这个过程,刷下去的不少,有的甚至重审的时候被刷 —— 见鬼的事多了去了。
其他洲界的鬼,以及贵人们的宠物、花草,也占了不少名额。前世非人的,不需要等,直通转投,于是留给这边的转投名额就更少了,只能采取掣签的方式。掣签也是在本地,中了签的人,才到酆都领票。为了这一刻的荣耀,他们不远千里,朝圣一般,风光无限地走向酆都,穿过乌鹊门,抵达转投中心领票。
票上写明了投胎的详细信息,凭此票去所注地方,由地方胥吏三查七对,在耆老和乡民代表的监督下,重新投胎做人。

眼前的鬼,领的都是「上票」,也就是「人票」。「上票」之外,还有「下票」,即所谓「畜票」,或称「虫票」。下票是强制发遣的,没什么情面可讲。至于究竟是成为虫豸,还是微生物,是做牛马,还是猫狗,都不一样。
这就是说,下票也并不一定都很「下」。譬若猫狗,分野生和家养。经历一个严冬,野生猫犬十有八九「二进宫」。这里头有很大的区别。一只兔子,一窝生 10 个,一年产 5 窝。理想状况下,三年后就能有 13 万个直系后裔。再过几年,该有百万亿的孝子贤孙!
可世上哪来那么多兔子?没有!只有少数(3 亿)能长大到有幸进四川人火锅里的程度,其余的又去哪里了呢?
人类就是被保护得太好了,才不知道生命的本来面目。刚一下生就死去的小动物,根本没有功德可言。爹不疼,娘不爱,没有社会关系,就算是遇见最为公正的中正官,又怎么给你增阅历、叙功德?当然只能继续下生,循环往复。
相比较而言,家养的就很好了:不仅饮食无忧,甚至可以反过头来支配人类。还因为有了旁人对它浓郁的感情,使得它们的分值特别高,就拥有更好的前程。野猫残存的记忆不断告诫它们,趁着还活着,一定用力卖萌,务必感化人类,形成羁绊。

除了宠物票,其余下票基本都是「下下票」,又有一个名称 ——「快票」。
快票不用等,都是强制催单结业。我见过一群大头鬼,被全副武装的夜叉赶进瓮城,参加集中转投会。说什么「会」,就是囫囵个儿往坑里跳,一会儿的事,全没了。下生以后什么情况,只能听天由命。
叙定可以为人而不愿意等待的,可以自愿选择「快票」。可谁又想享受这种「快捷」呢?老文当然也不愿意。
等吧!就这样等了 7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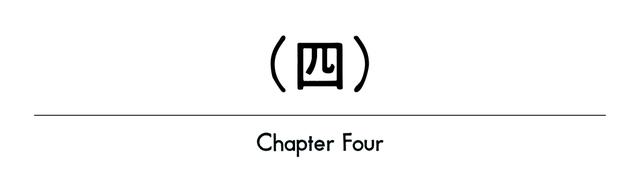
等忙过去两大波,老文终于抽出空,想把树上的那位放下来。
刚走到路当中,却从乌鹊门那边来了几个公人,戴着极高的黑帽子,竖着金色的条纹。衣服同样是黑的,也竖着金色条纹。他们十分显眼,个个都在两米以上,且瘦,脑袋在细长的脖颈上耷拉着,仿佛燃烬的火柴头。
他们咋咋呼呼地把人放下来,开始驱散围观人群,让没领票的赶紧领票,领了票的赶紧走路。
老文生怕惹到他们,活着的时候跟人打官司,惹公爷不高兴,屁股都打飞沫了,血溅满阶,从此发誓不进公门。听人说让黑的抓住,可不是耍处!只好乖乖回去,继续卖他的东西。
「人挂了是鬼,鬼挂了是魙。这人算是完了。」来买火烧的回首望着树上的人,感叹道。
说话的名叫陈遐龄,生前是乡公所的会计,诗词爱好者,有事没事都要说出些高深的词汇,好震惊一下老文。
老文死烦他,他说高阶词汇的时候,时不时就要瞟一眼秋娟,看秋娟敬不敬佩。然而秋娟总不与他对视。

「你说魙死了,又是什么?」陈遐龄问。
「谁知道呢?」秋娟揪着面,眼都没抬一下。
虽然烦,但毕竟是大客户,一次要买几十个火烧。是自掏腰包,带去单位发给同事。因此户部那边的官吏,都不买早饭,专等会计的。
老文敷衍道:「您这个问题很高深。」
陈会计听了,便提高了一下自己的裤腰,每当他要发挥的时候,就要这样做。斜眼望了一下老文,又正正地望着秋娟,词还没说出口,突然又冲来一波公人。模样和上一波差不多,只是穿一身白,凶猛地追撵商贩。
一时间,摊贩们如同惊弓之鸟,疯了似的推着车跑。老文也推着他的破三轮,吱呀吱呀地朝南巷子跑去,那叫一个费劲。行人都驻足看了,有些愕然。
秋娟在后面,左手拎着炭桶,右手提着面。一边跑,一边破口大骂。

会计要帮她提一袋,奈何没有臂力,面粉袋子坠了地,吐出一地霜花,被公差们践踏。白公差们仿佛嗅到了令人神怡的麦香,弯下腰,贪婪地捞着面粉往嘴里送,本来就白的脸白得吓人。一边咀,一边追,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左右商贩,锅碗瓢盆,风雨雷电,混成一团。可这回是跑不掉了,公差使出一招前后夹击,所有摊贩的工具、材料,连同他们筐里香喷喷的火烧,都给弄走了,人也抓了一多半。
巡路管理处就在城门下,年前来了个新主管,听说人不错。见老文脸上被抓了彩,帽子丢了,后脑勺露出来,还挂着个清朝的辫子,十分困惑 —— 按说不该有这种人啊!
问老文啥时候生的,又是啥时候下来的。说是光绪初年出生、宣统二年下来的。更是惊得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说等票不可能等那么久吧!打了好几个电话确认。

同僚都来看,才知道附近卖火烧的小夫妻是清朝的,那男人的六合帽里竟然藏着一条尾巴。
都困惑地问:「你怎么可能一直摇不到号呢?」
老文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大家看不是个事,把东西物归原主,依然遣送回籍。
临行前,主管声色俱厉地对他说:「回去把你的辫子剪了!」又突然贴近他的耳朵,轻声细语:「现在都兴赶时髦,不能当老古董不是?」

许多年后,夫妻两个在省城路边支起摊,摆出报纸。兼带着卖冷饮、泡泡糖,还有其他时髦的玩意儿。
又过了几年,他们攒够了钱,买了个正规摊位。承包了一座方亭,还是卖报纸、饮料。再后来兴电话卡,就弄了三台座机。附近的男女青年都爱来煲电话粥,每次拿起电话,都要说很久。
夫妻吃住都在亭子里,有个折叠床,搭在木架一侧,刚好衔接上,就能睡开两个人。等吃饭,靠亭子不远处摆个煤球炉,坐上锅,把折叠桌摆出来,开始做饭。
老文拖着一条长长的辫子,拿出两个小碟,倒上米醋。把铝锅里的水饺用笊篱舀出,端盘,上桌。现用铁勺,倒上油,捏上一把花椒,贴在煤球的火舌上。等油热,花椒黑了,拿筷子篦着,花椒便留在铁勺里,冒了青烟的热油却进碗。碗里的辣椒面受了烫,滋滋啦啦地叫起来,吹出上千上百的泡泡。
老文吃辣,还配一头蒜,清脆爽口,辣得汗流浃背。
秋娟吃不得辣。但她调制的水饺馅儿老文最爱吃,用花椒水、鸡蛋、五花肉,配各种时蔬。这个春天,不是春韭、荠菜,就是「无事忙」,那是家乡杨树花的俗称。要淘洗几遍,彻底洗干净,清水泡一夜,将苦楚都泡没了,再挤出水分。当馅儿,独一味,可谓「苦尽甘来」。

时令一到,老头、老太太挑满扁担,五毛钱一麻袋。秋娟买了个中年妇女的,那女人竹筷插髻,粽子鞋。鼻翼有一颗芝麻大小的痣,笑起来像春雪。春雪是她活着时的朋友,鼻翼也有一颗痣。
但谁又知道春雪去哪里了呢?
不知道啊!所以他们时常向老家来的新鬼打听故人,尤其是儿子的下落,但总得不到什么确切的消息。
正吃着,来了个老客户,穿西服,戴浅色墨镜,长方形的脸,酒糟鼻,很匆忙的样子。
照例要一份《时事消息》,一份《月旦评》,一瓶橘汁,两块钱,给钱就走。今天却不走了,瞥了眼桌上的水饺,眼直勾勾的。肚里如同水车过桥,木轮咕咕噜噜。
细如竹节的食指指过去:「能不能卖给我一份?」
老文笑道:「这是俺们自己吃的。」
「哦……」他含糊应着,眼睛却死盯着秋娟筷子上被咬了半口的饺子。绿色的春韭,透明的粉条,肥瘦恰好的五花肉。醋碟之上,滴落了它们的油星。
「我给钱,行不行?就给我尝一个吧。」他恳求。
老文和秋娟面面相觑,都停下了手中的筷子,将盘子和一双干净筷子递出去。那人竟不接筷,夺过盘子,捏住饺子的耳朵,昂首送进了嘴里。

水车被骏马拉下了台阶,街边的辘轳也不停地转。水车辘轳奏响了音乐,馋虫爬到了食客的胃管!
秋娟忙给他舀了一碗饺子汤,见他狼吞虎咽,生气道:「你慢点,谁和你抢了?」
话音刚落,老饕的西服随着清晨的广播抖了起来,他的牙齿在打架,身体战栗了,眼眶跟着湿润,便不顾秋娟让他喝口汤的话,将下一个捏起来,朝着辣油蘸去,又一个昂首,喉结一鼓,就进去了!

剩下的三个也吃完,两张十块拍在桌上:「预定明天的了。」
秋娟一阵不爽,心说这就是一整盘水饺,也不值十块钱!给二十块做什么?再说,你说预定就预订么?明天不吃水饺怎么办?
那人却风风火火:「开发一下这个业务吧!」说完,就走了。
俩人拿着两张纸钱,看来看去,越琢磨越不是滋味。
简直莫名其妙嘛!然而想久了,心里头的不舒服就少了,觉得是老天逼他们适应这个时代。你看,咱不是都安电话、卖橘汁了吗?水饺反而离本行更近,不是么?
「包不包?」老文问。
「包!」秋娟说,「包就多包点,卖,就是要麻烦你了,照看亭子,怕你忙不过来,不知道行不行?」
老文想了几秒,眼睛亮了亮,说:「行!」

第二天,那人果然如期而至,拿了报纸、饮料,就坐在桌前,看着报说:「要快!」
才 10 秒,热腾腾的水饺就端上来了。筷子也就砸了砸桌面,发出清脆的响声。将筷子对齐后,夹起水饺,蘸了辣子,一个一个送进嘴里去。
肚里的馋虫又在安逸地唱,还没吃完,就有一个买《每日晨刊》的问:「老板你这水饺怎么卖?」听了价格,一屁股坐西服对面。很快,摊位上坐满了三男一女,吃完,都喝了汤。
头上来的吃得心满意足,又扔下十块钱要走,说是预订,被老文扯住:「用不了那么多!昨天就不该给,这一盘也用不了十块,刚才都说了,只要三块。」
西服笔挺:「竟然这样便宜?」看了一眼还在吃饭的食客,说:「我忙,礼拜天再跟你说!」

后来,这位客户家里买了一台新冰柜,把旧冰柜送给老文他们。又叫了肉联厂的朋友一起品尝水饺,肉联厂的朋友给老文提出建议:「天气马上转暖,包好的水饺摆在板子上,放进冰柜,冻好,过一夜梆硬,收在塑料袋里,就不粘连。都按 25 个一份分好,不要按 30 个一份,容易吃撑。个人建议,你们可以包小一点,不小也没事,但要卖五元一份。还有许多饭量小的,可以卖 15 个,三元一份,不要再细分了,这样有得赚。还有,加桌子,白天卖。到傍晚,冻好的直接卖给下班的路人,让人家可以回家自己煮,也省了你们的麻烦。」
因为听劝,所以赚钱。冬至将至 —— 要准备 2000 份水饺,老文不得不放下手头的工作,和秋娟一起应付。他们的服务依然是那样的周到,水饺依然是那么的饱满,就引起了他人的不满。
这当然不能怨邻居,他们的客人太多,排队总挡在别人家门口。桌子摆了一片,这是摆桌子的地方吗?路边又不让搭棚子,雨天不好干,冬天太冷,便将报刊亭转手,就近找了个店面。不卖报刊、杂志,专门做饭店。
老文见过那位老板的明信片,「五铢口服液总经理 姜子发」。搬冰箱的时候去过他家,经纬马路燕儿台甲字号第五。当时就知道家境不一般,没想到是特别不一般。

老福田已经记不清许多事了,但酆都南大门大匾上的「乌鹊门」三个字,他还是认得的。
起初,大家都不明白,像他这样耄耋冬烘的糊涂蛋,是怎样一次就抽中转世机会的。那些等了十几二十年,甚至三四十年的街坊,除了羡慕嫉妒,又能怎么样呢?
因为情况特殊,像老福田这样的忘事精,一旦抽中了签,得由当地出两位公差护送。护送当然不可能免费,正好借着这样的由头,索要相应的「盘缠」。可福田才下来,除了几十块的新人消费券,没有一丁点积蓄,又不能真把他撇下不管,也不能让他饿死,就触发了「耆老会议」机制。耆老们在当地公所开会,决定还是应该由当地公中出钱。
公中自然也不是冤大头,能出的钱很少,就把活摊派给了两个呆鬼:老实人周广元,比周广元更老实的杨三水。反正就这点钱,能省下,多余的就归他们,省不下,多出的就由他们自己出。
这摆明了糊弄鬼呢!没想到两人当即应了。别人唯恐避之不及的活,他们抢着干,让耆老们闹不明白。
他们的方法也奇,扒运煤车,一天到地方,下了车就要饭。杨三水能用手走路,周广元会口技。进酆都的人都是要走的人,给钱痛快,围观看热闹,毫不吝啬,一上午挣个三十五十的不在话下。
到了乌鹊门,还能免费讹一顿好的。有个操着老家口音的小夫妻,只要用家乡话和他们套近乎,就送火烧。时机选对了,还能是肉火烧!
那女的长得不漂亮,但是耐看,心很善。男的给他们火烧的空,就要倒水送来,生怕别人噎着。因此,一路从老家走到南大门,其实都用不着花钱。
老福田又喊饿了,他经常这样,跟小孩似的。可这回俩人傻眼了,熙熙攘攘的南大街,竟然没有一个摊子。就是常年在这里卖火烧的夫妻,也不见了踪影。
一打听,原来全搬走了。两人你看我,我看你,大眼瞪小眼。
也是饿得慌,就领着福田进了街边的馆子。

一碗面要七块!他俩狼吞虎咽地吃完了,看老福田吃。才吃了两口,老福田就嫌难吃,开始闹。从出发到落地,耳根子就没清净过,周广元气不打一处来,敲着老福田的脑壳骂:「你还挑上了!给我吃!」恶狠狠的。
「别打他。东西是难吃,清汤寡水的。要是卖火烧的还在就好了!」杨三水道。
「就是!」周广元撂下竹筷,一双油手拍在桌上,震得满屋的面条跟着颤:「太难吃了!」
生怕这店家赚钱,周广元多要了两碗汤,就着桌角那罐辣椒油,用得就剩下一点渣渣。把福田领到南大门,出介绍信,领了临访卡,填了表,就进城。
老福田没吃上好吃的,一路闹,路上的都瞧他们,俩人恨不得赶紧送他滚蛋。可完不成任务怎么行呢?
况且酆都的繁华,让他们流连忘返。要不是临访卡只有两日期限,在这里摆个摊表演一番,吃烧饼,睡桥洞,只用一年,还不攒够一万!
就先送老福田进了转投大厅,那里自然有人接待,暂时用不着他们。便出来,准备游两日。然而酆都的东西太贵了,外面一块的,这里要十块,外面三毛的,这里要三十。没等第二天,他们就灰溜溜走了,东西也没敢吃。

老福田的转投地,距离酆都很远,有三千二百里。转投中心的文书宁庭芳办事干练,在别人那里一半天才办完的业务,在她那里半天就弄完了。办完了,就让周广元、杨三水两个把人再送目的地去,却不见他们的踪影。
喊了半天,还是没人应。第二天,正要打电话给乡公所告状,却见俩人风尘仆仆地来了,挨了一顿骂。俩人不敢回嘴,满脸堆笑地接了人。
原来两人饿急了,嫌城里东西贵,跑去外面吃,又回城杂耍了两回,挣了点钱,才回来。
一路骂,不知道非要跑一趟酆都干什么,直接从旧地方送到新地方不好吗?又庆幸有这样送人的机会,让他们能赚到别人赚不到的钱。
一路上,老福田有时候很安静,有时候闹得不可开交。还打周广元,周广元气急了,就还手。他总是恨,恨老头有这么好的机会,却一路都在闹。杨三水一直拦着不让周广元打,说老福田什么都不知道,投胎的地方不好,说不定是贫苦人家,这才让周广元消了气。
快到地方,福田又闹着,想吃好吃的。给他买什么东西都不乐意,就要吃鱼。周广元、杨三水,撸了裤腿,给他抓去。抓到两条黑鱼,借老乡家的厨房做了。又闹吃醋,这家没有,去邻居家借,倒在鱼汤里,多撒盐和葱花。吃了,就不闹了。
一路辛苦,终于把老福田送到了地方,由地方公所签收。临了,两人哭了,让福田到了外面,如果记得,就给他们的家人带个好。

大学的第一个暑假,我终于有机会单独活动。
我去周广元家的时候,发现他没什么家人了,有个侄子住着他的屋。我问他周广元的时候,他立即紧张地说房子是周广元许给他的,明明我都没说房子的事。我渴得慌,说口渴,他也不让一口水喝。我到院子,问能不能喝缸里的水,他媳妇不知从哪里冲出来说:「不能弄脏了!」
于是我舀起缸里的水,卖油翁似的倒进嘴里。她媳妇惊叫了,说:「有细菌!」他也就从堂屋门刁狼似的冲出来,抓住我的胳膊。那女人要我给一百块钱损失才肯放我走,还污蔑我偷东西。
我只好假装掏钱,从裤兜掏出一把冥币洒向天空,小媳妇又惊叫起来,忙着抢,他铁钳似的大手松开了我的胳膊,也去抢,我趁机跑了。很快身后传来他们的怒骂,说我拿假钱骗他们早晚遭天谴。
我又去阳谷看杨三水的家人。他的父亲去世了,我找到他母亲的时候,她正用一双小脚蹬着三轮,拉着一车菜去集上卖。
我把杨三水的消息告诉她,她颤着头,翻开老旧又整洁的靛蓝粗帕,一层一层地剥出一毛、五毛、一块。新版的钱,还有以前的钱,总共十五块。让我拿五块,剩下的转交给杨三水,让他别舍不得花。
我说:「不用了,三水好着呢,可能挣了!他让你买吃的,买喝的,别舍不得花。」
我反过头,给了她五十,说是杨三水给的。她看出不是,很生气,坚定地推开。我假意要买她的荠菜,她非要一袋一袋地称重,高高的,始终不多要一分钱,还给我抹了零头。
我只好找到村里,让大队假装发福利,把东西发给她。

老文有三个兄弟,五个姐妹。大哥和三弟都闹拳,死在了天津岸,三妹、五妹,都走丢了。
他与秋娟一直没生育,又与堂兄弟不和。几个堂兄见这情况,翻着花地骂他们「绝户」。老文婚后十年,他们就开始霸产霸地。每年春耕翻地,都多占两尺,渐渐占完,打又打不过。去官府告状,没使钱,挨了毒打。后来连屋院也都让人霸占,堂兄在院墙外面,打出「正宗肉火烧」的旗号,还造谣说老文的不正宗,用石灰当面粉。
老文便听秋娟的,从二姐四个儿子里过继了最小的一个承嗣,就是福田。搬到村外住,拼了命供孩子读书。
福田很不争气,没敢去找叔叔伯父要回家产。他小时候奸馋滑懒,没心没肺,父母死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忘记了自己还曾有过父母。直至自己当了爹,才想起过去的许多错。他后来吃够了苦,竟成劳模,儿女也很争气,但越争气,他就越怨恨自己小时候不懂事。
后来,他忘的事越来越多,小时候的场景却愈发清晰。
福田越老,就越像小时候,他去世前一直哭闹,说家里的东西不好吃。他倒是闹高兴了,全家人焦头烂额,气得儿女都骂他是讨债鬼。
要走时,女儿单位的领导,儿子单位的教授、老师,都来探望。赶上弥留之际,都等着听他的遗言。结果搞出笑话,要人在碑上刻上他的乳名。
那时已没人知道他乳名,他自己大喊:「我叫甜甜!我叫甜甜!」
众人反应过来,答应了他,他才不闹了。睡了一会儿,突然张口抬肩,汗出如油,眼睛瞪着房梁上的红字,伸手去抓空气,孩子一样哭喊:「妈妈 ——」

福田就是这样走的,很快就转投到了新地方。
我清楚地记得他变成「我」的过程。按正理,孟婆汤喝完以后,就是类似全麻的状态,连时间概念都不会有,然后忘记所有前尘往事,倏忽到新妈妈的肚子里。
可福田的记忆没有被洗刷掉,我的新生就来了。
我记得福田的过往,但更多的是自己的过往。我连我是怎样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拽进肚子里,甚至娘胎羊水流动的声音都记得。在痰湿弥漫的混沌中,时间的流速是缓慢的,往往我以为两小时过去,实际却只过了一分钟。
我似乎也等了一百年,才与那些熟悉的人重逢。
更加奇怪的是,不知什么缘故,清明、中元、过年,以及一些特殊日期,我都会看到许多漂泊无依的鬼魂。
他们一如常人,有的只是在路口坐坐,然后就回去。有的远远跟在亲人后面,一言不发。他们已经没有了家人,或者确实有亲人朋友,只是完全没人想念他们,也许更多的是怨恨。
我想,人与人还是不同的。也是在那时,我发现我可以游荡到他们的世界。我从他们的嘴里,打听到去往那个世界的方法。
该相逢的,终会相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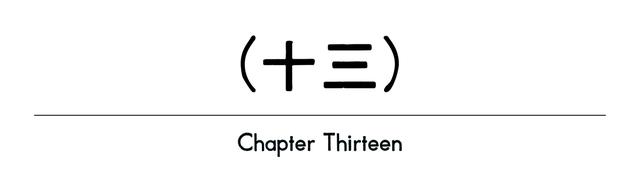
「老板,都有什么?」我坐下。
「咱墙上有的。大葱猪肉丸,韭菜肉,白菜肉,芹菜肉,香菇肉,玉米肉,牛肉,胡萝卜羊肉,虾仁,三鲜,莲藕,芸豆,香椿,茼蒿,鲅鱼,拼盘……想吃什么随便点啊!」秋娟笑着。
「无事忙有吗?」
「无事忙?」秋娟一怔,「无事忙,就几天应季,咱们也没上过,没有存货的,老板。」她依旧笑,还是那样美丽动人。她是两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那真是可惜了,无事忙加上肥肉多多的五花,再加上春韭,真的是绝配啊!」
我看见秋娟的眼睛亮晶晶:「老板,如果您不想吃水饺,小店还能做菜:泰山三美,沂蒙山炒鸡,冻粉里脊丝,凉拌猪耳朵,爆炒腰花……」
「没有火烧吗?」
这话问得秋娟将头一错,盯着我看了半天:「老板是哪里来的?」
她显然不可能把我湘西口音浓重的普通话,和她的老家山东联系起来。
我一时控制不住,望着她还在微笑的眼睛,喊道:「妈,俺饿哩慌!」
我改用老家的话,让秋娟更加愕然,她显然慌了神。把头一低,泪珠一抹,不说话了,去后厨,换老文出来。

「老板,饿了就点菜。要是没事,就先走吧。」老文瞪着个铜铃眼,跟三星堆的纵目人似的。
哈!我终于又见到他了,我已经完全想不起他的模样,但还是一见如故。
见我笑,老文「哼」的一声,把辫子一甩,长辫绕着脖子转了两圈,尾巴搭在锁骨窝前。他拿起辫尾,用牙齿咬住,要干仗的架势。
他什么时候敢打架了?
后来我才知道,有人还留着辫子的事,已经见诸报端,甚至登上热搜。上头派来两波使者劝,劝不动。赶上这几天迎接检查,上头让老文不要抛头露面。老文本来都答应了,只在后厨干活,结果我又来找事。
我忙解释说我是福田的朋友,是「甜甜」的同学。
他们听到「甜甜」两个字,明显激动了。明白过来终于等到确切的家信,都哭了。为了平复他们的情绪,我点了冻粉里脊丝,大葱肉丸水饺四两。
店门口摆着卤肴,猪头肉、猪尾巴、鸡腿、鸭肠、鸭舌、鸭翅。我要了些鸭肠,香辣劲道,老文又端上白酒,关了门,三人一起喝。
为了证明我确实认识甜甜,我说出了只有我们三个知道的往事:「7 岁那年,闹饥荒,你们去外面要饭,把他藏在地窖,留了水和一点吃的。等回来,东西早吃光了,人已经饿得奄奄一息。你们眼前也黑,要了一天饭,就要了半块土豆,打了两把草籽,烧了,一口没吃,给他吃。他饿急了,一口噎着了,好不容易咽下去,又叫渴。他爬不动,你们还能爬。旱灾,水也不易得,你们扶着墙挪去井边排队。井是大井,螺旋石梯,最下头人们又挖了一丈深,随挖着就出点水,都是浑浊的泥汤,不挖水很快就干。你们给排队打水的磕头,乡亲们见了,都说快先给孩子喝吧。排最前打水的男人,舀了一瓢自己桶里澄清的水给你们。你们把水端回家,给福田。他喝了,问:『为什么这个水这么甜?』我说的对也不对?」
「对!对!对!后来下了一场痛快雨,水滴落地上,噗噗冒烟,后来苗长出来了,我们就活下来了……甜甜现在在哪里啊?」老文和秋娟都抓着我的手,激动地问。
我只好如实回答。
听后,秋娟满脸不悦:「这都 20 年了!」埋怨福田下来都不知道找她,我只好解释实情:「你们走的时候,他还太小,又没有照片。过了那么多年,记忆早就模糊了。他的模样也改变了,你们应该也认不得了。再说,他刚一下来,就中签走了,算是幸运的。」
「一来就中,好事,好事。」老文山一样的肩膀垮了下来,低着头坐在凳子上。秋娟的脊梁抵着白墙,反倒笑了。

「有缘的人一定会再次相见,不如顺其自然。常言道:『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做马牛。』他现在在外面,不管过得怎样,肯定也想见你们,想你们的美酒佳肴,我们又何必在乎是以什么形式再见呢?」
公所早就来人通知他们,鉴于他们的特殊情况,上级允许他们直接去酆都领票,不用等摇号了。但不知怎么想的,他们没去。而且之前这些年连摇号也没去。按照规定,不参加摇号的,逢年过节是不允许回乡探亲的。
当我少年时,没有钱财,我会烧些纸钱给他们。天地银行强制结算,不管纸钱后头有几个零,也不管烧的是香车还是别墅,是新出的电车,还是最新款的手机,效果都是一样的,并不比一次写信或者梦见好到哪里去。
但是,所有的想念会变成他们的运气,虽然只有一点点,也足以改变所有人的命运。

老文和秋娟一定留我吃完晚饭,从未有哪顿饭,能让我吃得如此感动。菜香,酒香,饭香,但我必须告辞了。
路上,我突然感到伤心,若有所失,过乌鹊门的时候,竟嚎啕大哭起来。我到酆都,要找曾经的小吏,现在的总理大臣宁庭芳盖章。
清明前几天,我被宁庭芳找到,她知道了我能交通阴阳的事,请我去劝劝老文他们。我和她立了合约,合约规定,如果我成功劝他们转投,就把他们安排在我身边。
有缘人本来就能再次相见的,但和普通的转投不一样,宁庭芳可以把他们的灵魂拽进一扇写着「履突时空」的门,将他们的灵魂转移到更早以前,和我同时长大。
我无权得知他们变成了谁,只能自己感受。

老文,其实是我的初中同桌。在原来的人生里,他叫邵毓麟,光绪元年五月生人。
秋娟,我的大学同系同学。原叫马玉英,光绪三年二月生人。
他们在青岛啤酒节认识,全程我都没参与,直到看到老文的朋友圈,秋娟竟然点了赞,两个相距千里的人,竟然有这样奇妙的交集!
我留言道:「你俩认识?」
都回复我说:「认识啊,怎么啦?」
婚礼定在了五一,他们已经议定请我去当伴郎。
今生今世,我有新的父母和新的朋友。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奔不同的前程。但我始终相信,该相遇的,总会相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