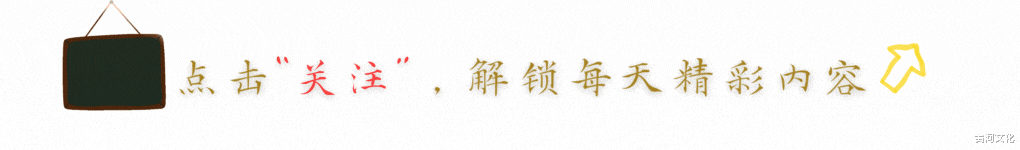第一次与狐狸相遇,是农历七月十五民间的中元节。我和丈夫去老家为已故的婆婆公公上坟,就在我们为亲人祈祷完毕起身时,我惊奇地发现,距坟地不远处的田地埂上,有双眼睛在注视着我们。我让丈夫看,他正全身专注地围着坟头奠酒呢,他不屑一顾地“有啥奇怪的,是谁家的狗跟着人游荡哩。”我自讨没趣自言自语地说,哦,这条狗毛色真好看,长的也秀气。“没夸的人了夸起狗来了。”丈夫取笑我。但他也还是抬起了头,顺着我的视线看了一眼,他疑惑地“呔,那好像不是狗,像狐狸。”站在不远处的动物好像听懂了我们的对话,没有丝毫的胆怯,更没有要离开的意思,眨着一双水淋淋的菱形眼睛注视着我俩,我顿时忐忑不安。它一动不动,似乎在向我们证明,它不是狗,是狐狸。它抖动了一下身子,没有要离开的意思。是不是它饿了?我这样想着,转身看了一眼土台上献的贡品。我漫不经心地说,每次献的东西都是以先人的名义来填饱狐狸的肚儿。丈夫瞪了我一眼,“你以为真的是先人吃了。”我瞅了瞅田埂上的狐狸,再看看坟头上的贡品,真有点不忍心离开。从我记事至今,我只听说过狐狸以及与之有关的神话故事,但从没有亲眼见过它,更没有这样近距离的对视过。它全身的毛色是那种灰色,确切地说像银灰,如涂了一层油彩,它优雅的身段与眼前绿油油的麦田融和在一起,是一幅无法预演的人与动物、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画面。我盯着狐狸感叹,现在的好多动物不怕人了。丈夫朝前走了几步,他顺手拔了一根摇曳的燕麦草,朝着狐狸摇晃“那是的,国家明令禁止不许伤害动物,没人敢捕猎,动物繁殖快了。”我看到狐狸竖起耳朵,好像听懂了我们的对话,它敏锐的样子倒让人心生爱怜。我看它很有灵性,半开玩笑的说,它是不是人投胎转世?丈夫别了我一眼“你书看多了,去问问,它是不是人转世投胎。”“哈哈哈……”丈夫为他能噎住我而放肆地大笑。狐狸用警觉的眼神怔怔地盯着我们。“狐狸确实是一种很有灵性的动物,但它再机灵也不会听懂人话,你神神叨叨的,让人心里发怵。”丈夫的数落,让我深深地吸了一口大自然的新鲜空气。

丈夫接着说“它感觉我们不会伤害它,所以也很好奇。”我反问,你不也无形中说他能通人性的吗?丈夫无语了。狐狸仍然与我们对望着。我发现它的眼眉间含满了秋色,我想,它也大概是与秋同行,漫步与大自然中,寻找只有动物才懂的浪漫与感动吧。“走啊,还发什么呆?”丈夫已经很不耐烦了。我发现狐狸根本没有离开的意思,倒也不像是贪念坟头的吃食,不过,它确实好像在等什么?“等什么,你去问问。”丈夫举起他手中的燕麦“吽——吽”喊了两声,跺了几下脚,这时狐狸抖了抖身子,转身朝着另一个方向缓慢前行。走了几步又停下来伸了一下脖子,似乎舒展了一口气。看它不是等着吃食物,我反倒有些失落。它悠悠荡荡走着,却又再次转身看着我们。我突然感到它那双属有灵动的眼神里,布满了一层淡淡的忧伤。我心里隐隐感到它或许有什么心事。“有心事?你真的是在聊斋中梦游,疑神疑鬼怪的竟看懂了狐狸的心思。”丈夫使劲捏了一下车钥匙。在我的猜疑与遐想中,狐狸一步一回头地向田野深处走去。大地上绿意弥散,麦田一块连着一块,野花装点着秋的景色,红的,黄的。人间烟火中伴着动物的悠闲与人的安然,各自体验着大自然的情怀。渐渐地我心中的恐惧感消失,用深情的眼眸,解读着狐狸的眼神和它的内心世界,即使我无法与狐狸交流,没有表白,没有告别,但狐狸看我们的那种眼神,却深深地吸引了我,让我久久不能忘怀。其实,以前对狐狸有很大的偏见。小时候常听村人说狐狸很坏,逮着机会溜进村子鸡就会遭殃。后来在文学作品中读到的特别是被文字妖化了的九尾狐。它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动物形象,具有复杂的文化内涵,它总是与神秘联系在一起。它在众兽形象中,给人的影响是妖媚,狡诈,阴险,残忍。特别是狡猾成性的九尾狐,它在神话里是狐狸经过千年的修炼后成精,尾巴分裂为无数条,能做出各种怪异和妖孽的事情。当时光的脚步倒回到先秦时期,九尾狐却被人们视为瑞兽,为王称帝,国家昌盛之兆,具有吉祥的寓意。《山海经》中记载的狐狸却有善有恶,从涂山之女到苏妲己,向人们展示的是狐狸的两面性。而蒲松龄笔下的狐仙却又是集人类的美德于一身,重感情,重友谊,一直是人类的好朋友。它们表现出的纯真和善良,有时比人类更加可爱。神话故事是人们的臆想与愿望,也是抚慰人心灵很朴素的精神食粮。经年的故事,散落于尘世,在时光的研磨和甄别中,有的变成过往拂去的尘烟,有的书写成流传千古的诗文。世间的一些经久不衰的神话和故事,时不时地从心中涌动,荡起层层涟漪。闲暇时日,我用荒诞的神话或神奇的传说填补空虚的心灵,在文字中寻找世间万物心灵相通的真情与真相。转眼,时光的大手挥笔画出了又一年秋的成熟,秋的绚灿,秋的硕果。我与亲朋好友相约去祁连山赏秋景,观秋色,捡蘑菇,采摘酸刺果。我们的目的地是民乐南端玉带河上游的石门里。秋色在大地上铺开。季节的飘窗外,鹅黄色的树叶点缀穿过林地间的阳光,照耀在人的身上、脸上、眼睛和心里。在秋风相伴的庄稼地里,体验大自然的深情,在诗与远方的向往中,亲吻祁连山的秋韵与秋景。过玉带河停车进山时,我的身体出现了状况,心跳加快,气喘嘘嘘。大家一致认为我不能上山,我只好失望地呆在原地。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我的喟叹、沮丧。我在玉带河边漫无目标地转悠,河水哗哗啦啦,拍打着石头,像是赞美秋天,与陌生的我打着招呼。我走着,寻着,山脚下布满荆棘的桦柴和鞭马中,也显露出红丢丢酸刺果,零星的野草莓。顿时,我孤独的心身得以慰籍。手不停地采摘,心里充满了秋的气味,眼里满是秋的丰盈,秋的感动,以及大山的宽厚与豁达。蓝天白云,山崖石壁,万物生命,山川河流,此刻我仿佛在世外桃源里做梦呢。仰望、远眺。突然不远处的青苔上蹲着一条酷似狗的动物。妈呀,我差点哭出来,心突突突狂跳不止。是狗,还是狼?环视四周一个人影都看不到,怎么办?我想大声叫喊,吓唬它,但又怕我的叫声会引来更多的野兽。我浑身都在打颤,手中提着盛酸刺果的小桶,在慌乱中早已打翻,酸刺果散落在柴草里,我已顾不得那些了,就想赶紧逃离。无奈,双脚被脚下的荆棘绊住,双腿好像灌了铅,不时地被绊倒,我连爬带滚过了一条小溪。四下瞅了瞅,没有一个人影,瞟一眼那个动物,它像一幅雕塑一动不动地盯着我,感觉那双眼睛是那么的熟悉,好像哪里见过。蓦地,我的脑海中出现了去年秋天遇见的狐狸。是它?身段不大,银灰毛色。看它仍然在原地不动,没有追赶我的意思,我的心才稍稍平静了一些。我定了定神,恢复了一下慌乱的心绪,满腹疑惑地对着狐狸嘀咕,难道你真是人转世托生,是吓我,还是看,难道我们真有前世缘?不远处的动物两只前腿直立着,后腿坐在石头上。水汪汪的眼睛一眨不眨。它被绿茵茵的草丛,盈盈的野花拥簇着,既温馨又浪漫。山岩苍翠,林木茂密,河水潺潺,一切都显得那么和谐、自然。刚才的惊慌失措在一点点的消散,此刻我想的是,眼前的动物,它的眼神没有一丝一毫的敌意,倒像是有种女性的温婉与柔情。是它,我感觉是去年秋天我遇见过的灰狐。我想它一定是吸收了大山的灵气,成为通人性的仙狐。或许想对我诉说点什么?我和灰狐就这样对望着,似乎我们早就认识,但一时又想不起是前世,还是梦里。我猛然醒悟,我们的相遇不是梦境,更不是在聊斋故事里,而是现实版的真人真事。这是一个听来的故事。大概是上世纪60年代末期,大集体生产队红红火火的劳动场景,在祁连山下的玉带河边荡开。那时候没有条件上学的男女,只要能拿得动铁锨,就要参加生产劳动,给家里挣工分。挣不到工分就分不到口粮,分不到口粮你就得饿肚子。家里条件好一点的孩子能晚一点参加劳动,如果人口多条件差的,不论男孩还是女孩,十三四岁就给队上放马、放牛参加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当然挣的工分自然也很低。少年一家是从城镇下放到乡村。不谙世事的他,对农村的很多事感到既新鲜又好奇。他家隔壁邻居有位和他年龄差不多的姑娘,身影单薄早出晚归,她已涌入大人的行列参加集体劳动。他们经常遇见,也清楚对方的来历和身份,但从来没有开口说过话,哪怕是一句简单的问候或是礼节性的招呼。尘世间有些缘分,被时光的风卷袭,在岁月的河滩里搁浅,消散流失于人间烟火中。两位相识却一直保持着沉默的少年,被农村的习俗和规矩束缚着。其实他们各自的内心,是对世界的美好认知和对人情世故的感知。他们的心灵如玉般纯洁。少年对祁连山的雪,玉带河的水是入心的喜欢。被雪山水滋润的山村虽原始古朴,却也有着宁静祥和的魅力,这景致正好填补了他内心的寂寥。村里的女子不管春夏秋冬,无论年龄大小一年四季头上都包着围巾。从头巾的颜色上便能区分开年龄的大小。岁数大一点的,年老的女人,大都是深色的,如灰色,黑篮色,咖啡色。那些年轻的小媳妇,未婚的大姑娘都喜欢色彩鲜亮,颜色艳丽的,如大红、玫红、天蓝、橘黄、翠绿等。村子里,田野上仿佛飘摇着一面面小彩旗。这是当地的习俗,也是乡村的一道风景。少年家与一墙之隔的邻居渐渐熟悉了。邻家的姑娘与少年差不多大小。他们的遇见是“恰好”的那种感觉。四目相对时,那一刻的美丽便留在了记忆里。姑娘穿着的衣裤,既不合体而且还很破旧,但那一块又一块叠摞的补丁干干净净,平平整整,匀称的针脚里包含着女子温柔、细腻的心思。她的脸虽然被围巾包裹的很严实,但从她露出的两只眼睛里可以看出,一个心事重重的女孩,在世事的磨砺中,生出的忧伤,淡淡的,那是艰辛生活刻下的痕迹,让人爱怜。当岁月的风掀开往日的幕布,向着玉带河轻舞飞扬,曾青春年华的少年,经岁月的洗涤和历练已变老,但忆起遥远的遇见却又是无限的感慨。那位羞羞答答,端庄朴实的农家姑娘,让少年心怀憧憬。他怀着对异性的好奇,对她多了一份关注。日子在往复循环中一天天的度过。然而一连几天少年眼中熟悉的身影消失了。他在路上,在人群中寻找着。有一天,无意之中他听家人说姑娘生病了,而且很严重。那些多事的女人在劳动停歇的瞬间,围拢在一起挤眉弄眼的说话,却又四处张望,唯恐别人听到。少年虽然牵挂着姑娘,但不好意思打听她究竟得了什么病。在焦急和不安中聪慧的少年观察、期待。然而一连几天姑娘家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她的父母、哥哥依然早出晚归,没有显现出异常。就这样日子在平淡中安然度过,有一天少年突然就听到邻家姑娘已经死了。他不相信这是事实,发疯似的朝姑娘家跑去。这时他和姑娘的哥哥遇见了。他问“是真的吗?”“嗯”,“那为啥不送去医院?”“吃了几片药,也请了神婆……”姑娘哥哥没有丝毫的悲伤,反而显得如释重负。“那她究竟得的啥病?”少年涨红了脸,姑娘哥哥欲言又止“哎,啥病……”他停了片刻,低着头,声音像蚊子一样“说不出口的脏病。”脏病,世间还有这种病?少年第一次听说这个病名,他十分惊讶,想弄明白“脏病”究竟属于什么病?他发现人们在议论这件事情时,都是低声咬耳,神神秘秘。这样的情景更增添了少年的好奇心,他一定要弄清真相。经多方打听,少年了解到了事情的一些原委。姑娘因第一次来潮,参加劳动时干的又是力气活。她不好意思给妈妈说,更不愿让别人看出端倪,便不惜余力地坚持劳动,渐渐地血流不止。家人发现后,说是鬼魅附身纠缠,请了神婆做法驱妖,不见效果,村庄距县城大概30多公里,没有人提议送去医院救治,只吃了几片药,不知是安慰患者的心,还是安抚活人的眼。家人们眼睁睁看着姑娘流尽了体内最后一滴血,人霎时变成了一具白色的空皮囊。那天晚上,大雨倾盆,电闪雷鸣。当姑娘咽下最后一口气时,有人看到从她家院子里飞出了一道犹如闪电的白光。一个鲜花般生命消失了,然而,在她身后又飞出很多传言。“她是狐狸转世啊,你们没发现她的眼睛,水汪汪的迷人,那是妖气。听到没,她死了的那天晚上,一道白光飞出村子,野地里狐狸就发出了哀嚎……”“一个女娃娃,哪来那么多血?”更有甚者“她是怀上娃了,打胎导致大出血……”后来,有人看到玉带河边经常出现一只灰色的狐狸,它时不时站在土丘或高一些的地埂上眺望,哀嚎,眼里还淌着两行泪水。此刻,我竟对不远处的狐狸,产生了爱意。从初遇到再次相见。我感觉它有人间情思,有深深的失落与悲伤。在它的灵魂里似乎跳动着与人为善的那份情怀……亲历者讲完这个故事,神色凝重地注视着远方,虽然他已年过半辈,但对于这件事他依然久久不能释怀。我从他的长叹中,能够理解他的心情。对于一个旁观者,能做到的只是对逝者的同情、怜悯,对愚昧落后的现状却无可奈何。“我们来了——”进山的人回来了。蹲守的狐狸听到声音,像上次一样,长吁短叹,起身、站立、抖了抖身子,掉头走了几步,又转身看了看。我突然领悟,这只灰狐是通人性的。你看,它在哀伤失落的同时,依然对人间充满了留恋和不舍。回家后,每当想起那个眼神,它刺痛的不只是我的感官,而是深深刺激了我的精神世界。
个人简历:滕建民,笔名漠北雪莲,文学爱好者。甘肃省作协会员。有文字发表于省、市、县级报刊杂志,文学网站。偶获过国家级、省市级举办的散文征文赛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