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历史上的女性——第34回这次咱们说说历史上的那些女性。不是讲故事,就是聊聊她们的事儿。每期咱们都会挑些有意思的女性来谈谈,这次也不例外。这些女性啊,有的名气大,有的可能你都不咋听说过,但她们的故事都挺值得琢磨。咱也不扯那些复杂的,就简单说说她们的经历、事迹啥的。这些女性啊,生活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背景,但她们都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这次咱们要聊的这些女性,各有各的精彩。有的智慧过人,有的勇敢无畏,反正都不是一般人。她们的故事啊,有的让人敬佩,有的让人感叹,反正听了都挺有感触的。好了,咱也不多说啥了,直接进入主题吧。这次要聊的这些历史上的女性,绝对值得你一听。
来听个搞笑的事儿。有个同学不舒服了,就写了张请假条让同学帮忙带给老师。这家伙平时就大大咧咧的,写东西从不在意标点符号,经常连标点都懒得加。他的请假条是这样写的:“李老师您好,今天我生病了,得请一天假,请您批准。”
这同学的哥们儿挺爱捣蛋,瞅见请假条上没标点,就心生一计,悄悄给添上了。老师接过请假条一瞅,当时就笑了。请假条上写着呢:“李老师,您好!我因为生病,得请一天假。望批准。”
那个请假的同学,他原本想说的是“我生病了,所以需要请一天假”,但因为偷了个懒,结果闹了个大笑话。这事儿就说明了标点符号有多重要。
其实在中国古代,这类笑话可不少见。就像《韩非子》里头讲了这么个事儿:鲁哀公问孔子:“我听说夔这家伙只有一只脚,是真的吗?”孔子一听,立马笑了,然后给鲁哀公解释了好一阵子。原来啊,夔是个人名,他是上古尧帝那时候的一个非常牛的乐官,特别懂音乐。后来舜帝上台了,琢磨着找人接替夔的位子。尧帝就说,像夔这样的乐官,有一个就足够了。他原话是说“夔有一个,就够了!”没想到被粗心或者不懂文书的鲁哀公给误解了。

古代汉语没标点,说话写字就容易让人摸不清头脑。到了汉朝,虽然有了“句读”这玩意儿,帮忙给文章断个句,但特别随意,也不详细。北宋那会儿,书本上还是看不出明显的断句,文章的意思还是得靠读者自己去琢磨。那时候的文章,最多就用个“。”来表示一句话说完了,中间语气转换或者停顿,就用个“,”或者“、”,跟现在的句号、逗号和顿号差不多。除此之外,也没啥别的标点符号了。
这说白了就是标点符号的原始样子,只能用来分分隔文字,没啥别的意思,更不能表达疑问啊、感叹啊这些情感。特别是那时候,加了“标点”的书特别少,大多数书还是光有字(就像现在有的书法作品,还是这样,一整篇的字,一个标点都没有,看着都让人头疼)。
看没有标点符号的书,对老百姓来说真是挺费劲的。这种状况一直拖到了清朝快结束的时候,才有人从国外把一整套标点符号带了回来。这个人就是外国人眼里的“中国天使”——斌椿。
斌椿是满洲正白旗的一员,跟内阁大学士恒祺沾亲带故,以前还在山西襄陵县当过知县。1866年,他踏出国门,成了清朝头一个去欧洲开眼界的(或者说头一个出国的官员)。那他究竟是怎么去欧洲的呢?这事儿得扯上一个英国人,名叫罗伯特·赫德。

赫德19岁那年,也就是1854年,他就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一待就是五十年。这五十年里,他一直在给清朝当海关的总头头,管着税务的事儿。
1866年,也就是清朝的同治年间,31岁的赫德打算回英国办婚礼,他希望清政府能派几个官员跟他一起去英国看看。慈禧太后看到了赫德的请求,就跑去问恭亲王奕䜣该怎么办。奕䜣呢,他一直管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思想比较开放,他觉得官员出国访问挺好的,就支持了这个想法。

不过后来奕䜣摊上事儿了。那时候,朝廷里的官员们一个个都挺保守,谁也不想出国门瞅瞅,更别提清朝压根儿就没派人去过欧洲。跟之前的明朝比起来,清朝那简直是更封闭了。虽说1840年鸦片战争后,欧洲列强用枪炮轰开了清朝的大门,但也就是些外国人往咱这儿跑,咱中国人还是没迈出过那道坎儿。就拿道光皇帝来说吧,他还闹了个大笑话呢,居然问手下大臣:“英吉利和伊犁之间能不能走着去?”这事儿就能看出清朝有多闭塞。一直到同治那会儿,愣是一个清朝官员都没正式去过欧洲。
不光清朝,翻看中国历史的长卷,你会发现之前也没官员去过欧洲。汉朝那会儿,咱们的人顶多走到西亚;唐朝时,唐玄奘西天取经,也就到了印度;明朝的郑和七下西洋,船队到过南洋、非洲,却也没踏上欧洲半步。要说真有人到过欧洲,那也就蒙古大军骑着马冲过去了,但那可不是友好访问,也不是旅游观光,纯粹是为了打仗征服。他们没从欧洲学到啥,甚至压根儿没意识到有个地方叫欧洲。
所以,清朝的人对欧洲那是一窍不通,当时的官员们心里头直打鼓,谁也不愿意踏上那片未知的土地。就连那些平日里口口声声说要学习洋人的长处来对付他们的大臣们,此刻也都变成了胆小鬼,不是这个不舒服就是那个有毛病,想尽办法推卸责任。反正,朝廷里上上下下那些官员,一个个都装病躲着,没人敢应声。就在这时,有个老爷子站了出来,他就是斌椿。
那时候,斌椿已经63岁了,本该在家享清福,但大学生恒祺给他介绍了个活儿,去海关给赫德当文案,也就是秘书。赫德看斌椿挺有本事,就鼓励他去英国考察一番。赫德心里的小九九是,想让斌椿出去见见世面,回来帮他推动中国的外交工作。
斌椿虽然上了年纪,但眼光独到,也挺有胆识。他从小就读儒家经典,参加过科举考试,虽说是个老派的读书人,可他的阅历和想法却挺不一样。他以前在外地当过官,走南闯北,见过不少世面,心胸挺宽广。他还写过这样的诗句:“心里老想着出海去,可惜没那机会啊;每次海上来客人,聊着聊着就羡慕不已……”所以,这次出国访问的机会,斌椿特别上心。
但当斌椿决定这么做时,很多人,包括他的家人,都跳出来反对。他们都说英国那地方太野蛮,不能去冒险。为了劝他打消念头,他们还提起了汉朝时苏武出使匈奴,结果被困在贝加尔湖长达二十多年的事儿。

但斌椿心意已决,毫不动摇。他讲道:“老天爷想考验读书人的胆量,就用万里波涛当难关!”他接着说,“我可是朝廷正式派出去的使臣,名正言顺地去国外访问,这种机会可不是谁都能碰上的,此番出行根本无需多虑!”
1866年农历一月二十一,斌椿领着京师同文馆的三名弟子,像张德彝他们几个,还有他儿子广英,一块儿从北京出发去欧洲游历。他们一路上经过了香港、新加坡、苏伊士这些地儿,在海上漂了二十多天后,终于在3月18号抵达了法国马赛,这是他们的第一站,先要去法国访问看看。
一踏上岸,斌椿他们立马被看到的景象给惊呆了:大街上来来往往的,男女老少都有,自由自在地逛着。年轻姑娘穿着挺凉快,身材都显露出来。还有那些高鼻梁、蓝眼珠的外国人,踩着高跟鞋,头发卷卷的,到处都是。再看路边,那些教堂的尖顶直愣愣地冲向天空,工厂里的大烟囱呼呼地冒着烟。这一切都让这位六十多岁的老爷子长了不少见识,心里头别提多激动了。
斌椿他们几个留着长辫子的人,吸引了好多外国人的目光,这些老外对这些装扮“特别”的人也特别好奇,甚至还把他们登上了报纸,成了热点新闻。后来,报社还特意出了本带斌椿照片的画册来卖,没想到一下子就卖光了,斌椿简直就像个“大腕儿”一样。在大街小巷,大家都在聊他们的衣裳、长相和举动,这一切都让人感觉很新奇、很带劲。
在法国,斌椿他们成了大明星,走到哪儿都有人盯着看,抢尽了风头。马赛的记者整天围着中国这个官方考察团转,不停地问他们对马赛感觉咋样。有的法国老百姓还特别热心,操心起斌椿在马赛的日子过得好不好,甚至还有人给他出主意,让他找个法国美女一起过个浪漫的夜晚……
夜幕降临,斌椿他们被领到了酒店七楼房间休息。头一回坐电梯,斌椿惊得不行。以往,他只知道吟诵李白的诗句,“高楼耸云端,伸手可摸星”;而现在,这直冲云霄的大楼,眨眼间就到了,简直太不可思议!他不禁赞叹,西方那“巧妙”玩意儿,真是名符其实!斌椿的儿子和那几个小伙子更是乐开了花,在电梯里上上下下玩得不亦乐乎,心想,这感觉就跟孙悟空驾云飞天似的,爽极了!
从马赛出发后,他们选择坐火车直奔巴黎。斌椿这辈子头一回见到火车,心里头那个激动啊:哇塞,这车长得跟长龙一样,瞅着挺憨厚的,可跑起来,速度比马儿还溜!到了巴黎,他逢人就讲坐火车的那股新鲜劲儿。当地的华侨商人瞧他这么迷火车,干脆就送了他一个火车的小摆件。
后来,斌椿根据自己的欧洲之旅,写了一本日记叫《海外漫游录》。在这本书里,他分享了自己对欧洲的看法和经历。谈到火车时,他是这样叙述的:
每队车子有五十到六十辆不等,都用铁环串在一起。头一辆车装的是点火装置,第二辆车拉的是煤,路上不够了就随时加上……
书里讲到了火轮升降机、煤气灯这些机器的事儿,还特别有意思地写了儿童自行车:
有个木头做的马,大概有三尺多长,它的两个耳朵装有转轴。人要是骑上去,用手转动它的耳朵,里面的机关就会动起来,然后这木马就能不停地跑。这大概是借鉴了木牛流马的设计思路吧?
斌椿他们结束了在法国长达17天的旅程后,紧接着抵达了赫德的故乡——英国。英国可是工业革命的起源地,伦敦比巴黎热闹多了。一到伦敦,斌椿就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人口众多,楼房排列有序,街道也干净整齐。高楼大厦一座挨着一座,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斌椿看得都惊呆了。在伦敦,斌椿见到了好多从未见过的新鲜玩意儿,比如蒸汽机、火车、电报、显微镜、轮船、高炉、枪械,还有各种机器工厂。这些东西让他看得眼花缭乱。斌椿满心欢喜地到处转悠,还在伦敦的照相馆里,拍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张照片呢。
赫德做了安排,英国政府给他们提供了非常隆重的接待。到了5月7号那天,维多利亚女王特地在白金汉宫搞了个大型舞会,就是为了欢迎这些远道而来的东方朋友。斌椿呢,也创造了历史,成了第一个踏进白金汉宫的清朝大臣。
宫廷舞厅真是又大又气派,装修得金碧辉煌,让人看得目瞪口呆,光是灯笼就挂了好几千个。那时候,有800个男女在那里一块儿跳舞,把这位中国大爷给震惊坏了。他头一回瞧见西洋女子穿着那么凉快,胸脯和后背都露在外头,他脸上那些皱纹里都透着兴奋和惊讶。他心里直嘀咕:这世面可真没见过!
中国的大使们,以前从没去过国外,这次得到任务出国逛逛,才发现国外竟然有这么美的地方!

第二天,维多利亚女王又单独跟斌椿聊了聊。斌椿挺感激,他说道:
看到伦敦的房屋和器具,做得真是精细巧妙,比我们中国的好多了。而且他们的政务管理,也有好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我还受到了君主的热情款待,能够到处游览美景,真是感觉既感激又幸运!
然后他就像李白附体一样,灵感爆棚,一口气写了好几首诗,其中有一首是这样的:
羽衣飘飘长带风,窄袖贴身显轻盈,胸前宝串闪亮光,耀眼夺目真迷人。乐曲响起霓裳调,众人合拍共起舞,鸾鸟凤凰齐展翅,仿佛飞到蓬瀛岛。
斌椿在英国待了一阵后,接着去了荷兰、丹麦、瑞典、芬兰、俄国、德国以前叫普鲁士、比利时这些地方。加上英国和法国,他总共花了四个多月,跑了11个国家,算是中国头一个好好逛了逛欧洲的人。他每到个新地方,都觉得特别新鲜,不光打听了当地的风俗习惯,还学到了像“地球是圆的,自己转个不停”这些以前不知道的事儿,这让好多中国人的老观念都翻了个个儿。
拿荷兰来说吧。早在明朝那会儿,咱们中国人就晓得有这么个国家,但那时候也就仅仅停留在脑袋里想想,《明史》里头有个《和兰传》,里面是这样讲述荷兰的:
红毛国也叫和兰,离佛郎机挺近。在永乐、宣德那会儿,郑和七次出海,走过了好几十个国家,但那时候还没提到和兰。他们那儿的人眼睛深、鼻子长,头发和眉毛都是红的,脚还特别长,有一尺二寸左右……他们使唤的仆人叫乌鬼,下水不会沉,在海面上跑就像在地上走一样。
斌椿到了荷兰后,才算真正深入了解了这个小国家。他在《海外游记》里是这样写的:“荷兰这个国家,长六百五十里,宽三百五十里,西北边靠着大西洋,地势平坦没有山,港口特别多,老百姓常受水灾,所以特别擅长水利,修堤坝很在行,划船运输也是一把好手,南洋那些小岛国,都建有码头……”斌椿感叹说,真是亲眼见到的才最真实啊。
7月6号那天,斌椿他们一行人抵达了瑞典。人家给他们安排去了北极圈里头的一个小城逛逛。他们亲眼见到了从来都没听说过的“极昼”这神奇景象,结果兴奋得整整一天都没合眼。
哎,你听说了吗?有些地方居然没有黑夜,一整天都是大白天!这世界真是啥怪事都有,斌椿都被惊得不行了。
在瑞典,斌椿他们受到了国宾一样的隆重接待。瑞典国王特意在他的度假屋见了斌椿,而王妃则被斌椿手里的一把扇子迷住了,那扇子上画的是沈凤墀的名作《采芝图》。王妃对中国的传统绘画也是情有独钟。
瑞典的皇后娘娘在后宫专门接见了来自中国的客人,用当地十分难得的水果大餐来款待大家。斌椿感到非常意外和荣幸,立马就作了首诗,大力夸奖皇后娘娘:
西王母住在瀛洲那片仙境,她能邀请人游览十二座珠宝宫殿;真奇怪,凡间的尘土根本飞不进去,因为那里碧波荡漾,青山环绕,守护着那美丽的琼楼玉宇。

斌椿他们9月18日回到了北京。他这次欧洲旅行,加上往返路程,一共花了快半年。他总共去了11个国家,坐了19次船,42次火车,跑了9万多里路,这比绕地球一圈还要多。斌椿把这次欧洲旅行的经历整理成了一本日记,交给了总理衙门。
斌椿英语不通,所以这次去欧洲访问,他只是简单记录了看到和听到的东西。但这些日记却成了当时中国人认识欧洲的一个重要途径。通过这些日记,中国人开始意识到,英法这些国家和越南、朝鲜这些藩属国不一样,世界远比他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斌椿这次出门,干的另一件大事儿,就是给咱中国带回了正宗的标点符号。在英国那会儿,有天早晨喝茶时,他借着翻译的帮忙,看了几张英国报纸。这一看可不得了,他发现英文句子中间夹着好多“小逗号”和小圆圈这些玩意儿,这让他激动坏了,赶紧问翻译这是咋回事。翻译就告诉他,这些符号叫标点,专门用来隔开句子,还能表达说话语气,跟咱们汉语的句读差不多一个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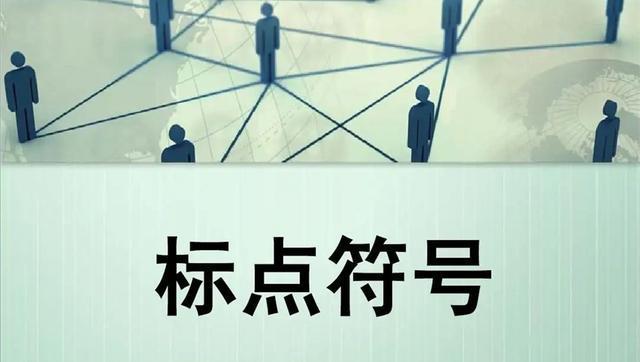
斌椿啃了一辈子的古书,深知读这些书有多费劲,主要就是因为断句,也就是句子停顿这块儿,大家全靠自己去猜古人的心思,这样很容易就理解错了。他觉得英国人搞出的那个标点符号挺管用,能帮读者顺畅地看书,还能让大家的阅读方式都一样。等他回到国内,就把这个重要发现上报给了皇上,结果他就成了第一个把标点符号带到中国来的人。
得提一下,斌椿的助手,年轻小张张德彝也是收获满满。他后来写了本讲欧洲新玩意儿的书,名叫《航海奇遇记》啥的,里面记了斌椿他们团在欧洲见识到的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后的那些新东西。这本书啊,算是给19世纪的中国和世界搭了个桥,让大清帝国在近代化的路上往前迈了一大步,影响深远着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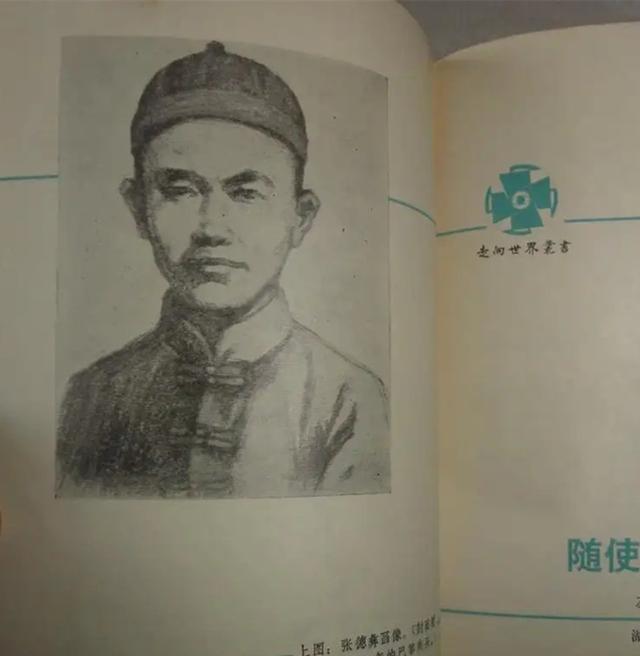
之后,张德彝郑重其事地把标点符号推荐给了中国的文化圈。他在著作《欧美环游记》里,讲述了西洋标点符号被引进中国的事儿,书里是这样叙述的:
西方国家的书里,他们标句子的方式挺复杂的。要是话说完了,就用“。”来表示;话还没讲完,就用‘,’接着;要是表达惊讶或者赞叹,就用‘!’;提问的时候呢,就用‘?’……就这样。
打那以后,标点符号就钻进了咱们中国的文字里头。但那时候它们还没咋被广泛用上,一直等到新文化运动那会儿,鲁迅、胡适这些大腕儿开始推崇白话文,标点符号这才火了起来,被大力推广。现在啊,当年斌椿眼里头那些像“小蝌蚪”跟小圆圈似的东西,已经满处都是了。
斌椿,这家伙在历史长河里差点儿就被抹去了痕迹,但他干的事儿可解决了咱们中文里“看书头疼”的大难题,这事儿,咱们后代人可得记着!他的功劳,真不该被忘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