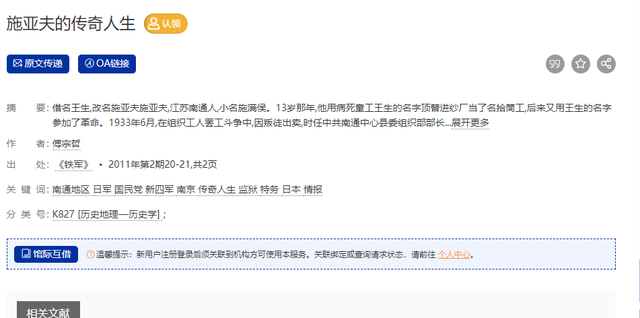1944年初的一个冬夜,夜幕早已低垂,寒风裹挟着刺骨的凉意,拍打着南通城的砖墙。
施亚夫像往常一样从伪军驻地返回他隐秘的府邸,他的脚步轻缓有序,看似没有任何异样。
然而,就在他准备推开屋门时,一个熟悉又急促的脚步声从暗影中传来。
来人是一身斗篷的潘宜娟,伪军副师长范杰的夫人。

“小林信男,他们怀疑你!”她的开场没有任何寒暄,而是开门见山地提到下午在师长田铁夫家发生的事。
潜伏多年,施亚夫是否终于暴露了?
 从红十四军到南通特委
从红十四军到南通特委1930年初,由于组织变动的需要,施亚夫转离了红十四军。
他随即加入了中共南通特委,开始专注于一项更为隐秘和危险的任务——兵运工作。
这项工作极为复杂,他需要秘密接触国民党部队中的基层士兵和营连干部,在看似平静的表面下建立起革命联络网络,并为中共争取军事资源和潜在支持。

1931年4月,一场突如其来的打击降临到施亚夫头上。
由于叛徒的告密,他的身份暴露,被特务机关逮捕。
在随后的审讯中,施亚夫被关押在阴冷逼仄的监牢里。
敌人反复用威逼利诱的手段试图让他开口,施亚夫始终咬牙坚持,没有透露任何党的秘密。
当年的8月,在党组织和社会力量多方面的努力下,他终于得以从牢狱中获释。

出狱后,施亚夫没有选择休整,而是迅速重新投入到革命事业中。
他与党的上级组织取得联系后,很快赶往上海。
在这座汇聚各方势力的复杂城市中,他在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中找到了新的革命立足点。

此后的几年间,施亚夫回到了南通地区,成为当地党组织的中坚力量。
他的才能很快受到组织信任,担任南通中心县委的重要职务。
在1933年的“五厂两校”罢工罢课事件中,面对工人和学生们对恶劣工作条件和压迫教育制度的强烈不满,施亚夫搭建起工人和学生的联合行动机制。
随着运动的扩大,施亚夫的身份暴露,他再度被捕。这次判决十分严苛,他被处以15年的长期监禁,并被送往南京的毛虎桥监狱。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南京城笼罩在战火的阴影下,日军飞机的轰炸将整个城市推向了混乱的深渊。
就在南京陷入混乱的某一天,施亚夫所在的监狱因轰炸起火。大火瞬间蔓延,监狱内部乱作一团。
施亚夫与其他犯人趁乱四散奔逃,他在混乱中竭尽全力避开敌军的搜捕,终于找到机会脱身。
 直面日寇:组建守土团抗击侵略
直面日寇:组建守土团抗击侵略1938年,日军在南通大规模登陆后,当地局势迅速崩塌,一片混乱。
占领迫使大批百姓流离失所,南通很快沦为日军的占领区。
施亚夫联络了一些愿意站出来抗日的旧部以及当地的爱国青年,组建了一支名为中国工农守土团的抗日武装。
守土团初创时力量十分有限,成员主要由一些散兵游勇和零散的地方武装组成,规模仅有数百人,装备更是十分简陋,大多数人只能拿着老旧的步枪和寒酸的冷兵器。

在频繁的行动过程中,施亚夫主动寻求与中共地下组织的联系,通过这些渠道,他逐渐与新四军建立了联系。
施亚夫利用这一关系,不断从新四军那边获得技术指导,甚至在一些战术安排上得到更为具体的帮助。
此外,还有一定数量的物资开始分流到守土团手中,有力支撑了这支队伍的生存和发展。

到1940年初,施亚夫经过组织安排,伪装成顺从者,被派任南通县伪政权中的宪兵队和特务队负责人,这一表面上的伪职使他迅速转变了抗战的方式。
他得以进入伪政权高层的核心区域,成为敌内部的“钉子”。
施亚夫以极强的隐蔽性,在日常的工作中积极表现,从而逐渐获得敌方的信任。
 从伪军师长到地下情报员
从伪军师长到地下情报员1941年,施亚夫所部被正式改编为“绥靖军第七师”。
从编制上看,这支队伍成为了汪伪政府名下一支成建制的地方武装,但所谓的“第七师”不过是个幌子,底下的实际力量远不如名字听上去那般体面。
当时队伍加起来不过区区两三百人,距离标准的师级建制差得远,还得靠多方拼凑的老旧装备才能勉强维持日常操作。

不久之后,汪精卫派他的得力心腹严济南抵达南通,试图对施亚夫所部进行实质掌控。
严济南到达后,直接提出要对“七师”兵员进行全面统计,这使得施亚夫意识到让“七师”以现有规模面对严济南是行不通的。
于是,他迅速与身边的心腹展开商议,制定了一套详细的计划。

在短时间内,施亚夫巧妙编造了一个虚构的花名册,将原来仅有几百人的队伍“扩充”到1.5万余人。
他不仅在册上排列了“虚拟士兵”的姓名、职务、军衔,还细致到每个人的口粮标准、武器分配,甚至连各连队之间的调度状况也一并备注清楚。
这份虚假的花名册被做得天衣无缝,足以让人信以为真。

严济南接过这份厚厚的花名册,顺着纸面匆匆翻阅,他甚至没有仔细核对,就对“第七师”的编制规模深信不疑。
此后,他带着完整的报告匆匆返回南京,把所谓的“1.5万大军”呈交给汪精卫。
不到几天,施亚夫便接到了命令,正式被任命为伪绥靖军第七师中将师长。
他身居高位后,更加巧妙地利用身份,对日伪展开了隐秘的情报战。

施亚夫利用自身的位置,将大量日军和伪军的核心信息秘密传递给新四军。
在缴获的文件中,有的记录着部队调动的详细时间,有的标明了补给线的路线图,还有一些甚至涉及“清乡”计划的核心内容。
这些情报每次都通过隐秘的渠道流向新四军,使敌方多次在关键的作战行动中遭遇挫败。

施亚夫的这些神操作没有一直掩盖过去。
到了1943年春,一些诡异的迹象引起了日军驻南通高级军官小林信男的注意。
敌人发现,不止一次的新四军作战行动能够准确预判日伪的攻势,日伪内部开始怀疑绥靖军可能有问题。
为此,小林采取了一系列手段,包括全面排查高级伪军干部的背景,将其与情报泄露的时间点进行比对。
最终,伪第七师的活动被列入了重点审查名单。
 被揭身份的危机
被揭身份的危机1944年初,小林信男已经开始对施亚夫的身份产生明显怀疑。
1月2日当天,施亚夫仍按惯例巡视着部队的日常防务情况,当晚九点,他结束查哨回到了驻地。
刚刚推开门,还没来得及脱下外衣,就遇到了副师长范杰的夫人潘宜娟。

潘宜娟告诉施亚夫,当天下午她去参加一场聚会,位置是在师长田铁夫家中。
席间几名伪军高层官员一边打麻将一边闲聊,其中有人提到,最近小林信男已经掌握了一些关键线索,怀疑施亚夫的背景不单纯。
这些线索直接涉及他早年红十四军的履历记录、他曾担任南通共党组织部长的历史,以及目前仍有人认为他正在与新四军保持秘密联系。

施亚夫听完后,脸上表情毫无变化,没有丝毫慌乱的迹象。
他平静地回应了一句,以轻松的语气打趣说起了“天下同名同姓的人不少”的话题,似是在刻意淡化内容的敏感。
实际行动中,他非常迅速地通过秘密渠道向新四军苏中军区发出了一份简短而明确的电报。

苏中军区收到情报后,立即展开分析,并快速与施亚夫商讨应对策略。
施亚夫很快与组织取得线下联系,参加了一次机密会晤。
与他接头的是新四军的一线领导,包括叶飞在内的几位军区主要负责人。
叶飞与三行署主任朱克靖亲自商议后,向施亚夫传达了最终决定:在1月11日,施亚夫必须率部起义。

施亚夫完全接受了组织的命令。他在会面中没有提出任何质疑或异议,坚定地表态将准时执行计划,以确保潜伏多年的成果能够在适当时机化为实际行动。
而组织方面也为这次起义制定了初步的行动框架,并承诺提供必要的配合,比如在关键地点的接应及随后的战略安排。
 起义风暴
起义风暴就在施亚夫与组织联系制定起义计划的几天后,新情况迅速浮出水面。
多方情报表明,伪三十四师的日军教官小林信男已经察觉到队伍内部的不稳定因素,并打算采取行动。
最为关键的情报是1月6日小林将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对施亚夫麾下仍忠于抗日的残余力量进行全面清洗,这将严重威胁起义的进程甚至施亚夫自身的安全。

施亚夫迅速调整计划。原定的1月11日期将战略性起义提前至1月5日,并通过多种方式将这个决定传达给相关成员。
他亲自协调资源和人力部署,同时谨慎得当地伪装起义准备工作,以防引起日军和伪军高层的疑心。

1月5日深夜,南通城逐渐恢复平静,大多数伪军士兵已经按照惯例各自归营休息,城内显得异常安静。
施亚夫以正常的夜间巡逻为掩护,亲自带着数十名可靠部下秘密活动。
他首先解决了困扰最大的戒严问题,提前打探负责戒严的具体兵力和布防情况,并调动内部人员巧妙削弱了几个关键点的守备力量。

起义队伍最终在凌晨时分集结。
为了保证行动的突然性,施亚夫并没有让大部队贸然前往重点目标。
他带领一支伪装小队,借着夜色直奔南门。
当他们抵达城门时,负责值守的数名哨兵以及一名值班军官对这支队伍的行动显得有些疑虑。

毕竟当时南通城门已经严令戒备,人员和车辆均不得随意进出。
施亚夫凭借自身的高阶军衔和熟稔的伪装身份,迅速镇住了当值军官。
他以“受命执行紧急军事任务”为理由,顺利通过了对方的质询。

施亚夫率领的这次起义在日伪高层中引起了巨大的震动。
由于起义行动切断了伪军大量兵力部署和互相调度的命脉,仅用一个晚上便重创了伪三十四师的中坚力量。
与新四军汇合后,施亚夫的起义部队迅速被整编并投入到抗日战场中。
在施亚夫带头起义的感召下,仅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时间内,周边地区就有大量伪军投向新四军的怀抱,据统计,仅1月至2月间,反正的伪军便突破2000余人。
参考资料:[1]傅宗哲.施亚夫的传奇人生[J].铁军,2011(2):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