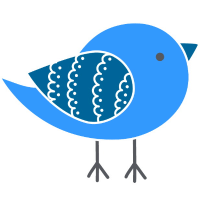五.机械灭螺队

负责管理岳阳氮肥厂筹备处家属子弟参与劳务的,是一位姓方的工程师。方工是一位大家都喜欢的老好人,他时不时来工地照看下我们这帮孩子,他十分担心我们的安全,同时他又负责与岳阳城北基建队沟通和联系,他担心基建队会不会剋扣我们的工钱。而且他还时时为我们这帮挑土石方的孩子,尽可能争取该得到的劳动福利和待遇。他知道我们这帮孩子在这儿挑土石方都是暂时的过渡,随着工厂各项工作的完善,今后我们之中该进厂的会进厂,该下农村的会下农村。方工和江工关系也不错,所以他对我也挺关照的。再说,我与厂里这班孩子不同,我是要靠挑土石方生存的,那些孩子则大多是赚两个钱或补贴家用,或做自己的零花钱。所以,整个劳动中我是最卖力的,无论干计件论方的挑土石,或临时抽去干计时的其他活,我在这班孩子中都是表现最好的。因此方工也很喜欢我,信认我。只要他离开工地,他都要叮嘱我,照看好这班孩子,千万别出什么安全事故。
方工是资江氮肥厂调来的,那是国家为备战而在湘西新化投资建设的一座生产化肥的工厂。那里地域偏远,经济落后,方工对穷困有切身感受,所以他对我有种本能的同情。
岳阳城北基建队主要承接的土石方工程,是大型机械开山劈岭后留下的一些死角,机械不便操作,只能人工来挖掘搬运,所以基建队的活计很零散,常常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在城北基建队我除了挑土石方,还常被抽去抡大锤打炮眼,装炸药,点火放炮。七里山的丘陵大多是花岗岩结构,大型机械留下的死角往往是一个个花岗岩的土堆,所以必须先炸掉这一个个土堆,然后再把炸松的土石方挑走铲平。当时开山劈岭的大型机械作业的队伍有好几拨,其中一支队伍便是岳阳市血吸虫防治站的机械灭螺队。
今天很多人对“血吸虫”病已经很陌生了,不知道血吸虫是什么样的病虫害,如果读过毛主席曾写过一篇名为《送瘟神》的七律诗,就会对血吸虫有所了解。洞庭湖区是血吸虫泛滥成灾的地区,水草沼泽地,湖边滩涂,芦苇地里都是血吸虫寄生的地方。血吸虫寄生在一种水生物钉螺中,这种钉螺繁殖快,生命力强。人被血吸虫感染了是很痛苦的,小孩生长发育受阻成株儒,妇女不能生育,青壮年丧失劳动力。得了血吸虫的病人吃得多,饿得快,肚子大,面黄肌瘦不成人形。所以在八十年代以前,这种血吸虫病是湖区重点防御的病虫害。岳阳血防站的机械灭螺队的任务是在春秋两季开进湖区翻耕土地覆盖钉螺消灭血吸虫,冬夏季节便承接大型的土石方工程开山壁岭,推土填坑。
方工是负责厂里基建的工程师,统筹安排七里山机械队的土石方工程。岳阳血防站机械灭螺队进驻七里山基建工地后,亟须要一个随队的饮事员,负责队上近二十个司机的饮食。于是方工找到我,问我愿不愿当饮事员,能不能办好近二十个人的三餐饮食。那时岳阳城北基建队的活不稳定,常常是干三天要歇两天,而我要生存要挣钱养活自己,所以我很想找一份稳定一点的工作。我曾跟方工透露过我的想法,方工同情我的处境,他也把我的事放在了心上,时时留意并打听看有没有机会和适合我的事情。方工这一问,我不假思索就立马答应了,我当时想,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啥活不能干呢,只要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
于是,第二天方工领着我去了机械灭螺队的临时驻地,灭螺队大多是年青小伙子,只有少数几个中年人。灭螺队大约有七八台推土机,每两人一台,轮班作业。我每天要搞四餐饭菜,因九点钟下晚班的师傅也要吃一餐饭。队上专门配了一个会计兼采购员,由他采买每天的蔬菜米面和油盐酱醋。饭菜也不复杂,蒸缽子饭,炒两个菜,一荤一素。其实这之前我是没干过饮事员的,在豫东老家四姐姐去长沙后,基本是我做饭,但简单得很,杂面锅饼和窝窝头,擀面条。我们四兄弟向南跋涉首站江北水乡,我们寄居在会计厨房里,在会计家的锅台旁搭砌了一个小灶,仅架了一口铁锅,闷饭、炒一个蔬菜或吃咸菜,伙食也简单。在株洲挑炉渣时,我和三弟都在厂里食堂买饭菜吃,很少自己做饭。现在一餐要做做近二十个人的饭菜,我刚开始还是有点怯场的。好在会计兼采买的是个和我同样矮小的退伍军人,他鼓励我不要怯场,慢慢来,他会帮助我的。
想不到我还真是个当饮事员的料,第一天当饮事员就获得了队上师傅们的肯定。蒸缽子饭我在道湖二舅舅家早见过,把淘好的米用杯子舀到缽子里,然后添上烧开的水,水添多少决定饭蒸得干和稀。炒菜我在江北水乡干了大半年,只是人多人少炒多炒少的区别罢了。放油放盐试着来,何况母亲早说过,油多不坏菜,多放点油,菜也好吃点。而且佐料多一点就能避腥避骚,菜式也好看许多,大多数人吃饭还是讲究色香味俱全的。总之,在长沙道湖在南城既看过母亲炒菜又吃过母亲炒的各种菜式,难不成我还会蠢到不会比照葫芦画只瓢吗?这辈子我对生活体会最深刻的便是,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在机械灭螺队做炊事员的第一天,可把我累得够呛。晚上九点做完最后一餐饭,我几乎是又睏又乏,腰都直不起来。但没办法还要洗碗收拾案板,还要准备好第二天的早饭米和菜。我当时觉得这饮事员的工作比挑土石方要繁杂多啦,事无巨细,悉悉索索,几乎没有一点歇憩的时间,还不如挑土石简单惬意。好在队里的师傅们全都是从农村来的,他们不但不挑剔,而且还很宽容。饭蒸硬了硬着吃,饭蒸烂了烂着吃,菜咸了少吃点,菜淡了加点盐。当然我也在一边择菜洗菜切菜的同时就用心想着,如何能把这样菜炒得好吃,让队上师傅们吃饱一点。慢慢地我摸索出些炒菜的门道出来了,而且我还买了本关于烹饪菜肴的书,不断翻看不断实践。十天半个月之后,我竟像模像样地把队上二十来人的饭菜做得熨熨贴贴,很少手忙脚乱了。当然我最怕的是烧煤灶这一关,我怕捅不好煤灶,影响火力蒸不熟饭,炒的菜不好吃。我又怕煤烧不干净,浪费了煤增加了火食的费用,于是我把煤和得很熟,蒸饭时我反复观察火势,遂烧煤这一关我也过啦。
灭螺队长和会计都是退伍军人,军队的生活把他们都磨炼成了品行好,见识广,格局大,有修养的好人。我这辈子在与人交往中,体悟最深刻也便是人性,我以为人性的好坏是决定一个人在人际中,在个人事业中能否获得好名声,能否获得成功的关健,而凡从部队中走出来的人,绝大多数人性善良宽厚,工作踏实肯干,所以,在人际交往中,他们比之一般人要好打交道些。机械灭螺队长姓汤,中等个瘦削脸,明眉大眼高鼻,乐观豪爽,大度宽厚。汤队长整天乐哈哈笑盈盈的,讲话中气十足,队上的工作安排的妥妥当当,大家都服他所管,听他的调配安排。会计兼采买,小小个白净脸,眼睛不大却光彩照人,细声细气却语调清晰,聪明智慧甚至有几分狡狤,而且还十分风趣会宽人心,别人做错了事,搞砸了场面,他一脸堆笑几句宽心的话语,于是一笑之间就泯灭了烦恼。他姓郭,大名叫郭能源,真正是能够为大伙添能量,找寻财源的好当家。
灭螺队驻地的隔壁是氮肥厂筹备处的临时幼儿园,和我们的工房子在一个院落里。幼儿园有几十个年龄大小不等的孩子,大的大约四五岁,小的刚刚蹒跚学步,咿咿呀呀还不会说话,一个个天真可爱。这些天真可爱的孩子给我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无尽的欢乐,我每每把饭蒸上后,一边择菜一边逗他们玩,我还给他们唱歌讲故事。这下好啦,我身边吸引了一大群可爱的孩子,我要去洗菜切菜炒菜啦,他们还粘着我,我只好喊阿姨来领开他们。阿姨笑着对我说,这个小师傅,你太可爱了,跟这帮孩子这么有缘,唱歌讲故事给他们听,他们都离不开你啦,我们要向厂里申请给你发工资呢。我也笑看对阿姨说,好呀,下一步我就教这些孩子做饭啦,让他们也当个小小的饮事员。那段时间我虽辛苦,但却是最开心的,我整日歌声不断,感染了幼儿园的阿姨和可爱的孩子们,也感染了灭螺队的师傅们。
灭螺队这些师傅全来自农村,平日里推山劈岭,修机车,一身汗水一身油汚,下班吃饭后就睡觉,沒有文化生活,没有生活的乐趣。我的歌声竟然产生了神奇的作用,他们也都开始啍哼起来,或唱歌或唱花鼓戏,一片欢乐融融的气氛。汤队长很高兴很真诚的对我说,小齐你这个开心果还真效,你看你给我们灭螺队这班小青年带来这么多快乐,他们工作干劲一下子高涨起来,我们的任务也超额完成了。郭会计也凑上来说,小齐呀还真是不错,现在都不要我买菜费神了,你看他每天安排我买的菜,写得清清楚楚的,这字写得比大学生都写得好哩。我听了他们的夸奖,别提心里多高兴啦,我那时就在想,要是能在灭螺队长期当饮事员多好。在豫东老家的苦难和压抑,从豫东老家出来后的飘泊辗转,江北水乡的辛劳,挑灰渣担心居委会派出所的清查,只有在岳阳才有一种稍事安定的劳动生活,虽辛苦但却是十分愉快的。
我在灭螺队当了一段时间的饮事员后,我和几个年青的师傅很快就成了朋友。其中一位年青师傅叫李庆秋,个子高但身板单瘦,长得很帅气。虽说是从农村来的,但他的帅气毫不弱示城市里长大的帅哥们。也许是长期在机车上少晒太阳的缘故,他肤色白皙光亮,眉清目秀,头花墨黑,十指修长如洁白的葱管,笑起来露出两颗白亮的虎牙,煞是逗人喜爱。人的长相颜面,历来就是人们交往的敲门砖,人们首先看的就是面前那张漂亮帅气且和颜悦色的脸面,李庆秋就长着这样一副让人看着舒服喜爱的脸面。我们成为朋友后,只要有空闲,俩人便粘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李庆秋和郭能源会计还沾点亲带点故,他们都是岳阳乡下的。李庆秋和人说话往往还有几分腼腆,笑起来脸上两个不大的酒窝如新月般斜飘在白净的脸膛上。交谈中他为我普及了岳阳本地的许多民风民俗,古迹典藏。他还答应有时间要带我好好转转整个岳阳的湖光山色,风景名胜。但直到我后来离开岳阳,我们都没有兑现这一愿望。
李庆秋还在七里山这儿邂逅了他心上的姑娘,其实是这姑娘的母亲看中了李庆秋这个帅气又朴实憨厚的女婿。我们驻地原是岳阳七里山人民公社,因75年决定在这儿兴建氮肥厂,这儿的村子都陆陆续续搬迁去了它乡。李庆秋的岳家可能还没来得及搬迁吧,再说由于兴建厂子,筹备处征用了许多民房,李庆秋岳家的房子院落都被厂里征用了,他们自家倒挤在院子里一处厢房中生活。李庆秋的岳家与灭螺队的驻地相距不远,师傅们去开机车推山劈岭的工地就在他们家的屋后。也许是李庆秋帅气的模样,也许是这个大男孩朴实腼腆的作派被李庆秋未来的岳母细心观察了许久。于是李庆秋的岳母便托郭会计撮合这门親事,当然郭会计也是欣喜若狂。女看上郎,十之八九这门亲事就妥了。李庆秋这位心上的姑娘,也是位长相甜美,性情贤淑的好姑娘,且又是家里的独女,她有两个哥哥均已结婚成家,分开独过。那次郭会计领着这姑娘到灭螺队的驻地,大伙都只夸这姑娘长得好看,有修养懂礼数,都羡慕李庆秋好运气,好姻缘,对方这么好的条件,这是打着灯笼都寻不到的好事,咋就偏偏被李庆秋遇上了呢。
一场秋风一场秋雨,初冬季节便在洞庭湖区拉开了帷幕。苍穹茫茫,铅云密布,雪白的芦花一团团一朵朵如漫天的飞雪在洞庭湖滩涂的千里芦苇丛中飞扬起舞,又随着初冬的寒风朝波涌浪翻的湖面飘去。灭螺队接到岳阳血防站的调遣布署后,遂将七里山的工程日夜加班完成了。于是数辆大卡车装载着七八几台推土机挖掘机开往岳阳城北大型轮渡,准备开拔洞庭湖区去翻土灭螺。我也和电影中起锅拔寨,收拾行囊的战士一样,把锅碗瓢盆,案桌砧板打包装车,随同机械灭螺队前行。我兴奋得像只快活的小鸟,心儿早飞去了洞庭湖畔那天光云影,古树掩荫,芦花飘飞的广阔湖区。的确,我与洞庭湖无边的芦苇太过有缘,当初在江北水乡砍芦苇,背芦苇,那时繁重艰辛的劳作,让我对芦苇有一种漠视的心绪,可这次要去洞庭湖的腹地去深翻土地埋葬血吸虫这怆害人们的瘟神,我脑海中首先浮现的却是那无边无际站立在斑烂秋色中的芦苇。那一望无际的金色芦苇和上下翻飞的洁白芦花,它们在浩荡的湖风中,在苍茫的天穹下,嘻戏欢唱,摇曵多姿,无拘无束舞着大自然最优美的姿态,随波逐浪,昂首向天。
汤队长笑看对我说,你就乐吧,高兴吧,到了洞庭湖你就会哭鼻子都来不赢的,三两个月难见一根青菜,死鱼烂虾是最好的菜肴,哈哈哈,到时只怕你连一支歌都唱不出来了。别听老汤的,有我呢,我还不是会隔三差五的来岳阳城购粮买菜的,郭会计接过汤队长的话安慰我说。嘿,你还真别说,汤队长讲的都是实情,郭会计讲的也没错。但郭会计讲的只是亦无风雨亦无晴的美好日子,他会隔三差五的跑岳阳城为在洞庭湖腹地的灭螺队采买粮食和菜蔬,让灭螺队师傅们吃饱喝足去深翻泥土,埋葬钉螺把千万瘟神送往西天。“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这是毛主席的美好愿景,他老人家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广阔而慈悲的情怀希望把洞庭湖被血吸虫困挠的百姓度上幸福的天堂。郭会计无疑比汤队长更具这种浪漫的军人情怀,他的安慰又现实吗?
然而一进入深冬季节,洞庭湖便是风雨送冬归,大雪送冬到,阴风怒吼,雨雪霏霏,天寒地冻,难见晴日,轮渡停摆,车马不行,更别说郭会计会隔三差五地来岳阳城置办补给了,就连飞鸟都不再飞越寒天冻地,飞过苍茫的芦苇,而是倦宿在芦苇丛中,啾啾避寒。我们灭螺队粮油告急,就真正只能熬稀粥,烤鱼虾拌盐水艰辛度日啦。我随机械灭螺队奋战在洞庭湖区的时候,正是1976年的深冬季节。那一年是中华大地的多事之秋。一年之内周总理、朱总司令、毛主席三位伟人逝世,三颗巨星殒落,已经让在十年文革的苦海炼狱中受煎熬的中国人民对四人邦深恶痛绝,但四人邦却在做着最后穷凶极恶的挣扎,政治形势极为严峻,阶级斗争的弦越崩越紧。先是天安门广场首都百万民众发动的清明悼念周总理的纪念运动,被四人邦疯狂镇压,再后来是十月一声惊雷,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四人邦的全面反击,终于结束了十年天怨人怒的大动乱,让文化大革命这场对苦难中华的人为大浩劫永远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架。
搞不清岳阳血防站为何撤换了汤队长,郭会计,他们俩人实在与文革与“四人邦”毫无任何瓜葛。血防站派去了机械灭螺站的钟副站长亲赴并督促灭螺队开展紧张繁忙而万分劳累的翻耕灭螺任务。机械灭螺队由两班作业变为三班作业,昼夜不息,轮流上岗。队上从站里补充了部分年青的机车司机,充实灭螺队的力量。我的饮事工作也繁重了许多,站里派了一个年近五十的会计兼伙食管理员,姓王,我们称他老王,巧得很钟副站长和老王他们俩都是转业军人,而且都是资深的老党员。同时站里还派了两位临时招来的小青年,充实饮事班的工作。当然对我而言,我不希望这次灭螺队的人事变动,我和汤队长郭会计已配合密切,关系融洽。两个月对我的炊事锻炼,我的厨技也精进不少,我做的饭菜也得到了灭螺队师傅们的交口称赞。但在抓革命促生产,“两个凡是”的政治形势下容不得我个人愿不愿意的。不过,让我喜出望外的是,钟站长,王会计却是再好不过的人,和他们相处,你只要是尽心努力地工作,他们都会给予你最大的支持和帮助。即便你不小心出了差错,他们都为你承担,为你开脱,安慰鼓励你。当然这差错绝不不可能是一个小小的炊事员,去反党反人民,去拿石头打青天一类匪夷所思的蠢事。
在洞庭湖灭螺最艰苦的日孑,诚如汤队长所言,但比汤队长描绘的更艰苦十分。一连数日洞庭湖区,朔风怒吼,大雪纷飞,天寒地冻,冰冷彻骨。机车被冻坏了水箱,机油冻成了冰块,整日都要一锅接锅的烧开水温水箱化机油,常常是机车打不着火,发动不了。但任务是硬指标,每台车要翻耕多少亩地,是上面下达的任务,只能超额不能减少。厨房工作更是艰巨,湖区出不去也进不来,粮油米面蔬莱肉类补充不了。怎么办,钟站长便组织没班的机长们破冰抓鱼,又组织他们挖深埋在地里的嫩芦笋。两个新来的小青年整天跟着我熬稀粥,破鱼肚,淹咸鱼,剝芦笋。盐倒是储备不少,但食油却不够,煎不了鱼就火焙,炒不了菜就盐渍。一碗稀粥两块火焙咸鱼,一筷子盐渍芦笋,遂一吃就是半个多月。天一放晴,老王便拨开一排排芦苇探路径,想方设法冲出湖区,去岳阳城里采买粮油菜蔬。
在那段苦塞的日子里,发动不了机车,干不了话,年青的师傅们就拥被而坐,在四面透风芦秆搭的茅棚里听钟站长读旧报纸。不听不听,这旧闻耳朵都听出茧子来啦,钟站长讲点别的吧,比如你和你老婆在床上的风流,那才是新闻呢,哈哈哈。要不让小齐讲故事,他讲故事绘声绘色,可好听啦。
钟站长咳嗽两声便说,那好,你们也别喝粥啦,小齐要跟你们熬粥焙咸鱼呢。要不把小齐讲过的故事,你们再讲讲,一个个来,看你们这群平日里的泼皮猴,哪个记性最好。谁先来!
我来,你们听着:十七八,十八七,十七八的大闺女,她没过门,想女婿……
想女婿干啥,贺国红,你都把老子裤裆里的东西都讲昂头啦,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