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关于西方伪史论的讨论很多,这个讨论最初的起因是西方的一些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对于某些历史产生了疑问,这些疑问引发了其他各国学者以及爱好者的进一步研究,结果这一研究不要紧,居然发现教科书上的西方古代史疑点重重,简直可以说是千疮百孔。
这些疑点汇总起来,单单摘要大概就可以写一本书,简单整理一下争议较大的疑点:
1,亚里士多德是否真实存在?这位西方历史上的圣人一生著作等身,写下超过1000万字的著作,流传至今天的有300万字,为何却没有一件真迹留存?

要知道1000万字的工作量很大,今天的高产写手,如果不是善用剪切粘贴的话,一天最多最多也就是8000字左右,不过那还是在写无脑小说之类,如果是严肃的学术著作,一年能写出20万字的都算是非常勤奋了。
这样算的话,亚里士多德如果是独自完成这些著作的话,需要持续高强度工作50年以上,这可能么?或者是他口述,有助手记录?总之疑点很多。
另外,亚里士多德这么多作品,是写在什么材料上的?按照西方史的记录,当时只有两种可能的材料,来自古埃及的莎草纸或者希腊自产的羊皮纸。
如果用羊皮纸书写的话,按照金灿荣教授的算法,大约需要十万只羊的皮,这需要杀掉全希腊的羊,大约是不可能的。。。
再说无论是莎草纸还是羊皮纸,这样大规模的制造一定是有遗址遗迹的吧?凡是大规模的历史活动必有踪迹可寻,可是关于亚里士多德的纸张,无论场地,工具,工艺,主料,辅料,统统完全彻底地湮灭在历史当中,连根毛都找不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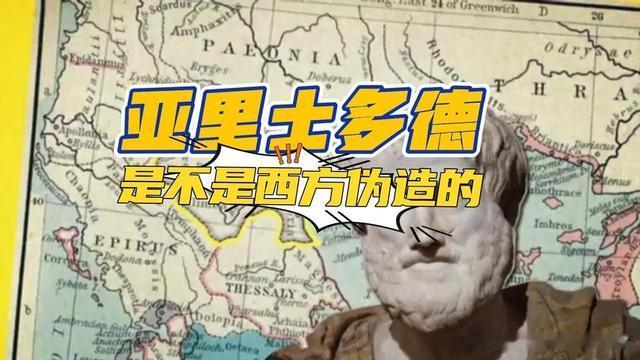
2,达芬奇是否真实存在?他书中所绘制的多个图样为何与中国元朝的《农书》高度相似?
达芬奇是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文艺复兴则是现代西方的起点。按照历史的记载,达芬奇可以说是天赋异禀,没有读过多少书,从一个作坊的学徒自学成才,成为了学究天人的一代大家,学问上通天文,下接地理,无所不包。。。

就是这样一位神人,如果你去研究他的生平,就会发现疑点太多了,他的身世,他的学问来源,他的结局,统统是语焉不详,令人费解。
关于这些相关的文章很多,网络文章包括严肃论文都有不少,有兴趣的读者很容易查到,这里就不展开讨论,只是特别说一下他著作当中的一些雷同。这些雷同如果是发生在今天的论文之中,必然会被以抄袭论处。
这些雷同,是被英国历史学家加文·孟席斯给扒出来的,他在《1434:一支庞大的中国舰队抵达意大利并点燃文艺复兴之火》一书中宣称,达芬奇在其著作中所绘制的那些令后人震惊无比的机械结构图,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和中国元代的《农书》高度相似。达芬奇所做的工作只是将这些图纸通过三维立体的方式重新画了一遍,然后署上了自己的名字。

孟席斯进一步查证出,《农书)以及其他文献,都是在1434年由一支中国舰队带到欧洲的。当时由4艘船组成的舰队抵达了意大利的威尼斯,给当时仍处在蛮荒时代的欧洲带来了当时最先进的地图、天文图、各种科技典籍,百科全书以及其他资料,这些资料当时由中国舰队的特使转交给教皇尤金四世。因此孟席斯认为,后来泽被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实际应该归功于中国人。而所谓文艺复兴三大家之一的达芬奇,不过是将当时来自东方的信息改头换面而已。
达·芬奇生于船队到达欧洲18年之后的1452年,达·芬奇关于这方面的信息来自于其前辈塔科拉和弗朗西斯科·迪·吉奥,而吉奥等人的信息来源就是中国舰队带到意大利的这一批科技典籍。关于这一重传承关系孟席斯经过了详尽的验证,他仔细对比了这几人著作中的相关内容,并和《农书》以及其他中国古籍中对应的部分进行比对,不能说是基本一样,只能说是完全一样。
这些雷同的部分主要集中在机械设计部分,包括攻城武器、磨坊和抽水机等。

3,航海大发现是否真的由西方主导?还是根本就是郑和舰队的功劳?
航海大发现通常是指在15世纪以来,人类不停探索海洋和世界的进程。由欧洲到达东方,由欧洲绕过非洲抵达印度,尤其突出的是尝试并完成全球航行的麦哲伦和哥伦布。正是因为这些前仆后继的努力,人类对于地球的认识才掀开了全新的一页。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么?
还是那位英国的史学家孟席斯,他在更早的一本书《1421:中国发现世界》之中就已经论述过,很可能最早完成环球航行、最先发现新大陆的并不是欧洲人,而是明朝早期的中国人。

孟席斯这个结论最直接的证据是一份名为“天下全域总图”的地图,此图是根据1418年的“天下诸番识贡图”绘制而成,反映了当时各地蛮族向明成祖进贡的场景。在这份地图上,有关欧洲,美洲,甚至大洋洲的一些地名已经标注出来,并且地图有明显的中国地图绘制的特点,即有蓝色的波纹线。
由此孟席斯认为,这份地图上所标注出来的地点,应该是15世纪郑和舰队远航时曾经到过的地方。从1405年到1433年,郑和率领远洋船队先后进行了多次的海上远征活动,其足迹遍布西洋各国,曾到达红海沿岸和非洲东海岸,这些都是有据可查的。孟席斯结合其他史料进一步推断,郑和的远洋船队在1421年就已经到达了美洲,这个时间比哥伦布要早将近70年时间。
关于郑和首先发现美洲一事,西方史学界有很多不同声音,多数的论据是指出天下全域总图根本就是一份伪造的地图,是后人根据同时期的欧洲地图,把地名译成中文,改头换面而成的。。。
这就比较有意思了,所以本文由此展开,谈一谈历史上和地图有关的另一段公案。
这一段公案同样发生在明朝,公案的主角名字叫做《坤舆万国全图》。

何为“坤舆”?中国古代以乾为天坤为地,舆的意思是车的底座,可以引申理解为承载万物。
在中国古代称地图为舆图,就是表示地上承载万物之图,而以“坤舆”二字冠名的地图,就相当于今天俗称的世界地图。
这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份比较清晰准确的世界地图,成图于明万历年间,距今已有400多年。
关于这份地图的作者,一般认为是明代科学家李之藻等人,他们利用了欧洲传教士利玛窦从西方带来的地图以及地理信息为依据所绘制而成。
所以一度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的历史书中,关于这份地图的作者都标明是李之藻和利玛窦等,也默认利玛窦对于这份地图居功至伟。

真实的历史如何呢?
先说结论,利玛窦并不是《坤舆万国全图》的原创作者,《坤舆万国全图》成图所借鉴的那些原始地图一部分是明朝的早期档案,另一部分确实是利玛窦从欧洲带过来的,不过即使这一部分的原始作者也不是欧洲人。
所以《坤舆万国全图》和利玛窦有点关系,但是关系不大,和欧洲则全无关系。
如何认定《坤舆万国全图》的原图和利玛窦无关?
认定利玛窦并非此图的原创作者,源于一位香港的学者李兆良。在他的同名著作《坤舆万国全图解密》中,指出了几个重大疑点,并由此确定利玛窦不可能是《坤舆万国全图》的原创者。
第一个疑点是关于欧洲尤其是意大利的部分,描绘得非常简陋,甚至有不少错误,而其他地区,尤其是中国的部分,则非常清晰完整。如果这是利玛窦依据欧洲地图的原创,很难理解他对自己的家乡了解极少,反而对刚来了几年的中国异常熟悉。

第二个疑点,此图中出现的大量地名,在同时期的欧洲根本没听说过。比如‘哥人河’,就是今天的哥伦比亚河,欧洲直到200年后才发现了这条河;比如加拿大北部的哈德逊湾,直到几十年后才被欧洲人亨利·哈德逊首次探索;比如非洲中部的“齐历湖”,也就是今天的坦噶尼喀湖,这个湖直到1858年才被英国探险家“首次发现”。在16世纪的欧洲地图上,整个非洲内陆几乎还都是一片空白。。。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根据李兆良的研究,在《坤舆万国全图》中,有超过一半的地名从未在同时期的欧洲文献里出现过。
第三个疑点,此图中出现了一些以前使用的地名,实际上在此图绘制时已经改用新名字。比如在《坤舆万国全图》中标注安南的区域特别加上了”旧交趾“这样的备注,而“交趾”改称“安南”这一事件发生在1428年,距离利玛窦绘制地图已经有将近200年,交趾这个名字早已经是陈年往事,特别标注备注在地图上非常奇怪;在 “三佛齐” 备注 “旧港宣慰司”,在 “大爪哇” 备注“元兵曾到擒其王”,同样的问题还发生在茶马古道和蒙古的一些地名,都做了详细的新旧地名的比对和备注,而这些变化也都在将近200年前,很难理解身处晚明的利玛窦会对那一段的地理沿革如此了解,并且只是对那一段特别关注。
第四个疑点,这份地图对于中国区域的测绘是非常精准的,这不可能是个人在短时间内能完成的事情,只能是举全国之力历经多年,才有可能完成。从这个角度来说,利玛窦和他的小团队既没有可能独立完成,也不可能有欧洲的先人给他提供如此详尽的原始资料。

那些原图来自于哪里?到底是谁绘制的?
根据李兆良先生的研究,这张地图的核心内容并非来自欧洲,而是明初郑和船队环球航行的成果。做出这样的结论有以下几个理由:
一,图上特别标注出来的地点,其新旧地名转换的时间都集中在明永乐年间,也就是郑和远洋航行的前后。从逻辑上说原始地图有很大可能出自郑和团队;
二,图上的很多海外的地名,明显带有中国人音译的特征。比如上面提到的”哥人河“,还有“鹦哥地”,“白峰”,“厄蠡””等,基本都是按照粤语或者客家话的发音转译的美洲当地的发音;
三,李兆良先生发现《坤舆万国全图》中超过一半的地名从未在欧洲文献里出现过,反倒和《郑和航海图》等明代档案有高度相似之处,比如太平洋称为“沧溟宗”,加利福尼亚湾称为“东红海”,白令海峡标注为“冰海”等等;

根据现存的史书记载,郑和船队曾经七下西洋,最远到达了东非。李兆良先生根据研究认为,郑和船队或许曾经完成了环球航行,并且测绘出了全球第一份真正的世界地图。
虽然这个说法还没有得到学界的一致认同,不过确实是有一些史料和实物证据可以佐证这个观点。
从技术角度来说,郑和船队的规模相当庞大,领头的宝船长度足有140米,整个船队有200多艘船,人员多达将近3万,所有船只都配有水密隔舱,有记录证明船队拥有当时最先进的星象导航技术,所有这些足以支持船队实现跨越大洋的航行。其规模远超后来的哥伦布等船队,其航海能力也远远超出当时欧洲的水平。
从文献角度看,留存下来的记录中有“涉沧溟十万余里”之类的描述,“沧溟宗”正是当时对于太平洋的称呼,郑和去东非的话不可能从太平洋走,在这个方向走这么远,很有可能就是横跨了太平洋到达美洲。
从实物角度看,曾经在美国发现了一块“宣德金牌”,上面刻有“大明宣德委锡”的字样,这在时间上和郑和船队的远洋时间也是吻合的;另外在秘鲁的印第安部落中发现的“亚洲象石雕”,以及在北美原住民处发现的“青龙旗”等文化遗迹,这些都说明早在明代初期,中国人就曾涉足美洲大陆。
另外,有一些特殊的工艺及物种的流传,也说明了中国和美洲之间在那个时间是存在交流通道的。比如玉米流入中国,以及中国陶瓷流入墨西哥,都是在那个时期发生的。

为何《坤舆万国全图》的作者曾经被普遍认为是利玛窦?
这个就要从利玛窦这个人说起,马泰奥·里奇(Matteo Ricci),中文名字利玛窦,号西泰,又号清泰、西江等,是以天主教耶稣会神父、传教士、学者的身份来华,1582年后,长期居留在中国,在广东,江西,南京,北京多地生活,利玛窦对于中国文化了解颇深,可以阅读中国文学并乐于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他和各地的一些士大夫交往甚密,颇受他们的敬重,尊称利玛窦为 “泰西儒士”。
作为西方派往东方的传教士,利玛窦1577 年到达亚洲。,1578 年 9 月到达印度葡萄牙占领的果阿邦,他在果阿和柯钦等地工作了四年后,于 1582 年 8 月到达中国澳门,后分别在肇庆、韶州、南昌,南京和北京等地生活。1610 年,在北京去世,终年五十七岁。万历皇帝赐以葬地,其墓在北京阜成门外,至今尚存。

按照利玛窦本人的说法,当他在广东肇庆期间,曾绘制了一份西方形制的世界地图,这份名为《山海舆地图》的作品引起了来访的士大夫们的惊叹,他们一方面对于这样新奇的地图绘制方式非常惊讶,另一方面也强烈要求利玛窦将其翻译成中文,并将中国放置到地图的最中央位置。这份中文地图出版后,给利玛窦带来了巨大的名声。他后来多年的至交好友徐光启就是在广东教书期间,通过这份地图知道了利玛窦的名字;
1599年他在南京期间,利玛窦又应当地的儒生朋友要求制作了第二版地图,第一版和第二版的正本及所有副本已经全部散失,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两版所有的正副本,在1602年之前就已经完全消失,并不是在后来慢慢湮灭的;今天世人所看到的是第三版,是1602年利玛窦在北京期间,应好友李之藻等的要求所作的。
第三版地图由三部分组成,椭圆形主图、四角圆形小图以及中文附注文字。

其中主图为世界全图,显示了五大洲的相对位置,中国位于全图的最中心位置。主图采用的是等积投影制图法,经线为对称的弧线,纬线则是平行的直线。山脉采用立体形象;海洋刻画则运用了中式地图常用的蓝色波纹。在主图的空隙处填写了与地名有关的一些备注说明,并简要介绍了地球知识与西洋绘图技法。
四角圆形小图包括在右上角的九重天图,右下角的天地仪图,左上角的赤道北地半球之图和日、月食图,以及左下角的赤道南地半球之图和中气图,另外还有量天尺图附于主图内左下方。
全图的文字,可以分为五类:一是地名,共有 1114 个;二是6篇题识,分别由利玛窦、李之藻、吴中明、陈民志、杨景淳、祁光宗署名;三是说明,包括全图、九重天、四行论、昼夜长短、量天尺、天地仪、中气、日月蚀、南北二半球等,是非常具备科学考古研究价值的资料;四是表,包括总论横度里分表,和太阳出入赤道纬度表等;五是附注,对各大洲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进行了简要的解说。、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除利玛窦自述以外,其他六篇署名题记中,都提到这份地图的主要作者就是利玛窦,并阐述了这份地图的由来,所述过程与利玛窦说的基本一致。
这也是为什么四百年来世人一直认为利玛窦就是《坤舆万国全图》的作者,直到李兆良先生提出不同观点,并展现了相关的证据。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关于利玛窦是此图作者的表述,已经在基督教以及严肃地图网站等介绍中消失。

利玛窦是有意冒名顶替的么?他的动机是什么?
利玛窦为何要这么说?利玛窦角色到底是原创作者,还是传播者,亦或改编者?
按照李兆良先生的推断,他认为这可能是明朝士大夫和利玛窦的一次合谋,真正的原始地图来源是藏在南京宫中的郑和船队的档案,因为这些档案在永乐之后不久,就宣称被销毁了。所以要想避开欺君的重大罪名,让这些信息重见天日的话,只能改头换面,套上利玛窦这个欧洲人的外壳,既可信又安全。

实际上在利玛窦署名的题记中,他确实曾提到编纂这份地图时曾参考了“中国通志诸书”,包括一些地方志。
通志也就是明廷官方所编制的百科全书,地方志书就是各个地方政府所编制的百科全书。中国历来对于这一类的记录非常在意,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每年都会拨出专门预算,委派专门的人员编制这些档案。这些文献对于研究历史沿革是非常有帮助的。
利玛窦在肇庆,南昌、南京等地居留期间,毫无疑问接触到了大量的地方志书,在留都南京,因为与高官焦竑的良好关系,他很有可能接触到了官方档案库中的历史文献。

至于是不是和官员们的合谋,这个不好说,只能说不是没有这个可能,明朝文官们瞒着皇帝做了不少事,并且废除船队,保留航海图等,这个确实和他们的核心利益相关,就是要把海贸的通道独家垄断在文人集团手里,当然这个是另一篇故事了,这里不再展开。
回到这份地图,个人的看法是,利玛窦应该是有一份原始地图的,也就是在肇庆期间就存在的那份第一版的《山海舆地图》,在第二版中,利玛窦确实借鉴了南京的档案以及各地的志书,进行了一些修正,而在第三版中,因为已经可以接触到北京的中央档案馆的文献,并且有一年之久,所以这一版的修正应该是比较充分的。
至于原始地图,虽然是利玛窦从欧洲带过来的,但是很有可能原创作者是郑和舰队,在1434年带去了意大利,这一点在上文中已经有所论述。
所以总结一下,郑和船队的一支曾经在1434年到访过意大利,把一些携带的中国科技典籍赠给了教皇,这其中也包括人类最早的世界地图。欧洲人在后来的一百多年里,消化吸收了这些知识,把一部分转化为达芬奇著作中的内容,地图则翻译成了拉丁文,并且按照西方绘图的习惯进行了改绘,同时把欧洲放置到了地图的中央部分。非常遗憾的是,因为当时欧洲并没有掌握精密的地图测绘技术,导致原始地图中的欧洲包括意大利的部分在100多年里并没有得到修正,仍然非常简陋,并且有很多错误。
等到利玛窦带着这份地图来到中国后,一开始可能只是希望拿这个做为敲门砖,借机拉近与士大夫的关系,事实上他达到了目的,徐光启等就因为这份地图和利玛窦结缘并成为好友。只是在利玛窦不断接触中国典籍和档案的过程中,他发现了这份地图后面的秘密,即这份地图和他在档案馆深处发现的那些170年前的记录是同一个来源,都是源自于郑和远洋船队。
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利玛窦虽然不是这份地图的原创作者,但也不算是欺世盗名的抄袭者。或者说利玛窦更像是将郑和时期遗留下来的全球地理资料与欧洲碎片化的知识进行合理整合的一位改编者。对于这份地图利玛窦同样有一些贡献,就是结合档案资料进行了修正,并且把东西方的制图方法结合起来。

利玛窦是肩负特殊使命来到中国的么?
有这样的怀疑也很正常,毕竟西方一贯的做法令人不得不起疑心。另外从利玛窦等在中国的行为来看,其实是有些怪异的。他们如果主要目的是来传教的,为何花在这个正事上的时间并不多,反而是把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在了诸如学习中国文化,努力和士大夫交往,把西方的科技知识传播到中国等方面。。。
这些行为来说,和传教士的身份是相差甚远的,如果说开始这样做的话,是为了更好地传教,后面几十年如一日做这些,是因为什么?
同时期包括这以后,在世界各地如美洲,印度,非洲,菲律宾等地的传教士有很多,基本都是恪守职责,专心给当地民众洗脑,很少听说有专注给当地传播科学知识的,毕竟科学本身就和教义是有所抵触的。。。

深究这个问题,需要慎重一些,避免掉进阴谋论的陷阱。
不妨来看看利玛窦自己写的书,看看从中能不能发现些什么。
利玛窦在中国共居留了28年,连翻译带写一共有16本著作,其中流传最广,史料价值最大的是一本名为《中国札记》的著作。
这本书是利玛窦在去世前最后几年写的,原稿用的是意大利文,共25万字。在利玛窦死后,这份手稿由在华的另一位耶稣会士金尼阁在1614年从澳门带回了意大利罗马。

这本书的内容主要包括几个部分:
1,记录了当时中国的各种情况,利玛窦熟练掌握了中文,并有能力对中国的典籍进行研究,可以说是西方学者中的第一人。加上他本身具有敏锐的观察力,他把在中国所见到的一切,上至国家政体,下至吃饭的餐具等都详细地向欧洲人做了介绍。可以说是从另一个视角看到的明万历年间的全景图。由于书中记录了万历年间的大量史事,于是成为了研究明万历史时,很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
2,把东方文化介绍给欧洲,在书中利玛窦着重介绍了儒家文化以及孔子,他对孔子有比较客观的评价:“中国古代哲学家中最有名的叫作孔子。……他以著作和授徒闻名,同时也以自己的言传身教来引导中国人民追求道德。他的学识修养,道德水平之高,使中国人认为孔子远比过去所有的先贤更为神圣。的确,如果我们认真研究过他那些意味深长的语录,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他的思想可以与最优秀的异教哲学家相提并论,甚至超过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
欧洲人得知茶叶,中国漆,甚至最早的中国的英译名和契丹有关,也都是源自于利玛窦的介绍。
3,把西方的科技介绍给中国,主要包括西方的算学,利玛窦和徐光启合译了欧洲的数学名著《几何原本》前六卷,还协助徐光启和李之藻等撰写了如《浑盖通宪图说》、《同文算指》、《测量法义》等这些有关天文和数学的译著;还有一部分主要的交流内容是天文历算学,这可以说是利玛窦和明廷官方合作的主要工作,利玛窦是将西学引入中国历法的第一人,对明清时期的历法演变影响深远。
4,和明朝士大夫们交往的情况,《中国札记》中一共记录了五十多位万历年间有名望的人与利玛窦的交游情况,包括徐光启、李之藻、翟太素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利玛窦与著名学者李贽的交往情况。李贽是一个极其聪明且敏感的学者,他对利玛窦的评价非常有意思。
李贽在《与友人书》中曾这样提到过利玛窦:“其西泰大西域人也。……凡我国书籍无不读,……今尽能言我此间之言,作此间之文字,行此间之仪礼,是一极标致人也。……但不知到此何为,我已经三度与之相会,毕竟不知其到此何干也。”
可见李贽虽然对于利玛窦的学识风度非常认可,可是对于他来中国的真实目的表示非常疑惑。。。

西方在当时是否已经在有组织地篡改历史?
如果把时间线延长的话,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基本可以肯定的。不过在利玛窦时期,西方是否已经在有组织地做这件事,不好说,目前没有发现直接证据,只有一些隐隐约约的指向。
利玛窦这一批最早的传教士,或者渗透东方也是他们的任务之一,但是应该还不是大规模有组织行动的一部分。
看一下明清时期传教士在中国的情况,大概可以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判断。
那个时期官方最看重传教士的是他们的天文历法能力,这份认同最初也是利玛窦争取来的。他本人的算学能力突出,大约在欧洲时也受过天文学的训练,到中国后通过展现其出众的演算能力,得到了包括徐光启在内的一大批实权官员的认可。
中国是农耕国家,历法对于农事是至关重要的,同时历法又和天文密切相关,而天文又和传统天命学说关系密切,因此天文历法的学习推广在历朝历代都是有所限制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明朝初期是严格禁止民间研习这一类学问的,只有钦天监官员的子弟可以学习这个,所以钦天监的工作岗位是世袭的。到了明中期以后,限制逐渐放松,越来越多的民间人士开始加入研究队伍,他们当中特别突出的也会被选拔进入官方的队伍。
研习这个学问,能力突出还是不突出,非常容易判断,最直观的方法就是通过对日食和月食等天文现象的预判,从预判的发生时间和实际的发生时间之间的差异来判断水平的差异。
稍微提一下中国的历法,实际上中国从远古时期,就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早在尧帝,颛顼,羲和氏的时期,就确立了二十四节气,阴阳历,回归年长度,岁星纪年及干支纪年,朔望月常数等基本内容。
到中古时期,上元积年,五星运动表,日月交食,及初始的晷影刻漏等知识和工具已经被运用到历法实践中,在二十四节气等的基础上,又推导出五行用事,六十四卦,没日灭日,置闰规则,奠定了农用历法的基础,有效解决了农业生产的相关问题。

到了南北朝和隋唐时期,中国的历法经历了一次大跃进,经过张子信,一行等卓越科学家的不懈努力,中国历法首次实现了对太阳中心差进行修正,推算出子午线经度一度的具体长度,第一次让地平视差修正走出了原始的经验主义,解决了困扰历代的“当食不食”,制定了第一张正切函数表,通过对五星的中心差修正解决了“圆椭模型”的问题,修正了刘焯的日躔表,提出了太阳冬至近地点的观点。。。这一时期的代表成就就是《大业历》,《皇极历》,《麟德历》和《大衍历》,标志着中国古代的历法研究已经从经验主义开始往数理科学的方向跨越。
到了宋元时期,在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宣明历》、《崇玄历》,《纪元历》和《授时历》等,标志着中国天文进入了全盛时期。其预测精度领先西方300到400年。
尤其是郭守敬主持确立的《授时历》,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完备精确的一项历法,结合弧矢割圆的方法,大量运用了几何模型构造历法,圆满解决了黄白道差,黄赤转化,里差漏刻等问题,废除了古老的九道术和上元积年,使用日月食的几何模型制定历法,极大地提高了预测日月食的精度。亦有一种说法,即郭守敬历法中用到的几何知识,有一部分来自于西域的回回部,这个是有可能的,不过要确定的话需要进一步的证据验证。
进入明朝以后,如上文所述,朱元璋对于天文历法管控严格,天文研究成为一个世袭职业,因为长期没有新鲜血液注入,导致优秀人才缺乏,继任者只能因循守旧,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到明中期以后,对于天象的预测失误越来越大,到万历崇祯时期不得不考虑全面改革。

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介入了中国的天文历法的制定工作。
利玛窦最早是担任顾问一类的角色,实际工作还是由原有的钦天监系统承担,利玛窦去世之后,由于中西历法争论激烈,于是将钦天监一分为二,成为东西二局,西局是以徐光启、汤若望为首,以西法主编历书;东局是原钦天监系统加上民间科学家魏文魁等,还是以传统大统历为基础进行修正。
据明史记载,这两个局在整个崇祯朝,一共进行过8次实测较量,涉及日食、月食和行星运动等天象,发生在1629年、1637年和1643年的日食,发生在1631年和1636年的月食,以及发生在1634年木屋运动、1635年的水星和木星运动,以及1635年木星、水屋和月亮位置的比较。对战的结果是西局八战八胜,东局则是颗粒无收。。。
事实上在崇祯历改期间,在北京地区可见的日食和月食,一共有24次之多,为何只记录了8次结果,其他16次是没有预测,还是因为对西局不利,记录消失?
崇祯皇帝在关于指示改历的圣旨中提到“日食初亏、复圆时刻方向皆与《大统历》合,其食甚时刻及分数,魏文魁所推为合”。这明明是在说传统团队预测更加精确,难度崇祯是在说谎?
继续顺藤摸瓜探究下去,发现了更为诡异的情况,明清时期与改历有关的书籍,明刻本与清刻本差别非常大,清刻本上都是有利于西法的表述,明刻本则普遍存在缺页现象,并且所缺失的都是同样的几页,这种匪夷所思的诡异现象不得不让人展开联想。。。
所以说,千万别把明史当成正史,里面的猫腻太多了。。。认知作战从那个时期就开始了。。。
操刀手是谁呢?基本可以确定是汤若望!清朝的统治者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这个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清军入关之后,对于汉人并不信任,西方传教士更受重用,汤若望因此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掌握了这个天文历法的核心部门。
汤若望之后的几任钦天监监正几乎一直都是由西方传教士担任,这到底是自然传承,还是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尚需要进一步研究。
汤若望掌握了权力之后,一边大力发展基督教信徒,一边开始系统化地篡改明末历法之争的历史。发展到后来,开始变本加厉,甚至出版了一本名为《天学传概》的书籍,此书介绍了西方基督教的发展,以及基督教与中国的关系,关于这部分的内容非常荒诞不经,
汤若望认为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是基督后裔,中国从伏羲开始即是如此,中国人的先祖同样出自西方。
他还认为中国传统哲学和基督教相比,不过是雕虫小技,中国的《诗经》、《尚书》、《论语》、《孟子》等,全都是信奉基督之后的产物,孔孟之学也都是基督思想派发出来的细小分支。
在汤若望营造的认知世界里,中华文明被彻底否定,归入到西方基督教派生出的一个东方分支。这种说法引起了传统人士的强烈不满,在他们的合力反击之下,汤若望等西方传教士被逮捕法办,虽说汤若望本人在康熙的庇护下保住了一条命,不过整个西方传教士的势力经过这次事件受到了巨大打击。
康熙对于汤若望还是念念不忘的,在汤若望死后,康熙不但给汤平了反,还恢复了他“通玄教师”的名号。
在汤若望主持钦天监期间,把传统历法说得一无是处,可事实绝非如他所说,真要是那样的话,他也不用费尽心机去篡改大量的历史文献和实测记录。当时的一些有见识的儒生如杨光先等,已经认识到汤若望是包藏祸心,是企图用新历来实现“暗窃正朔之权给予西洋”的罪恶目的。。。
最后简单总结一下,西方系统化地篡改东方历史,是从清朝早期就实际开始了,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活动应该是始于工业革命之后,篡改东方历史和假造西方历史,是相辅相成的两件事,都是这个组织全力推动的。至于汤若望当时是个人行为还是执行秘密任务,这个不好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