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提起“司马光砸缸”的故事,相信大家一定是耳熟能详,一定是如雷贯耳,时至今日依然具有非常积极的教育意义。北宋时期,年幼的孩子们一起玩耍,其中一孩不慎落入水缸中,其余众人哇哇乱哭不知所措。千钧一发之际,司马光镇定自若地用石头砸缸救人。据《宋史·司马光传》记载:
群儿戏于庭,一儿登瓮,足跌没水中,众皆弃去,光持石击瓮破之,水迸儿得活。
人落入水中,通常认为只有把他捞出来才能获救,但年幼的玩子们显然不具备这种能力。于是,司马光发挥创造性思维另辟蹊径,通过砸缸放水的方法来间接救人,蕴含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和相对论思想。

问题来了,幼年便具有创新思维和开拓精神的司马光,成年后为何却变成了思想僵化和墨守成规的保守派?甚至于,被认为“北宋最后一次自救机会”的王安石变法,就在他的坚决阻挠下才功败垂成。
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和客观公正的态度,文史不假带您走进北宋,走近司马光和王安石,深入了解“司马光砸缸”和“王安石变法”的前因后果。为了抵制抄袭,本人在来源于网络的图片附加水印实属无奈,如有侵权请联系删图。同时声明,文章首发于今日头条,分发于百家号,拒绝任何第三方平台转载。
司马光出生于1019年,字君实,号迂叟,谥号“文正”,陕州夏县(今属山西省夏县)人。作为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史学家,他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和哲宗四位皇帝,因为“砸缸救人”而被后世所称颂,又因为“反对变法”而被后世所诟病。

司马光
“文正”是封建王朝对文臣的最高谥号,死后由皇帝亲自追认,是对官员的最高评价和最大褒奖,具有强烈的价值导向作用。历宋、元、明、清四朝,仅有30人获赠这一盛誉,其中宋代7人,元代10人,明代5人,清代8人。
宋真宗天禧三年十月十八日,司马光出生于河南光州光山,也就是今天的山西省夏县。当时,父亲司马池正担任着光山县令,因而给儿子取名“光”,从小就悉心教导他读书学习,希望日后光耀门楣。
司马光不仅天资聪敏,而且勤奋刻苦,七岁时便能背诵《左氏春秋》并且通晓要意,属于典型的“别人家孩子”。在一次玩耍时,他竟然还做出了“砸缸救人”的壮举,简直轰动了京洛一带,可谓年少成名。
天圣九年,司马池调任四川广元出任转运使,司马光跟随父亲一路经洛阳、潼关、宝鸡和汉中等地。刚刚入蜀时,他们在山路上遇到巨蟒拦路,年仅十二岁的他竟然再现惊人之举,沉着冷静地砍伤它推下山涧,丝毫没有恐慌和胆怯。
由于天赋极佳、博学多知和勇敢无畏,司马光越来越被父亲所宠爱。基本上,平时除了正式的公务外,他无论郊游、应酬和访友都会带着儿子在身边,有机会接触到许许多多的人和事,被夸赞“凛然如成人”。
因为太过于优秀,司马光被当时的许多大儒一致看好,甚至尚书张存都主动订立婚约将女儿许配。1038年,也就是宝元元年,十九岁的他不负众望,一举高中进士甲科从此以后步入仕途。同年,又迎娶张氏为妻实现了双喜临门,当真是春风得意马蹄疾!

或许大家也看到了,文章写到这儿已经出现了好几个年号,文史不假插几句题外话。北宋非常有意思,更换年号比较频繁,也比较随意,高兴时可以改年号,不高兴时也可以改年号。比如,仁宗皇帝赵祯就前后使用过多达九个年号,分别是天圣、明道、景佑、宝元、康定、庆历、皇佑、至和和嘉祐,成为中国历史上使用年号最多的皇帝。
1039年,也就是宝元二年,由于父亲调往杭州任职,司马光也主动申请调任苏州判官。不过,正当他准备挥斥方遒之际,母亲却不幸病逝了,从此辞官回乡丁忧守孝。

袁腾飞老师当年提出过“北宋缺将,南宋缺相”的论断,个人认为并非无的放矢。在“澶渊之盟”签订后,宋辽之间维持了总体的休战态势,但西北地区的党项人却在此时悄悄崛起,成为了双方的心头大患。
党项人是西羌族的支裔,最早盘踞在青海一带,长期受中原政权影响,还在唐末平定黄巢起义时被唐僖宗册封为夏国公,从此沿用“西夏”。北宋建立后,首领李继迁率部归顺,但获得了相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随着辽国逐渐崛起,西夏又向对方称臣,基本上臣服于宋辽两强之下。通过对吐蕃和回鹘等地的征伐,他们逐渐夺取了西凉府、甘州、瓜州和沙州等地,势力范围扩大后也拥有了与宗主国叫板的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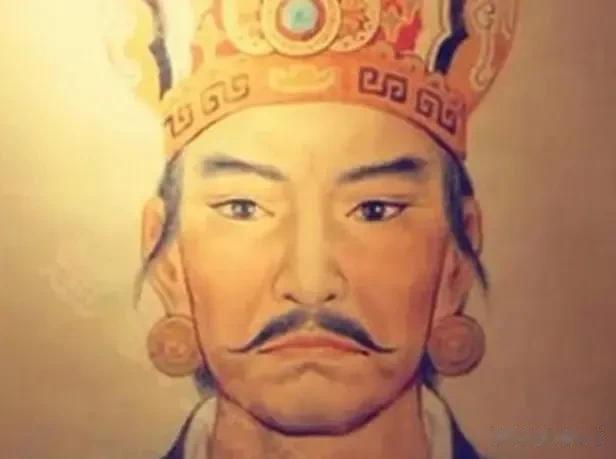
李元昊
1032年,李德明病故后由太子李元昊继位,从此开始了更加疯狂和激进的扩张之策。在他的统治下,西夏的野心不再掩饰,企图称帝建国并与宋辽两国平起平坐。
1038年10月,李元昊宣布建立大夏国并且定都兴庆府,筑坛受册为皇帝。宋朝坚决不承认他的帝位,立即下诏“削夺赐姓官爵”,双方关系完全破裂,宋夏战争终于打响。
可以说,在司马光为母丁忧的这段时间,宋朝一直都在与党项人打仗。只不过,战事却进行得异常憋屈,异常窝囊。

宋朝是当时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但军事实力却令人汗颜。经过三川口之战、好水川之战和定川寨之战,朝廷虽然嘴硬不承认,但事实上都以失败而告终。不过,两国国力差距太大,西夏不是“打不过你”,而是“耗不起你”,最终无奈主动求和。
1041年,也就是庆历元年,司马光刚刚为母亲服丧期满,父亲司马池却病死在了晋州。于是,他和兄长司马旦扶灵回到了故乡夏县,悲痛地表示“平生念此心先乱”,又开始为父丁忧。
丁忧期间,司马光将满心的悲哀都化作动力,创作完成了《四豪论》、《贾生论》和《十哲论》等名篇。同时,他也切实感受到了下层百姓的疾苦和无奈,希望能够入仕为官保国安民。
1044年,就是庆历四年,司马光在丁忧结束后重新入仕担任丰城知县,很快就实现了“政声赫然”。两年后,他奉旨调任大理评事,从此留在东京成为了一名京官。
庆历七年,贝州农民王则起义后自称东平郡王,公开聚众与朝廷为敌。当时,司马光父亲的生前好友庞籍正担任着枢密副使,他连夜写成《上庞枢密论贝州事宜书》为对方建言献策,仅仅两个月便平定了这次起义。
1055年,也就是至和二年,庞籍前往并州出任河东路经略安抚使,司马光也在对方的提携下改任并州通判。当时,他已经年满36岁,虽然和妻子张氏恩爱如初但却始终无儿无女。
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影响,妻子张氏不愿意委屈丈夫,悄悄购入一个年轻女子纳为妾室。不过,司马光却连看都没看,表现出了高尚的情操和人格,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
平心而论,司马光在方方面面都称得上是封建社会的“楷模”和“标兵”,除了不贪财、不恋权和不好色,而且还心怀社稷和百姓。就是这样一位“完人”,为何会亲手开启了北宋的党争,又亲手摧毁了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
王安石出生于1021年12月,祖籍位于抚州临川(今属江西省抚州市),比司马光要年轻两岁。笔者可以很负责任地说,他二人都是当时的佼佼者,也都是为了实现大宋中兴,偏偏却是背道而驰。
对于国家的衰落,王安石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变法主张,而且还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系统阐述了自己的主张。只不过,当时的宋仁宗已经力不从心,故而没有准奏,只是嘉奖了他的忠君爱国而已,难怪会有“凡事不会做,只会当官家”的评价。

仁宗皇帝驾崩后,二十岁的赵顼登基即位,史称宋神宗。年轻人血气方刚,总是想做些事情,很多方面都想除旧革新。在此背景下,王安石再次上疏要求变法,终于得到了新帝支持,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具体负责。
为了彰显自己的信心和决心,王安石提出了著名的“三不足”暨“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当时,中书省的宰相和副宰相共有五人,分别是老气横秋的曾公亮、称病不出的富弼、不幸逝世的唐介和叫苦连天的赵抃,只有他自己一人属于生机勃勃的状态。
与此同时,反对变法的人却是“兵强马壮”,个个都是鼎鼎大名的人物。比如,欧阳修、苏轼、苏辙、韩琦、吕公著、程颢、程颐、范纯任、赵颢......,他们都是变法的绊脚石。

可能有人会问,这个长长的名单里面为何没有司马光?他不是顽固派的代表人物吗?事实上,司马光在变法之初并没有坚决反对,即便许多方面都存在保留意见,但还是选择“看看再说”。
在王安石的推动下,被称为最后一次自救机会的“熙宁变法”开始了。果然,变法很快就初见成效,极大地缓解了社会的许多矛盾,也极大地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这令神宗皇帝很高兴。
由于这次变法的步子太大,力度太大,极大地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而且,王安石此人太过于理想化,太过于天真,又太过于固执,得罪了越来越多的人。于是,原本观望的许多中间派也开始反对变法,比如司马光。
在变法之初,司马光认为这种“高大全”的举措极难成功,但还是抱有谨慎的乐观态度。可以说,他虽然不是变法的支持者,但也不是反对者。

王安石制定了一系列的律令和法规,从战略层面进行了整体规划和部署。不过,他并不是真正的实干家,在具体的变法过程中没有沉下心来监督执行情况,更没有关注具体的落实情况。
以最著名的“青苗法”为例,规定各州县的农民在夏秋两收前可以向官府借贷现钱和粮谷。当然,各地官府也会收取不高的利息,这样既能缓解农民困难,又能增加朝廷收入,看起来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在实际的变法过程中,各级官员往往阴奉阳违,理解力和执行力都出现了重大偏差。于是,有些地方为了谋取私利而提高了利息,有些地方为了骗取政绩而虚报了产量,使得许多赋税都转嫁到了百姓的身上。
在十月革命期间,布尔什维克领袖列宁为了实现土地改革,曾多次提到“俄国不要重蹈王安石变法的覆辙”。但是,对于王安石本人却是非常推崇的,盛赞他是“中国十一世纪时最伟大的改革家”。
除了“青苗法”外,像保甲法、水利法、将兵法、募役法和均税法也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总结起来就是,佛祖的经书不错,但被和尚们念歪了,完全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面对新法,反对派们利用一切手段予以破坏,甚至还采取了“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损招。例如,苏轼为了公开反对新法不惜上疏皇帝,最终被外放徐州和湖州等地,绝对属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或许是“新官上任三把火”烧完了,或许是“满腔信心和激情”用尽了,曾经无比支持变法的宋神宗开始犹豫了,甚至动摇了。见到有机可乘,反对派们一拥而上各尽其能,意欲除之而后快。
作为一个看大门芝麻绿豆官,区区“安上门监”郑侠也敢跳出来刷存在感,向神宗皇帝进献一幅《流民图》。图中画的都是流民惨状,有的冷得全身打颤,有的饿得面黄肌瘦,除了嚼草根和啃树皮的,还有卖儿鬻女的,无限放大了灾荒景象。
作为反对派的代表人物,文彦博把“天久阴”、“星失度”和“华山崩”等不祥之兆也与变法联系起来。他宣称,只要免去王安石的职务并且停止变法,立即就能禳除灾异而使国家平安。
在反对派和改革派正面硬杠的同时,中间派们开始选定方向,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司马光。某日,他和王安石公开辩论,甚至当着神宗皇帝的面也不肯让步,一个坚持“破釜沉舟”,另一个则坚持“四平八稳”。
眼见无法说服对方,司马光豪横地递交了辞呈,独自躲到洛阳去编撰《资治通鉴》。而他这一去,就是十几年的时间,被反对派们赞誉为“光荣的孤独”。
在反对派的持续攻讦下,宋神宗终于不再支持王安石,甚至还下旨废除了争议较大的部分新法。在他驾崩后,年仅八岁的赵煦继位,朝政大权完全被太皇太后高滔滔所把持,而她历来就非常仇视新法。

1074年,也就是熙宁七年,王安石被罢免参知政事一职,以观文殿大学士的身份被贬为江宁知府(今江苏省南京)。同时,司马光被召回朝廷担任参知政事,他不仅重新起用守旧派大臣,而且还接连废除了许多新法。
眼见自己呕心沥血的成果被消除殆尽,身处江宁的王安石欲哭无泪。而且,曾经被他寄予厚望的变法派也纷纷倒戈,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吕惠卿。
吕惠卿是变法的副手,是王安石一手培养和提拔起来的后备人才。不过,在恩人遇到麻烦时却落井下石,甚至诬陷对方参与谋反,最终导致复出无望。
哀莫大于心死!
看到自己的新法几乎不复存在,王安石辞去官职告老还乡。结果,第二年就郁郁而终,带着无尽的遗憾闭上了眼睛。得知消息后,司马光显得十分悲痛,还坚决要求朝廷优渥对方的家属和亲眷。据《宋史 》记载:
光意以谓朝廷宜优加厚礼。
不难看出,司马光和王安石之间没有个人恩怨,只是政见不同而已,完全算得上是君子之争。只不过,正是前者的墨守成规和固步自封,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后者变法的失败,而且丧失了北宋最后一次自救的机会。
1126年,也就是靖康元年,完颜宗翰率领金兵东路军进至汴京城下,逼迫朝廷签订城下之盟。第二年,他们再次南下并且攻占了都城,还将昏庸无能的徽钦二帝和朝中大臣全都俘掠到北方,史称“靖康之耻”,北宋至此灭亡。
如果王安石能在变法过程中循序渐进,如果司马光能在变法过程中吐故纳新,当年的王安石变法极有可能成功。如果是那样,北宋的历史定然会被改写,但历史无法假设,更无法改变。

对于王安石和司马光,著名历史学教授易中天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观点。他认为,这二位都是理想至上和道德唯一的人,前者觉得自己从事的是利国利民的伟大事业,为此可以无所畏惧和无所顾忌;而后者也这样认为,同样可以无所畏惧和无所顾忌。于是,两位君子在如此崇高的道德驱使下,开启了党争的序幕,加速了北宋覆灭。

鲁迅曾经说过,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司马光和王安石都是当时的能臣和忠臣,而各自的品行操守和爱国热情也都没有问题。但是,前者的历史地位却远不如后者,很大程度上就在于缺失了幼年时那种“砸缸救人”的创新思维和义无反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