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开卷便自陈“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我之罪固不免,然闺阁中本历历有人”[1],体现了作者的自愧自悔之情,却又在贾宝玉神游太虚境、王熙凤毒设相思局、秦可卿淫丧天香楼、尤氏姐妹双丧身等情节,沿用了“红颜是祸水”的叙事俗套。

人民文学出版社整理本《红楼梦》
这不禁令人困惑:一部扬言要使“闺阁昭传”,要令“世人换新眼目”的小说,怎会落入“女祸论”的俗套?倘若如此,那么鲁迅所谓“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2]的评价,就要大打折扣了。
这些困惑的出现,应当与今传本《红楼梦》“增删五次”,却未能完全消化“戒妄动风月之情”的《风月宝鉴》的旧稿有关。
惟有厘清《红楼梦》对祸水叙事的改写问题,才能够解释相关人物形象矛盾,个别情节悖乱的原因,进而对《红楼梦》的成书过程与最终意旨有更清晰的认识。

学界普遍认同,《风月宝鉴》与《红楼梦》是“一稿多改”或“二书合一”的关系[3],但无论哪种情况,经作者“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之后,《红楼梦》的主旨已与《风月宝鉴》相去甚远。
风月旧稿旨在“戒妄动风月之情”,女性只有以“祸水”的形象存在,才能完成“戒色保生”的叙事功能。而红楼新稿则意欲“使闺阁昭传”,认可女子“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从而有别于“熟套之旧稿”。
尽管如此,《红楼梦》在整合风月旧稿的过程中,未能完全消解掉旧稿中的祸水叙事,因此留下了诸多线索和破绽。
《红楼梦》整合的风月旧稿,据甲戌本评点及后世学者考论,大概包括秦可卿姐弟、贾瑞、王熙凤、二尤等人的故事,并有“……‘风月宝鉴’四字,此则《风月宝鉴》之点睛”[4],“秦可卿的故事应是旧本《风月宝鉴》中的高峰”[5],“凤姐当然是《风月宝鉴》里主要人物之一”[6]等说法。

《红楼梦成书研究》
简言之,与“风月”相关的主要情节大抵都来自《风月宝鉴》,其中的女性形象通常是祸水的人设。
贾宝玉神游太虚境一节,小说之所以让秦可卿客串贾宝玉风月体验的引路人,是因为只有兼宝钗、黛玉之美的祸水,才能达到更好的点化效果,“领略此仙闺幻境之风光尚如此,何况尘境之情景哉”。
为了彰显这个人设,小说特意安排野史稗说中著名的祸水——西施、赵飞燕、武则天、杨贵妃、寿昌公主、同昌公主、莺莺等人客串出场,她们的身份有贵有贱,德行或淫或贞,浣纱女西施、歌舞伎赵飞燕的出身并不高贵,帝女寿昌(阳)公主与同昌公主也不曾闻有淫行,她们的共性只有一个,那就是都具备祸水的属性或成为祸水的资本。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红娘抱过的鸳枕”之所以有资格与武则天的宝镜、赵飞燕的金盘、同昌公主的连珠帐等稀罕物相提并论,是因为鸳枕的主人崔莺莺虽然是唐传奇中虚构的人物,但她在问世之时就被打上了“祸水”的烙印,后经《西厢记》这部“淫书”宝典的文本改造,早已成为世俗祸水的代言人[7]。

《元稹集》
原作者元稹曾借张生之口,概括了祸水的共性:
张曰:“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贵,乘娇宠,不为云为雨,则为蛟为螭,吾不知其所变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据万乘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僇笑。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于时坐者皆为深叹……时人多许张为善补过者矣。[8]
张生所谓尤物,就是祸水。
在《新唐书》发明“女祸”一词之前,尤物就是祸水的代名词,早在《左传》中就有了尤物为祸的说法:“女何以为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义,则必有祸。”[9]
后世亦常将二者混用,如贾宝玉谈论尤氏姐妹:“真真一对尤物,她又姓尤。”这个“尤”姓,就是作者对二人身份的有意提醒。
张生的祸水论,注意到了祸水“无差别攻击”的能力——只要是天生尤物,就有祸国殃民的可能,为祸的大小,与她们的出身关系不大,主要取决于她们遇合对象的尊卑,历史已有明证。
因此无须纠结秦可卿的出身,误入索引的迷途。即便幻境中的兼美不是警幻之妹,她的“鲜艳妩媚”“风流袅娜”也足以令宝玉“难解难分”;就算现实中的秦可卿是营缮司郎中的养女,也不影响她与贾珍“情既相逢必主淫”。
按照祸水叙事的套路,祸水“不妖其身,必妖于人”,害人害己,必得其一,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便是后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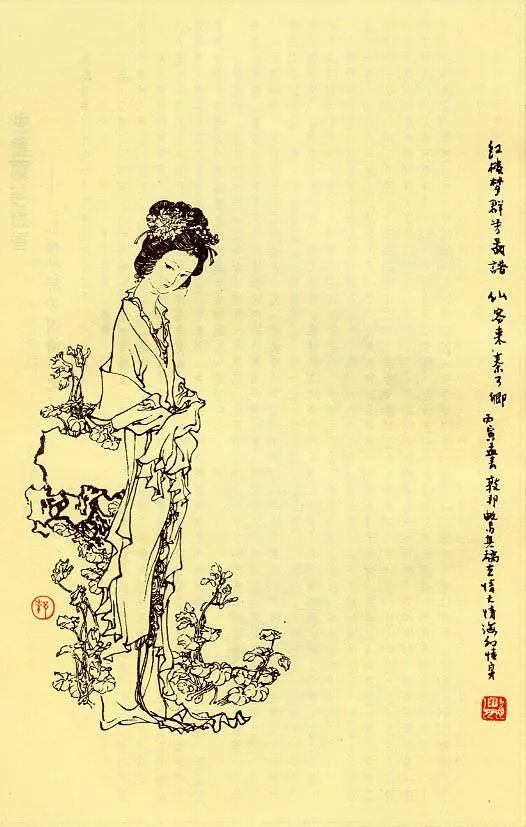
戴敦邦绘秦可卿
贾瑞正照风月鉴一节,王熙凤同样扮演了祸水的角色。她明知贾瑞心存不轨,却毒设相思局,让贾瑞误以为有机可乘,才越陷越深。
陈其泰认为,蚁不叮无缝之砖,贾瑞之所以敢撩拨王熙凤,证明王熙凤也是风月中人,即“不知文者,谓此回为凤姐洗濯。知文者,谓此回为凤姐坐实也。人不风月,则风月鉴中,胡为乎来哉”[10]。
王希廉也认为,王熙凤对贾瑞之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贾瑞固属邪淫,然使凤姐初时一闻邪言即正色呵斥,何至心迷神惑,至于殒命”[11]。这种“受害者有罪论”,实际是受到了该情节祸水叙事的影响。
贾瑞故事作为《风月宝鉴》的点睛之笔,本身是逻辑自洽的,但移植到《红楼梦》中,贾瑞与王熙凤初遇一段就显得殊不合理了。
小说写到王熙凤从秦可卿处探病出来:“于是凤姐儿带领跟来的婆子丫头并宁府的媳妇婆子们,从里头绕进园子的便门来。但只见:黄花满地,白柳横坡……凤姐儿正自看园中的景致,一步步行来赞赏。猛然从假山石后走过一个人来,向前对凤姐儿说道:‘请嫂子安。’”

赵成伟绘王熙凤
引文省略部分是《红楼梦》中唯一的一段骈文写景,早有学者注意到了这段的违和,指出此时王熙凤不仅没有审美的心情,也不会突然提升审美的水平——毕竟《红楼梦》中的王熙凤是个文盲,“绝无可能用骈四俪六的思维方式观察景物”,因此揣测“它就极有可能是曹雪芹删除未尽的‘旧稿’《风月宝鉴》中的‘零碎’之一”[12]。
依笔者看来,这段描写还存在一处漏洞,那就是王熙凤原本“带领跟来的婆子丫头并宁府的媳妇婆子们”一起进的园子,但在贾瑞出场后,这些人却集体失踪了。待二人交谈完毕,凤姐转过了一重山坡儿,才“见两三个婆子慌慌张张的走来”。
按第五十四回贾母“掰谎”所说,仕宦书香大家的小姐,奶母丫鬟服侍小姐的人也不少,怎么可能只有一个紧跟的丫鬟?
同理,王熙凤是大家媳妇,出门虽不至于前呼后拥,但也常带着婆子丫鬟,很难有落单的机会恰好被贾瑞撞见。因此这一段应该是《红楼梦》并未处理好《风月宝鉴》旧稿的明证。
再如尤氏姐妹,亦是风月旧稿中的重要角色。尽管《红楼梦》中淡化了尤氏姐妹与贾珍、贾蓉、贾琏等人的淫乱关系,将尤三姐的形象做了净化处理,但尤氏姐妹双丧身,仍未能逃脱祸水“不妖其身,必妖于人”的套路式结局。
特别是尤三姐托梦尤二姐一段,残留了祸水论的套话:“你我生前淫奔不才,使人家丧伦败行,故有此报。”“自古‘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天道好还。你虽悔过自新,然已将人父子兄弟致于麀聚之乱,天怎容你安生。”这些合乎祸水叙事的情节,应当都出自风月旧稿。

连环画《红楼二尤》
如果说贾宝玉游太虚幻境、贾瑞正照风月鉴,是劝诫痴男莫要堕入女色陷阱,那么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与尤氏姐妹双丧身,则是劝女子莫要犯下淫行。
这种女色害人害己的陈腐论调和俗套情节,在正史与稗说中极为常见。但相对全篇而言,这些笔墨所占的比例很小,且与其他情节多有抵牾。
为了避免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还应通篇审视、全局关照,才可能了解作者的最终意旨。

从《风月宝鉴》到《红楼梦》,不仅是“把一部‘戒妄动风月之情’的作品”改写成“一部主旨将‘儿女之真情发泄一二’的艺术瑰宝”[13],而且还将小说的主角也由风月故事中的痴男怨女改写为“正邪两赋之人”。
这一改动,表明作者有意区别于“满纸才人淑女,子建文君红娘小玉等通共熟套之旧稿”,同时创造出更为复杂的人物形象及两性关系。女性不再只是情感世界的主角或配角,而是与男性共同作为“正邪两赋之人”被关照,小说的主题与格局也就不再局限于“儿女之真情”了。

孙温绘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所谓正邪两赋,是指兼秉天地正邪两气所生之人。小说第二回通过冷子兴与贾雨村的对谈,隆重地介绍了这一类人物的特点和分类:
使男女偶秉此气而生者,在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于万万人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纵再偶生于薄祚寒门,断不能为走卒健仆,甘遭庸人驱制驾驭,必为奇优名倡。
为了说明何为两赋之人,贾雨村还例举了个中代表,如生于公侯富贵之家的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与魏晋名士,生于诗礼清贫之家的温庭筠、柳永、唐伯虎、祝枝山,生于薄祚寒门的李龟年、黃幡绰、敬新磨、红拂、薛涛、崔莺、朝云之流。
贾雨村还特别指出,贾宝玉就是两赋之人,“方才你一说这宝玉,我就猜着了八九亦是这一派人物”。
不仅如此,在冷子兴介绍完贾府“元、迎、探、惜”四春及王熙凤后,贾雨村又补充道:“可知我前言不谬。你我方才说的这几个人,都只怕是那正邪两赋而来一路之人,未可知也。”
这段“正邪两赋论”将男女并举,一同置于“天地生人”的宏观视角下去关照,与上文张生那段立足男性偏见的“祸水论”有云泥之别。
莺莺出现在这串名单中,是为了说明她的聪明灵秀在万万人之上,与秦可卿卧房内作为祸水出场的情况已大有不同。

德藏明刻套色《西厢记》 崔莺莺像
贾雨村的正邪两赋之说,可以看成是作者“假语村言”,有意提醒读者应从这一角度去理解本书的主要人物——尽管贾雨村和冷子兴明确提到的只有贾宝玉、林黛玉、贾府四春和王熙凤几位,但不妨碍我们借用正邪两赋的观念,从形象的丰富性、多样性去考察书中的主要人物。
贾宝玉作为《红楼梦》的核心人物,他身上的正邪两赋属性最为突出,这一点前辈学者已论述详备[14]。
出了太虚幻境,贾宝玉不再是风月故事的主角,他的人生更多地围绕一种艺术化的生命体验展开,并在这种体验中找到知音与共鸣。
除了林黛玉,贾宝玉与“风流跌宕”的北静王、“天生成孤僻人皆罕”的妙玉、“名驰天下”的琪官蒋玉菡等人也颇为合缘,是因为他们都可以在正邪两赋的谱系中找到定位:北静王可以归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的情痴情种,妙玉可以归入生于诗礼清贫之家的逸士高人,琪官则可以归入生于薄祚寒门的奇优名倡。

《桐花凤阁评红楼梦辑录》
同道中人,自然惺惺相惜。陈其泰曾就妙玉弃杯,宝玉洗地一节指出:“妙玉之心,惟宝玉知之,是两人犹一人也。盖宝玉忘乎己为男,亦忘乎妙玉之为女,只是性情相合,便尔臭味相投。此之谓神交,此之谓心知,非食人间烟火者所能领略。若说两人亦涉儿女私情,互相爱悦,则俗不可耐矣。”[15]
这段评论,应该是领会了作者的意图,因为在看龄官画蔷、帮平儿理妆的情节中,都印证了宝玉对女性的怜爱,只是出于一种纯粹的“意淫”,无关乎风月。
俞平伯认为,《红楼梦》中的金陵十二钗都是“‘间气所钟’之人”[16]。若以正邪两赋的标准来看,她们或多或少符合“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的标准。
小说不再将她们作为风月故事的女配,去服务“戒风月”的旧叙事,而旨在彰显她们身上的聪俊灵秀之气,以回应“使闺阁昭传”的新主题。
秦可卿在《红楼梦》中的现实身份是宁国府的管家媳妇,她“生的袅娜纤巧,行事又温柔平和”,是贾母心中“重孙媳中第一个得意之人”。
得知秦可卿的死讯,“那长一辈的想他素日孝顺,平一辈的想他素日和睦亲密,下一辈的想他素日慈爱,以及家中仆从老小想他素日怜贫惜贱、慈老爱幼之恩,莫不悲号痛哭者”。
在删去“淫丧天香楼”一节之前,秦可卿已有别于传统的祸水形象。
删去“淫丧天香楼”的直接原因,据甲戌本第十三回批语:“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作者用史笔也。老朽因有魂托凤姐贾家后事二件,嫡是安富尊荣坐享人能想得到处?其事虽未漏,其言其意令人悲切感服,姑赦之,因命芹溪删去。”[17]
批者其实是注意到了秦可卿的人设前后矛盾,套用“既是忠义,必不做强盗;既是强盗,必不算忠义”[18][ [清]俞万春著,戴鸿森校点:《荡寇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的表述,既是祸水,必无此远见,既有远见,必不算祸水。

同治十年重镌《荡寇志》
在删掉“淫丧”之后,小说为秦可卿设计了更合乎她身份、更符合逻辑的死因——病逝。小说之所以强调秦可卿的出身寒微,又聪明太过,实际是让她处于“贫女居富室”的尴尬处境下,外无依仗,内乏援手,要做到妥帖周全,只能加倍劳神。
因此尤氏说她:“虽则见了人有说有笑,会行事儿,他可心细,心又重,不拘听见个什么话儿,都要度量个三日五夜才罢。这病就是打这个禀性上头思虑出来的。”
秦钟闹学一出,就道破了秦可卿的难处,戚蓼生盛赞这一段妙笔称:“欲速可卿之死,故先有恶奴之凶顽,而后及以秦钟来告,层层克入,点露其用心过当,种种文章逼之。虽贫女得居富室,诸凡遂心,终有不能不夭亡之道。我不知作者于着笔时何等妙心绣口,能道此无碍法语,令人不禁眼花缭乱。”

戚序本《红楼梦》
评点家已经注意到,即便没有其他变故,秦可卿也很难强寿。嗣后张太医前来诊病,说秦可卿的病源是“心性高强聪明不过”“思虑太过”,切中肯綮。
后文反复铺垫“倘或因这病上有个长短”,“这病不过是挨日子”等,并非是有意遮掩什么,而是陈述事实罢了。
王熙凤作为旧稿的主要人物,在第十二回毒设相思局后,便基本脱离了风月剧情,不再有涉淫的笔墨。
第二十一回贾琏曾抱怨王熙凤:“只许他同男人说话,不许我和女人说话;我和女人略近些,他就疑惑,他不论小叔子侄儿,大的小的,说说笑笑,就不怕我吃醋了。”平儿反驳道:“他醋你使得,你醋他使不得。他原行的正走的正。”
第二十三回贾琏又埋怨王熙凤“扭手扭脚”,太过保守。可见,作者有意让王熙凤脱离旧稿中的祸水人设。
作为贾雨村和冷子兴明确提到两赋之人,王熙凤身上的两赋属性十分突出。她的亦正亦邪、精明能干在第十三回协理宁国府、第十五回弄权铁槛寺就有充分展示,甲戌本第十四回脂批:“写秦氏之丧,却只为凤姐一人。”[19]
尽管如此,王熙凤也未能挽救贾府败亡的命运。小说多次写到贾府的日用不敷与王熙凤的独木难支。
第五十五回王熙凤因过年忙得小产,在病榻上还琢磨俭省的法子:“若不趁早儿料理省俭之计,再几年就都赔尽了。”
第七十二回王熙凤为了周转不得不将月钱放利:“若不是我千凑万挪的,早不知道到什么破窑里去了。如今倒落了一个放账破落户的名儿。”

电视剧《红楼梦》中邓婕饰演王熙凤
但王熙凤的用心良苦,不仅招来一堆骂名,就连贾琏都不理解,惹得她新病旧症竟合成血山崩之势。即便没有“一从二令三人木”,王熙凤也将命不久矣。可见无论是“贫女得居富室”,还是“凡鸟偏从末世来”,都无法阻挡悲剧的必然发生。
秦可卿的早逝,足以撇清她与贾府败亡的干系,而王熙凤的夭亡,则与贾府颓势难挽直接相关。她们不仅不是“败家的根本”,反而是家族的续命人。
正因为《红楼梦》打破了祸水叙事的套路,将男女一同置于“天地生人”的标准下,发现了兼秉正邪两赋的特殊一类,才担得起“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的殊誉。

《红楼梦》开篇便宣称,意在“使闺阁昭传”,因此才有对“祸水叙事”的改写。在《红楼梦》之前,尽管也有诗文稗说为女性翻案,但像《红楼梦》这样集中地展现女性才干的长篇巨著,却前所未有。

《传统与现代:红楼梦中的明清时代图景和女性书写》
首先,《红楼梦》呈现了一个客观事实,那就是女性的行止见识并不低于男子。作者亲自见证了“当日所有之女子”“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才会真诚地得出结论“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才会在小说中为闺阁昭传。
除了上文提到的秦可卿、王熙凤极具才干,宝钗、探春也都有理家之能,就连不问俗务的黛玉,都能发现贾府的重重危机,称:“我虽不管事,心里每常闲了,替你们一算计,出的多进的少,如今若不省俭,必致后手不接。”
但背负家族复兴希望的贾宝玉却全不在意,“凭他怎么后手不接,也短不了咱们两个人的”。
可惜这些聪慧的女子只能被拘谨在内宅,英雄无用武之地,迫使探春发出这样的“呐喊”:“我但凡是个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了,立一番事业,那时自有一番道理。偏我是女孩儿家,一句多话也没有我乱说的。”即便如此,探春们也无法摆脱被男性主宰、受家族连累的悲剧命运。
小说除了正面铺叙“闺阁中历历有人”外,还通过反向对比,展现了男性的堕落腐化。如薛蟠出场就害死了一条人命,是个典型的纨绔子弟,但当他进了贾府后,贾府子弟居然能引诱的他“比当日更坏了十倍”,可见贾府子弟不堪到什么程度。
到第七十五回,宁国府的族长贾珍正在与诸妻妾开怀作乐赏月,忽听得三更时分墙外有人长叹,一阵风过,恍然闻得祠堂内槅扇开阖之声……暗喻贾家先祖们对家族和后辈子孙不肖的彻底失望。
就连贾宝玉这个被宁荣二公视作唯一希望的继承人,同样无法承担起男权社会赋予他的重任。

《贾宝玉论》
作者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才会在开篇就自陈:“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
这种沉痛的反思,在贾宝玉出场时的《西江月》中得到重申。正因为作者意识到“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才会在愧悔之余,去客观地呈现在贾府败亡的过程中,女性管家者的竭心尽力与男性当权者的堕落腐化,为女性翻案,为“祸水”正名。
其次,《红楼梦》还回应了一个叙事传统,那就是无论正史还是民间稗说,都充斥着“女祸论”的陈词滥调。《红楼梦》既有意“洗了旧套、换新眼目”,有别于那些风月笔墨,自然不会甘于蹈袭祸水叙事。《红楼梦》之前虽不乏为祸水平反的声音,但实在有限。
如在女祸论盛行的唐代,诗人罗隐曾不合时宜地写了一首为西施平反的诗:“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20]
后来吴伟业作《圆圆曲》“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21],还是沿用了祸水论的套路。、
关于祸水问题,鲁迅曾发表过一段犀利的论述:

《且介亭杂文》
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信妲己亡殷,西施沼吴,杨妃乱唐的那些古老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决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但向来的男性的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有出息的男人。[22]
鲁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他的观点尚且领先其时代,时光倒退两百年,久处封建社会的曹雪芹也能够表达出同样的观点,就更加难能可贵了。
小说第六十四回林黛玉作《五美吟》[23],分别题咏了西施、虞姬、王昭君、绿珠、红拂等五个薄命红颜,并从女性生命价值的角度重新审视了这几位“古史中有才色的女子”,她们最大的悲剧是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她们的薄命都源于男性的失败与无能,否则不会有西施入吴、虞姬自刎、昭君出塞、绿珠坠楼和红拂夜奔。
正如上引鲁迅所说,男权社会中,女子没有那么大的能量去背负兴亡的责任。小说第七十八回贾宝玉作《姽婳词》,感叹“何事文武立朝纲,不及闺中林四娘”,用戏拟的手法对《长恨歌》《琵琶曲》等“男性中心主义言情模式”的突破[24],对女色误国主题的创造性的转换,也呼应了小说首回说不借“历来野史,皆蹈一辙”的套路,“令世人换新眼目”的构想。
作者在自省与翻案之余,还思考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谁才是悲剧的真正罪魁,是什么造成了悲剧的无解?

《中国小说史略校注》,鲁迅著,陈平原、鲍国华编注,浙江人民出版社2024年1月版。
尽管小说作于所谓的康乾盛世,但小说开篇就点出了“末世”二字,并道出悲剧周而复始,非人力所能改变——如执迷不悟的贾宝玉,会沦落到“寒冬噎酸齑,雪夜围破毡”[25]的下场,但改弦易辙的甄宝玉,也没能逃脱甄家被抄、家族败亡的命运——二人殊途同归。
鲁迅说,贾宝玉呼吸领会到了“遍被华林”的“悲凉之雾”,所谓悲凉之雾,其实就是一种末世的气息。在这个“末世”中,不仅绝大多数女性没有施展才华的可能,男性们也必须按照修身齐家入世的道路规划人生,罪魁祸首其实是僵化了的男权制度。
《红楼梦》没能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也无法预测现代社会男女平权的到来,但它认识到了问题所在,就足以领先同时说部了。
总之,《红楼梦》作者用“辛苦不寻常”的十年光阴,完成了“字字看来皆是血”的自我超越。他从同情女性的遭遇,欣赏女子的才情升格为自我的剖析与社会的反省。

《王国维文学评论三种》
小说将男女并举,勇敢地正视男权社会中既得利益者的腐朽与退化,指出他们的失德与失职,颠覆了以往正史稗说用红颜祸水来替罪的祸水叙事,实现了为闺阁昭传的直接目的,同时也将个体悲剧与家族悲剧引向更深层面的思考,在“康乾盛世”的表象下敏感地察觉到了末世的况味,这才使得《红楼梦》超越《风月宝鉴》及其他小说,成为一部伟大的经典著作。
注释: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明清小说天人关系叙事研究”(22XJA751001)阶段性成果。
[1] [清]曹雪芹、[清]高鹗著,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页。本文所引《红楼梦》原文据此本,不另注。
[2]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外一种:汉文学史纲要)》,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313页。
[3] 参看沈治钧《从〈风月宝鉴〉到〈红楼梦〉》,《红楼梦学刊》2001年第1辑;夏薇《从〈风月宝鉴〉到〈红楼梦〉——成书与创作思想的嬗变》,《文学评论》2022年第6期。夏文提出:“《红楼梦》的作者借用了传统的‘女祸’思想,却没有固守它。”
[4] [清]曹雪芹:《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影印本,第1页。
[5] 俞平伯:《影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十六回后记》,见《俞平伯论红楼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959页。
[6] 俞平伯:《〈红楼梦〉中关于“十二钗”的描写》,见《俞平伯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212页。
[7] 陈文新:《〈西厢记〉:一个文本的复杂身世与多重面相》,《长江学术》2014年第1期。
[8] [唐]元稹撰,冀勤点校:《元稹集》,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785页。
[9] [春秋]左丘明撰,[晋]杜预集解,李梦生整理:《春秋左传集解》,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753页。
[10] [清]曹雪芹著,陈文新、王炜辑评:《红楼梦百家精评本》,崇文书局2019年版,第84页。
[11] [清]曹雪芹著,陈文新、王炜辑评:《红楼梦百家精评本》,第84页。
[12] 王光福:《论〈红楼梦〉中唯一一段骈体写景文》,《红楼梦学刊》2010年第3辑。
[13] 张平仁:《红楼梦诗性叙事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73页。
[14] 参看陈文新《贾宝玉的谱系归属》,见《传统小说与小说传统》,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3—267页。
[15] [清]曹雪芹著,陈文新、王炜辑评:《红楼梦百家精评本》,第309页。
[16] 俞平伯:《〈红楼梦〉中关于“十二钗”的描写》,见《俞平伯学术论著自选集》,第172—178页。
[17] [清]曹雪芹:《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第274页。
[18] [清]曹雪芹著,陈文新、王炜辑评:《红楼梦百家精评本》,崇文书局2019年版,第71页。
[19] [清]曹雪芹:《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第293页。
[20] [唐]罗隐著,李之亮笺注:《罗隐诗集笺注》,岳麓书社2001年版,第73页。
[21] [清]吴梅村著,叶君远选注:《吴梅村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7页。
[22] 鲁迅:《且介亭杂文》,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第177页。
[23] 《红楼梦》第六十四回是否是曹雪芹原笔,虽有争议,但蒙府本、戚序本和甲辰本的第六十四回有一条批语“五美吟与后十独吟对照”,一般认定是脂批。因此林黛玉《五美吟》是曹雪芹原笔,应无争议。可参看侯俊才《〈红楼梦〉第六十四回版本源流考》,《红楼梦学刊》2022年第5辑。
[24] 袁宪泼:《〈姽婳词〉互文性结构及其蕴含的诗学观念》,《明清小说研究》2021年第4期。
[25] [清]曹雪芹:《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影印本,第41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