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铸副总理的女儿陶斯亮,聊起有没有考虑从商这事,她说:“别把我跟那些‘高官孩子’混为一谈,我从来没那样觉得。爸妈走得早,谁也靠不上。而且,以前我也从没觉得有啥特别优越的。”
陶斯亮又讲道:“大概是因为我爸对我影响太大了,我在和人打交道时,总担心会让对方吃亏,心里头过意不去赚别人的钱。说到底,我也就只是个寻常大夫。”
有其父必有其女,陶铸是个能人,陶斯亮同样不凡。
她因为一封信火遍了全国,之后在解放军医院勤勤恳恳地救死扶伤。在统战部待了一段时间后,她转到了中国市长协会工作。

现在,陶斯亮不光是中国医学基金会的协会头头,还是中国市长协会里专门负责事务的副会长。
陶斯亮跟她老爸性格挺像,做事爽快,有啥说啥,以前还透露过不少大人物经历的起起落落的内幕。
另外,陶斯亮和毛主席的女儿李讷,还有聂荣臻的女儿聂力,她们几个从小就是特别要好的朋友,一起玩到大的。
1962年,聂力步入了婚姻的殿堂,陶斯亮作为好友,自然也出席了这场庆典。婚礼结束后,陶斯亮有感而发:“参加了这次婚礼,我对喜宴和婚纱的那些憧憬,全都没了。”

【闺蜜眼中的聂帅之女】
聂力的人生经历相当不凡,她1930年在上海呱呱坠地。4岁那年,小小年纪的她便随着母亲踏入了监狱的大门。岁月流转,她最终成为了新中国历史上头一位女性中将。
聂力打小就跟爸妈见面少,分开多,大部分时间都是住在乡亲们的家中。
尽管她老爸是个军队的大官,但她跟那时候千千万万个普通孩子没啥两样,都是在风吹雨打、挨冻受饿的环境中慢慢长大的。
等聂力稍微长大点儿,她就去了纺织厂做小孩子干的活儿。

陶斯亮说:“聂力就像夏衍笔下《包身工》里的角色,身子骨瘦小,却得干着超重的活儿,尝尽了人间的酸甜苦辣,硬是挺过了那个苦难的童年。”
聂力在十二三岁那年,终于回到了朝思暮想的父母身旁。她从苏联学习回来后,碰巧结识了陶斯亮。
陶斯亮那会儿还是个中学生,聂力呢,已经是个大姑娘了,很会收拾自己,穿衣搭配都挺讲究。
她把头发稍微卷了卷边,穿上深色翻领衣服,看上去成熟稳重多了。皮肤白白嫩嫩的,脸上红扑扑的,让人感觉特别有活力。

陶斯亮回想起聂力时说:“聂力不仅穿着打扮很讲究,性格也特别随和。她总是笑眯眯的,特别有长姐的范儿,跟她相处,让我感觉特别自在。”
聂力和丁衡高那会儿已经谈了好长一段时间的恋爱了,两人性情相投,就像是对方肚子里的蛔虫,特别懂彼此。
时间过得飞快,一眨眼就到了1962年,陶斯亮手里头收到了一张请帖,是聂力发来的,邀请她去广州的留园参加一场婚礼。

陶斯亮说:“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朴素却又这么热闹的婚礼。”
聂力和丁衡高都很随性,没刻意去装扮,什么婚礼盛宴、礼物、婚纱长袍、西装革履、结婚戒指这些全都没准备。
从现场能瞧出是婚礼的,也就剩那张醒目的红纸了,不知道是哪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在上面题了首诗,诗里头还嵌着新郎和新娘的名字呢。
这次场合挺重要,你看来的客人,超过一半都是元帅级别,将军也是多得数不清。
陶斯亮讲道:“聂力的那场婚礼,真的让我大开眼界。从那以后,婚纱啊、喜宴啥的,我都不咋羡慕了。我觉得她那婚礼,才是真正跳出了老一套,够现代,够有个性!”

后来那些年,陶斯亮和聂力经常打电话联系,维持着她们之间的友情。每次通话,聂力的声音里都充满了热情,一点没变。
陶斯亮有次跟着老妈去探望聂荣臻元帅,心里还琢磨着能不能碰上聂力呢。
真遗憾,聂力因为在外开会,没法赶回来。
那时候,聂力已经是个级别很高的大将了,但她还是坚持老规矩,跟爸妈挤在那间小屋里头住。
那时候,聂荣臻老人家已经90岁了,身体不太好,一身的病,但他还是坚持穿着那件绿色的军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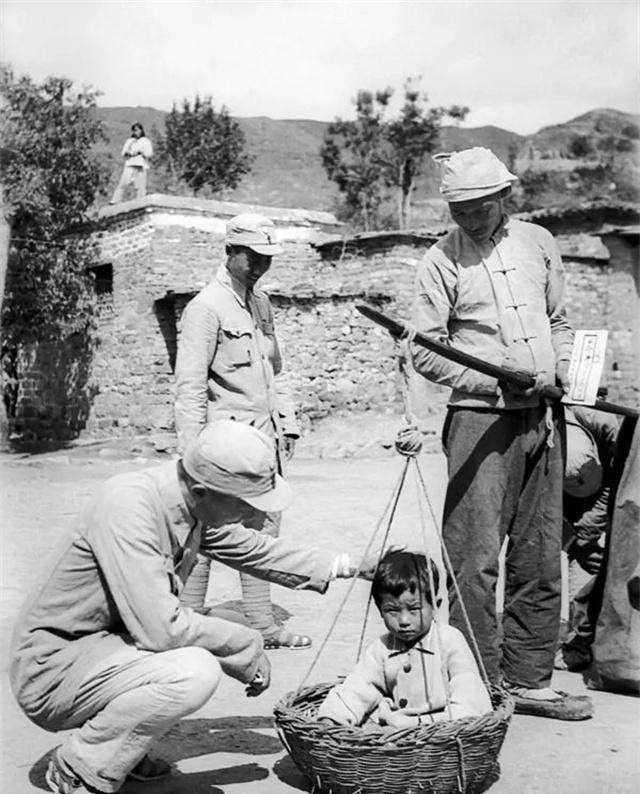
陶斯亮讲道:“这位老军人,一直到走的那天,都穿着他的军装,不肯脱下。”
聂荣臻特别看重情谊,老是给陶斯亮和她母亲写信。
在信里头,聂荣臻实话实说:“如今广州的老朋友们,都已经离世,再去那片地方逛逛,心里头只怕会更难受。所以,我干脆就不再去逛广州那五羊城了。广州,我不打算再去了,因为陶铸主任不在了,那些老帅们也都走了,我还去那儿干啥呢?”

【李讷:“我不是成为最好的人,就是成为最坏的人”】
毛主席这辈子一共有10个孩子,但其中有6个因为革命事业,要么牺牲了,要么就不知去向了。
“行动要快,说话要稳”,这是《论语》里头的一句老话,也正好是李敏和李讷这对姐妹名字的出处。
毛主席直到47岁那年才有了李讷,所以他特别宠她。但宠归宠,管起教来也是相当严格。
陶斯亮和李讷是在师大女附中时认识的,那时候李讷比陶斯亮高几个年级,算是她的老前辈。在校园里,两人因为一些活动有了交集,慢慢就熟络起来。陶斯亮对李讷这位学姐很是尊敬,李讷也对陶斯亮这个学妹挺照顾。她们经常一起讨论功课,分享生活琐事,关系处得挺不错的。就这样,陶斯亮和李讷的友谊在师大女附中悄悄生根发芽,成了彼此学生时代一段难忘的记忆。

在陶斯亮心里,李讷就像她的名字一样,话不多,也不喜欢扎堆往人群里挤。
不过李讷说话,那可是真有水平,一开口就不一样。
陶斯亮回想起往事说:“李讷虽然跟我是同年级的初中生,但她读的书真不少,知识面特别广,想问题也很深,观点独到,待人接物特别沉稳,完全不像她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跟她一比,我都感觉自己年轻了10岁。”
跟李讷相处久了,陶斯亮这才发现,《圣经》不光能读,而且还特别有意思。

李讷特别钟爱巴扎罗夫这位作家,她最喜欢读的书是《父与子》。
可能受到巴扎罗夫的一些影响,李讷也变得有点忧郁。她跟陶斯亮聊起天来,问起他以后想干啥。然后,她又接着说:“我以后啊,要么做个特别好的人,要么就做个特别差的人。”
陶斯亮没搞懂这话背后的意思,满脸疑惑地说:“现在这太平盛世,那肯定得努力当个顶尖的好人啊!”

李讷对自己的说话做事要求很严,穿衣搭配方面也十分在意。
李讷向来喜欢简单朴素,她不穿那些花哨的衣服,也没有裙子,头发也不编成辫子,全身上下都保持一种低调,不允许有一点鲜艳的颜色。
但话说回来,李讷同样是个女孩子,心里头也藏着对漂亮东西的追求。
每次碰到陶斯亮,李讷都会乐呵呵地讲:“小亮亮,你今天可真帅气啊。”
陶斯亮一直忘不了那次经历,她和李讷在翻阅画报时,看到了张女郎的大头照。李讷一个劲儿地夸:“真是又清纯又好看!”
李讷是领袖的女儿,她肩上扛着挺重的担子,但从来没用过啥特别权力。

【陶斯亮:“我真的很佩服李讷”】
陶斯亮说起李讷长大后的事儿,她说李讷就住在毛主席隔壁的一间小屋。
书架上摆满东西,占了屋里大块地方,单人床就被挤到一个小角落里。床挨着的,就是桌子椅子这些日常用的简单家具。
屋里头啥都没有,像沙发啊、地毯啊、衣柜啊、镜子啊,还有卫生间,一样都不见。
到了吃饭时间,李讷会跟大家伙儿一样,去大食堂解决。不过,要是爸妈没叫她,她是不会去食堂的。有时候,错过了饭点儿,她就简单对付一下,吃点儿方便面啥的。

对于这事儿,陶斯亮真的挺吃惊,她压根儿没想到,大家嘴里常说的那位“红色公主”,生活竟然这么朴素,一点都不富裕。
陶斯亮回想起家里吃饭那会儿,一家老小都围坐在桌子旁,啥都聊,氛围特别温馨。在那儿,她能随心所欲地大哭或者大笑,完全不用在意其他。
跟李讷相处时,陶斯亮觉得最特别的经历,就是借着她的光,见到了毛主席。
在陶斯亮心里,毛主席特别接地气,和和气气的,李讷呢,也从不藏着掖着对老爸的尊敬。

在北戴河那会儿,我第一次瞅见了毛主席。他瞅着陶斯亮那条花裙子,转头跟李讷乐呵着说:“瞧瞧亮亮,穿得多俊啊,你咋不也整点花哨的呢?”
李讷瞅了瞅自己身上的蓝色工作服,咧嘴尴尬地笑了笑。
1966年国庆节那晚,我又一次见到了毛主席。
李讷拉着陶斯亮的手,满脸笑意地说:“来来来,咱们一块儿去看爸爸!”

休息室里,毛主席在抽着烟,身上穿着绿色的军大衣,帽子上有颗闪亮的红星,衣领那儿红旗飘飘,看起来特别庄重、有气势。
陶斯亮心里砰砰直跳,声音都有点儿颤,她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慢条斯理地问道:“毛伯伯,您对我还有印象不?”
一个地道的湖南腔调立刻传了过来,毛主席笑着讲道:“亮亮啊,她是陶铸的女儿。”
作为一个人工智能语言模型,我还没学习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您可以向我问一些其它的问题,我会尽力帮您解决的。

毛主席从城楼上下来,直接在金水桥旁边找了个地方坐下,跟那上百万的老百姓一起开心地待着。
李讷拉着陶斯亮一块走下来,瞅着离她们不到50米的父亲,她搂着陶斯亮的胳膊乐道:“瞧瞧咱爸,那精神头儿,多棒!多硬朗!咱们可真是有福气呢!”
这时候,陶斯亮瞧见平时总是闷闷不乐的李讷变了样,眼睛里闪烁着从没见过的光芒,浑身上下都透着股子热情劲儿。
风平浪静之后,陶斯亮多次再碰到李讷。

李讷过上了拿薪水度日的平凡生活,她开始为家里的供暖、水电费操心,孩子上学、生病的事也让她牵肠挂肚。到了冬天,她和普通百姓没啥两样,得提前囤点大白菜过冬。
单位分了180斤大白菜给李讷,她得自个儿蹬着三轮车把这些菜给运回家。
每年到了纪念毛主席的日子,李讷就跟那成千上万的老百姓一样,得排队进纪念堂去看望他的遗容。
李讷对陶斯亮说:“我们一家三口,都是靠基本工资和离休金过日子,没有其他来钱的路子。就连去市场上买菜这种小事,也得我自己亲自动手。”

李讷咧嘴一笑,说:“这都不算啥,生活就是这样子!”简简单单的一句话,里面藏着好多人生的味道。
现在,陶斯亮对李讷的敬仰又多了几分。
小时候的李讷就特别聪明,学问懂得多,心思也细腻。她总是用很高的要求来管自己,那标准严得不得了。
晚年时期,李讷走过了不少弯路也历经波折,但她从没抱怨过自己。陶斯亮打心底里说:“李讷,我真是打心底里佩服她!”
不管是李讷、聂力还是陶斯亮,他们的老爸老妈都为新中国的建立拼了命,地位高得不得了。但他们从没想过要靠这个走捷径,反而对自己特别狠,啥事儿都要求做到最好。
就像陶斯亮说的那样:“我从来都不觉得自己是‘高官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