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九四五年的深秋,德国哥廷根的街道,在盟军的轰炸后,弥漫着刺鼻的焦糊气息。
一个中国留学生,季羡林,怀里紧紧抱着一个牛皮纸包裹,在满目疮痍的废墟间,高一脚低一脚地奔向郊外。

包裹里,藏着他熬夜抄写的《糖史》手稿,还有几片干枯的海棠花瓣——那是他七年前从清华园里小心翼翼地摘下的。
谁曾想,三十年后,这些花瓣与手稿一同化作了小学课本中的《海棠花开》,而泛黄的纸页间,那股淡淡的乡愁,却是由战火硝烟与故国月色共同酝酿的,不为人知的秘密。

今天,我跟大家聊一聊,小学语文教材收录季羡林的作品以及背后的故事,感兴趣的朋友,不要错开哦。
以下是课本中的季羡林印记:
✎
窗前的花海,二战中的秘密信号
部编版五年级下册的《自己的花是让别人看的》,其实是一篇诞生于纳粹阴影下的散文。
一九四三年的哥廷根,季羡林租住在一位犹太老夫妇的家中。当盖世太保开始搜查庇护犹太人的住户时,他在窗前摆满了矢车菊——这是房东太太教给他的暗号:花盆朝外表示安全,朝内则需躲避。
某个夜晚,空袭警报突然响起,他毫不犹豫地冲回正在燃烧的公寓,抢出了房东太太珍爱的《浮士德》手稿,而他自己珍藏的敦煌卷子,却在那场大火中化为了灰烬。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哲理,就这样在战火中得到了最深刻的诠释。
教材里描写的那片“花海浪潮”,其实当年是犹太邻居们偷偷在每户窗台放置的报春花。
季羡林在散文里并没有提及这段历史,但在给编者的信中,他却深情地说:“如果孩子们能从这些鲜花中读出人性的光辉,那么,那些消失在集中营里的笑脸,也就没有白费。”

✎
夹竹桃的启示:中德文化的交融
苏教版六年级的课文《夹竹桃》,其实,暗含着季羡林独创的“文化交融”理念。一九三七年的某一天,他在哥廷根植物园里惊奇地发现,德国园丁竟然将中国的夹竹桃嫁接在了本地的桃树上。
他惊叹不已,并在日记本上画下了嫁接的示意图,旁边还注解道:“佛经翻译也应该如此——东方智慧为砧木,西方逻辑为接穗。”
这个意象,在二十年后化作了文字,但很少有人知道,文中的“红白相映”其实藏着一段惊险的往事。
二战末期,为了保护房东的犹太藏书,季羡林将《大唐西域记》的手抄本染成了粉红色,与歌德诗集捆在一起,谎称是“中国婚俗典籍”。
当德军搜查时,他指着窗外的夹竹桃解释说:“红色象征智慧,白色代表慈悲,这正是我们东方的辩证法。”

✎
对话中的承诺,未尽的心愿
北师大版五年级的课文《小苗与大树的对话》,记录着一位九旬老人的赤子之心。二零零三年的某一天,季羡林先生来到一所小学接受采访。
当孩子们问他:“季爷爷,您小时候最痛苦的作业是什么?”时,他突然老泪纵横,哽咽着说:“是描红《圣教序》,母亲总说写不好字就回家种枣树。”
众人不知,那天正好是母亲的忌辰。
采访结束前,孩子们送上了一串用枣核串成的项链,季羡林先生颤抖着写下了“幼苗当知泥土香”这句话相赠。
这句话,后来被刻在了他的墓志铭上。而当年提问的那个小学生里,有一位叫李文亮的男孩——二十年后,这个名字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永远地镌刻在了历史的长卷上。

✎
《母亲的牵挂》:一封未寄出的家书
在人教版六年级上册的课本里,《怀念母亲》这篇文章,其实是季羡林先生八十岁时,饱含深情的泣血之作。
回想起一九三三年赴德留学的那个夜晚,母亲不辞辛劳,从山东官庄赶到北平,只为给他送上一包晒干的红枣,并告诉他:“枣树是你出生时栽下的,想家了就嚼一颗。”
这位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农妇,却在儿子远行七年后,因无法寄出那三百多封口述家书,而郁郁而终。家书里,满载着对儿子的思念与牵挂。
二零零一年,当这篇文章被选入教材时,编辑曾建议删去“我痛哭了几天,食不下咽,寝不安席”这样过于激烈的表达。
但季老却坚持保留,并在旁边批注:“让孩子们知道,学问虽无国界,但眼泪永远流向故乡。”
如今,课本里那些温润的文字背后,仿佛还能看见哥廷根地下室油灯下的身影——年轻的季羡林,将母亲最后一封家书:那是同乡捎来的皱巴巴的纸团,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枣树结果了”,贴在《梵语语法》的扉页。
从此,每次读书前,他都会轻轻地触摸那些字迹,仿佛这样就能感受到母亲的温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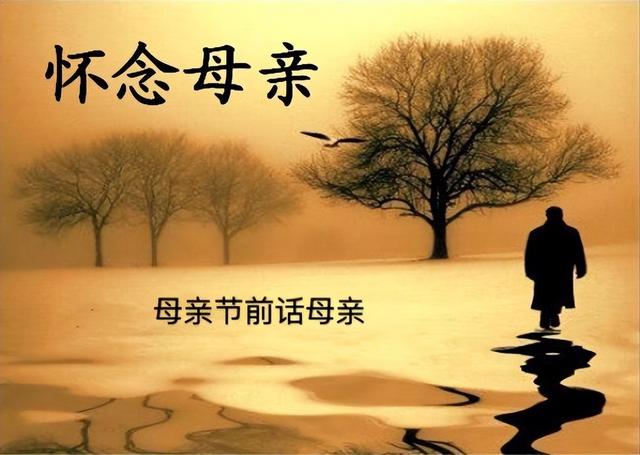
✎
课本之外的季羡林印记
※《怀念母亲》的初稿,是写在德军投降的传单背面上的,如今静静地躺在清华档案馆里;
※哥廷根故居的矢车菊种子,每年都会被德国师生精心挑选后寄往中国的小学;
※教材里删去的那句“我的中国心在敦煌卷子里燃烧”,如今已经成为了香港某中学的壁刻;
※那包未能送出的山东红枣,在二零一二年的某一天,在故居的墙缝中被发现,它们已经变成了晶莹的碳化琥珀,仿佛在诉说着那段尘封的历史。

结语
当孩子们朗读着“爱祖国,爱母亲”时,或许,他们应该更多地了解这位老人——他曾用梵文书写乡愁,用德语翻译《论语》,而他的书桌上,始终摆放着母亲捎来的枣核。
最深的学问,终究要落回泥土里生根。
而那些入选教材的散文,不过是他在东西文明间架起桥梁时,随手撒下的海棠花种,它们在岁月的长河中生根发芽,绽放出绚烂的花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