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次见到郭松龄
1925年初,我来沈阳,本想考取文会书院念书,未果。在街上看到“东三省陆军军士教导队”招考学兵的广告。我当即到北大营报名,经考试被录取,分配到第一营第四连。从此开始了我的军旅生活。
当时的教导队队长是由张学良兼任的,人们都知道他是“少帅”,如果能到教导队当学兵,便于和他发生关系,于个人的前途是有好处的。因此,我就决心进入教导队,不管怎么苦、怎么累,我都咬着牙挺着干。
1925年春,有一天排长(值星宫)通知,要把内务特别整理好,院子打扫干净,本来内务、清洁是每天必须严格整理好的,而今天,还要好上加好,被垛用绳子拉成线分毫不错,同时告诉郭军长今天来视察,大家听到也都很兴奋。因为每天在操场上出操时,都影影绰绰的看到郭军长和二个人抬一挺德国制造的马克沁式重机关枪,和一群人在一起,听指挥的人口令作前进、跑步、卧倒、射击、利用地形地物等动作。那一群人是军官教育班的学员,他们都是各部队抽调来的排长以上现职军官,来受训的。我当时很奇怪,一个当军长的还跟学员一样出操,这在那个时代的军队中是没有的事情。不一会郭军长来到我们连里视察,看到:他的而孔是微白的,两目炯炯有神,说话店音宏亮而爽朗,穿一身软布军衣,黑色钩子皮鞋扎绑腿,系武装带,肩上有一付金光闪闪的中将肩章,一个随从参谋(参谋人员的领章上有铜质带竹节的×,表示胸有成竹的意思)夹着皮包,跟在后面。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郭松龄。
军官教育班
是年八月间,教导队举行期考后,郭又到教导队以营为单位进行点名,凡是期考成绩列在前十名的学兵都挑出去了。我是被挑出者之一。在点名的时候,对每个人都仔仔细细的看一下,并简单的问是哪里人,多大年龄,什么学校毕业等等,然后集合讲话。他说:“看到你们考试的成绩还不错,把你们挑出来,转到军官教育班去念书,希望你们要好好努力用功……”随后我们各人携带衣物、 行李到东山咀子军官教育班本部报到。这时,东大营(即现在的东山咀子)已经建成新的营房,原在北大营教育班学员也都搬到新营房来,他们编成三个队。由教导队挑去的学兵编成第四队,由应鸿伦任中校队长,少校队附有邓玉琢、裴焕彩等二人。
教育班是郭松龄一手经办成立的一个以培养军官为目的的军事教育机构,在军学教育内容上与讲武堂大致相同,但学期为二年,比讲武堂还多半年,另外增加英、法、德、日等外语课,准备将来保送到各国去留学。讲武堂学员的领章是两道红杠,教育班学员的领章中问是一道红杠,学员假日外出时,腰扎皮带,带剌刀,这是与讲武堂学员有区别的地方。
教育班由郭松龄兼班长,彭振国(别名筱秋)少将任教育长负专责,总队长是上校王云汉。教育班举行开学典礼时,郭亲自参加,郭夫人韩淑秀也随同出席。郭讲话时间很长,大意是:“当今世界军学日新月异,武器也随之改进,东北地处两大强邻之间,时时都在窥视我们,执工戈,卫社稷是军人之职责,但必须有新的学识才能担当这个重任,你们都是青年学生出身,具有一般文化,现在既有从成戎之壮志,更应努力学好新的军学知识,现在把你们选到军官教育班受军官教育,国家对你们抱有很大希望,你们要好好用功,勤学苦练,服从师长,不要辜负国家培养你们的厚意……”。以后郭经常到教育班来,有时集合讲话,有时到各处巡视,有时抽问学员们生活情况,看不出是一个当中将军长的大官样子。态度是严肃的,但不是令人可畏,在每个同学的思想上无形中产生一种敬佩之心。
入学后在军事学术科方面,开始与在教导队时相同,也是讲典范令、立正、稍息等制式动作,所不同的是增加有英、法、德、日等外国语课,我被分配到德语班。我在辽阳文德中学学的是英语,还有一点基础,希望继续学英语,分配到德语班很不乐意。向队长应鸿伦请求调换一下,应队长说,“分配到哪班就是哪,不能随便要求”。碰到一个钉子,但心里总是不安。

第一次见到韩淑秀
1925年4月的一个星期天,我去小河沿魁星楼附近安家鞋铺买“傻鞋”,因为他们做的“傻鞋”坚固耐用。当路经水簸箕胡同西口时,我灵机一动,何不到军长家谈谈去,给见就谈,不给见拉倒,反正不是犯错误的事。原先也常听别人说过,凡是去军长家的学生他都接见,因此鼓起了勇气。一进门房,传达人都问,“干什么?”我说见军长有点事。传达说“不在公馆,你是那里的”。我说,“是教育班的学生。”正在这时,韩淑秀由上房出来,(他住的是四合院没有二门)问传达,他那的?传达说:是教育班的学生,要见军长。韩淑秀说,叫他进来,我进了东厢房的客厅。韩淑秀问:“你叫什么名字,见军长有什么事”?我报名行礼后,说,我是新由教导队挑到教育班的学生,分我到德文班学德义, 我英语有点基础,想继续学英语。韩淑秀说:“现在世界各国的军事学,德国最好,叫你学德文,学好后,准备到德国留学不好吗?你有英文的基础,学德文更容易些,实在不愿意学德文和彭教育长说一声给你改英语班”。就这样,我行礼辞别了韩淑秀,到安家鞋铺买双“傻鞋”回到教育班。我听韩淑秀这一说,学好将来可以到德国留学,我也就没有再请求转英语班了。(当时教德语的教官是齐世英又名齐铁铮,现在台湾任立法委员) 不久,奉军进兵关内,由河北、山东、安徽又进而占领江苏直达上海,这是奉军最盛时期。军宫教育班第一期的学员,也没等到毕业,都纷纷回到原部队任职去了。
我留在郭松龄身边
因为军队都纷纷进关,各部队的初级宫员都需要补充、调换。我们第四队的学生,郭松龄也都挑年龄大的陆续派到部队当准尉排长,每派一个人,郭事先必须找去详细的问话,然后亲笔写一个二寸宽五寸长的便条“派令”。也不通过主管人事部门办手续,就拿这个“派令”直接到差。“派令”是这样写的:“兹派×××为×旅×团×连准尉排长,克日前往报到,并具报,此令。”郭松龄签字,并发给五十元钱买指挥刀、军衣罩、武装带、鞋、帽等物,一个个都高高兴兴的前往报到。
当时在军中无论办什么事情,只要有郭松龄签字的便条,什么事情都可以办到,也可见郭在奉军当中时的权势了。全军排长以上的军官,郭松龄虽然不能个个都认识,但每个人对郭都有爱戴的心情,因此,郭松龄三个字当时在奉军中各级军宫的脑海里印象很深。也是由于这一点,而造成他倒戈反奉的基础。
“官雨”越下越大。最后一直派到年满20岁的都出去当“官”了。我那年十九岁。填表时,我也把年令自己长了一岁,也填上二十岁。有天郭找我,当时认为这回外派该轮到我了。当我到办公室行礼后,郭说:你十九岁为什么要报二十岁。我说,二十岁不就可以当官了吗?郭笑啦,随即说,不要着急当宫年令还小,没有带兵的经验,也没有作战的经验,以后还怕没有官当嘛?最后剩下十七至十九岁的学生六十多个人,郭松龄集合讲话,说:“你们年令还小,没有带兵的经验,更没有作战的经验,现在军队出发,有战斗任务,就不再往外派你们去当官了。把你们分给‘少帅’(张学良)一半, 其余的留在我身边”。随即点名分开了,我分到郭的这边。不久我们随郭松龄去天津。驻在河北大街曹家花园内,(系北洋军阀曹锟住宅)我们每天轮流值勤四小时,其余的时间规定看书,打球,不准随便外出,有事向队长请假。韩淑秀经常给我们讲些历史故事,我记得有一次讲“楚汉相争怀王立约先入关者王”的故事。有时也问我们每个人家中情况,如问你是哪县人?父母都在不?家里还有什么人?哥几个?家里有地没有?打的粮食够不够吃等等琐事。她身穿布衣,颜色都是很朴素的,不事装饰,说话很柔和,没有一点官太太的架子。
滦州车站军事会议
十一月上旬郭松龄因病在天津住意大利医院,韩淑秀随同前往,我们卫士也去了几个,换成便衣住在医院作警卫和传达,每天来往出入的人很多,究竟做什么,说些什么我们无从知道,不久,郭出院我们由天津上火车,听说是回奉天,大家都很高兴,离家快一年啦,这时可以回老家看看。不料郭的专列指挥车到达滦站即停下来,在一个火柴公司楼上召开了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团、旅长和司令部的高级幕僚,其中认识的有邹作华、王静轩、郜汝廉、殷汝耕、齐世英和曾给黎元洪当过内务总长的林长民,当秘书长的饶汉祥等三、四十人,韩淑秀也参加会议,调一个亲信的步兵团担任外卫警戒;内卫警戒由卫队担任;会场内外的警戒则由教育班的三十多个同学担任。我们每个人都佩有一支短八分的合子炮,和一挺“巴尔克满”手提式轻机关枪,胸前系有皮子弹袋一条,内装四个“保弹板”全付武装担任警戒勤务,没有郭的手令任何人不准随便出入,在楼梯间和楼门口都有岗哨。真是里三层外三层,警戒森严。在楼梯间一个小屋内有一位身材矮小年约五十多岁,手里拿着旱烟管,倒背着两手,来回踱着慢步, 屋里点一支腊烛,最初不知他是何人, 后来听总队长王云汉说,他是姜督办,我们心里想,怎么把督办押起来啦。(姜登选别名超六,安徽人)在会议开始,郭讲话时间很长,讲话大意现在经过仔细回忆有这样一些话:历年来战争耗财巨万,致使东北民穷财尽,钱法日益毛荒,去年与曹、吴之战,是我们为保土安民故不得己而为之,此次之战,师出无名,徒为姜、杨争地盘,为上将军谋总统,这种兵连祸结,为少数人谋利益,争地盘而空耗国币,徒增民困。此时班师回奉,纯为清除乱源,改革东北政治,不事内争,而以休养生息为日的。上将军年事已高,暂息仔肩,饴养天年,让位与少帅,内修政治整军经武,外御强邻以固边防……。韩淑秀也讲了话,大意是说张作霖多年来穷兵黩武的罪恶事实,把一个物产丰富土地肥沃的东北家乡祸害得民穷财尽百姓吃不饱穿不暖,孩子们不能念书,我们跟前这帮孩子就是例子,他们念不起书,才出来当兵,不兴办教育,不培养人才, 不开发实业, 徒事穷兵黩武给少数人争权夺利……。他(她)们的讲话,我们值勤的人都听得很清楚,真是感人肺腑。会议结束把部队改为东北国民军。已快天明,第二天看到一份油印的,电文很长的一份通电,历数张作霖历年来勾结日本,签订条约,以大量的金钱购买武器,从事争夺地盘的罪恶战争。这份电文是饶汉祥的手笔,下署“东北国民军总司令张学良、副总司令郭松龄。”我们看了这个名的电文,心里说,儿子倒他爹的戈了。紧跟着一道“升官图”的命令,团长升旅长,旅长升军长,如刘振东、刘伟、范浦江、霁云等均由旅长升为军长。魏益三初为参谋长,旋即调为第五军军长,参谋长调炮兵司令邹作华升充。邹作华原任东北军的炮兵司令,是炮兵界的权威者,郭的反奉倒张,邹在内心本不倾服,以此调任参谋长,孰知后来郭军方面将不用命,士无斗志,特别是炮兵部队不发实弹、邹还暗中通款,张作霖向前方部队发出传单,很起作用。郭的失败,这也是原因之一。

枪杀姜登选
在滦州会议的当夜,郭将姜登选扣押在火柴公司的楼下一个楼梯间。姜之所以被扣,是姜由天津乘专车返奉路经滦州时,郭闻姜的专车到达,以请姜氏唔面为名,遂即扣押,但并未见面,会议第二天郭的专列指挥车仍停在滦州车站,升火待发,下午听到把“姜督办枪毙了”的消息,以后又听到枪毙时经过的情形是:由一个王副官(左手有残疾,外号叫摔瓜子)带两名卫士坐汽车以送姜到城里为名(车站距县城八里路)行经一段沙滩地,车就不走了, 由王副官向姜说, 这是段沙滩地,车子不好走,请督办下车走几步吧!姜即下车前行,王副官在后面,走不几步,王即向姜开始射击,“砰”的一声,姜即应声而倒,随后连打两枪。显赫一时当过安徽督军的姜登选,就这样丧生于沙滩。王等收尸体就地掩埋后,即回车复命去了。郭军失败后,张作霖为纪念姜登选,在奉天城西南面风雨坛,修了一座祠堂,名曰“姜公祠”。
挥军东进、连山暂停
郭松龄此时已将所掌握的奉军精锐部队(约七万人)编组为四个军,以刘振东为第一军军长,刘伟为第二军军长,范浦江为第三军军长,霁云为第四军军长,担任第一线攻击部队。以魏益三的第五军军长(预备军)在九门口、石门寨一带担任后方。当时郭认为奉天所有精锐部队都在自己掌握中,沈阳没有部队,吉林第十五师长张作相部曾占据山海关,但不堪一击,黑龙江省虽有两个骑兵旅没有多大的战斗力,而且鞭长员及。利用“南满铁路”运输须与日本交涉,拖延时日,如由草道轻骑南来,最快也得两个星期,等待江省骑兵到达而郭军己占据奉天了。因此,郭充满必胜的信心,预定十二月二十四日以四路纵队进入奉天,届时江省骑兵即使到达奉天,也无能为力了。但事情的变化非郭氏始料所能及,竟因江省骑兵迅猛到来进击郭军的左侧背,郭军后路被抄袭,遂致一败涂地。
郭军先头部队进抵山海关,一举将吉林第十五师击溃,猛烈追击继续东进,经过缓中、兴城。先头部队已到达锦州,而郭氏的指挥列车到达连山,时值天气严寒,遂休兵三日等候由天津运来棉服装,第二天棉服装与现大洋都已运到连夜分发到官兵身上,又发了双饷,都是白花花的银元,官兵领到后全军踊跃,士气大振。据由天津运服装回来的同学李树国说“这次好危险,差点没叫李景林给扣住,服装现洋装车后,刚要开车,这时车已开动,押火车头的人叫快开,他们就向火车开枪,我们(随去的卫队)也还击,这样才跑出来,好危险啦。
部队沿途无阻,迅猛东进,郭的指挥列车,紧随第一线前进。
当指挥列车到达锦州时,某日(确切日子忘记)值勤的同学忽然见到殷汝耕秘书陪同几个穿西装的人上车,与郭氏会见,同学们相互私议说,今天来了几个穿西装的人,个子不高,看样子象日本人,见总司令去了,不知干什么,但不到几个钟头就由殷汝耕陪同走了。指挥列车继续前进,最后到达柳河沟车站因机车无水而停止。

徒步入新民,化装逃走
部队官兵穿上棉衣、领了银洋士气高涨奋勇前进。当第一线部队到达新民县以东巨流河一带时,前方情况发生突变。并先表现在炮兵部队方面,据事后曾在炮兵当排长的关荣葛(三三洼人现还健在)说:“炮兵打出去的炮弹没有‘引信’打到对方不爆炸,步兵部队也迟迟不前进了,当时各部队也都发现了油印的反战传单,其中有这样的话:“我们都是自家人,不能给他们当炮灰互相残杀,吃老张家的饭,不打老张家的人。”……因此军心涣散,士无斗志。 白旗堡站 (现已改大红旗站)以东沿线的水塔,悉被奉军采纳外籍顾问伊亚格(不知是某国人)的建议,完全炸毁。这时郭的指挥车正停在白旗堡,由白旗堡再东进,机车无水可上。郭令百姓挑水往车里倒,由于天寒路远,滴水成冰,一担水连酒带冻倒在机车里所剩无几,这样又勉强前进到柳河沟,这个站又无多少百姓,因此,郭松龄弃车,亲自作前边率领全体幕僚,卫队徒步向新民县前进,(柳河沟距新民县十八里路)郭夫人韩淑秀坐大车,所有马匹都由少数高级幕僚和卫士们骑乘,在后面跟随,到新民县城内已进入黄昏,在一个烧锅院内住下,立即召开紧急军事会议。这时前线的枪炮声稀稀拉拉的还在响,入夜后火光冲天弹药爆炸声震憾原野,俄倾传来白旗堡弹药被炸粮服被烧的消息,官兵心中不安,郭氏夫妇见大势已去,次日天甫黎明,郭松龄身穿灰布面的皮袍,头带貂绒皮帽,穿灰呢子马裤。韩淑秀穿青布面的皮袍,围一条青色的毛线围巾,同坐在四套马的民间大车上,每个人身上各披一条俄国毛毯,与郜汝廉耳语几句后即出南门,企图奔立山车站上火车赴大连,卫队随后跑步跟上,所有马匹,都由幕僚和卫士们骑着,随在车后前进。
走出新民
走出新民县约廿余里到一个村子边(村子不大可能叫苏家屯)时,忽由前村发出枪声,初时,认为“联庄会”为防止溃兵而鸣枪,立即派人骑马前往通知说:“是郭总司令来啦,不要打枪”语甫毕,枪声更密,随之开了迫击炮,卫队们即利用地形卧倒还出,此时,郭氏大妇下车,由卫士关庆忠等二人扶入附近一家菜窖内隐藏,窖口用稻草盖上。随同郭氏前来准备成功后当后天省长的林长民中流弹殒命(他留有日本民胡子最容易认识)饶汉祥由同学王绍华挽扶隐藏起来,事后化装逃亡日本。当卫队与村内对抗时,由前方村内出来大批骑兵,跃马端枪,冲向卫队而来,咀里一边高喊“交枪不杀”一边骂骂咧咧的说这都是“郭鬼子小白脸子”卫队员兵素无战斗经验,又无指挥者,当即纷纷交枪,都跑到老百姓家烤火取暖,骑兵到处搜查,问我们:郭鬼子跑到哪里去啦,我们说不知道。最后由菜窖中将郭氏夫妇搜出去,随后又挨个搜腰,把新领到手的现大洋都搜去了。这时我们才知道,这批骑兵就是昨天夜间袭击白旗堡车站,纵火焚烧粮秣弹药新由黑江汇到来的穆春骑兵旅的王永清骑兵团。 王永清是胡匪头子,匪号“天下好”投降后改编为骑兵团任团长,归穆春指挥。当时,郭氏夫妇如能乘马突围脱险可以侥幸逃生,但郭氏顾着夫人韩淑秀不会骑马,而自己骑马纵然逃出围困,陷夫人于死地于心不忍,所以甘愿同归于尽。

当张作霖听到郭松龄倒戈的消息后,此时沈阳已无兵可调,吉林十五师由山海关败退下来,已溃不成军,江省骑兵虽以急电来援,但恐远水解不了近渴,在这种焦急的情况下,一方面急派教导队上校队附王瑞华为补充旅少将旅长,克日编组新军。一方面将珠宝细软物资完全运到日本站托日方保险,同时将“帅府”周围遍置煤油筒,准备一旦郭军入城即纵火焚烧使成焦土。张作霖当时说:“他妈拉巴子郭鬼子来时,给他剩一把掉咀的茶壶和三个茶碗还有一个掉把的别的你别想”(听大帅府的家人说的)。可见张作霖是决心要烧掉一切。待张学良由天津乘“海圻”兵舰到营口,登陆返沈后,除深受乃父痛骂外,督令王瑞华加速编组新军阻郭东进。王瑞华以教导队官兵为基干派中校教育副官邵文凯为上校参谋长,韩光策、范先炜、王以哲三个营长分别升任补充上校团长。开赴兴隆店,巨流河布防,阻止部军前进。
押送老达房夫妇遇害
王永清将郭氏夫妇由菜窖搜出后,立即报告穆春。并押解到辽中县老达房烧锅院内。穆即直接报告给张作霖(按例穆春是吴俊升所属的旅长,应先报告给吴,由吴再转报张作霖,而穆没有这样做,使吴俊升吃醋,以致后来遭到吴对穆处处不满),张作霖接穆春电话报告时,以手加额说:“他妈拉巴子可把郭鬼子捉住了,把他给我送沈阳来,我亲自枪毙他。继而一想,又给穆春打电话说:“把郭鬼子给我看好,我这边派人去取他”。随派卫队团少将团长高金山等待卫官二十多人乘两部大汽车准备前往老达房押解郭氏夫妇。杨宇霆怕郭氏到沈阳后与他有影响,遂矫张命在老达房就地枪毙。高金山到达后,遂宣布处死刑的命令。韩淑秀对郭说:“我为君死、 君为我亡,先毙我吧”。高金山问郭,你还有什么话要说么?郭没有说话,就在屋内执刑(一说在辽中县老达房南三、四里地方的辽河滩上被枪决的)尔后用棉被裹上尸体,装到大汽车内运回奉天,在小河沿暴尸三日以泄恨。市民观者如堵。以后由其亲友将尸收殓。

当郭氏由新民出走后,第二天张学良进入新民,其随员即住在郭氏前一晚的房内,听到郭氏被俘的消息后,欲令穆春先将郭送到新民县,打算把他放走。这个想法商诸于随他到新民县的亲信幕僚,机要秘书刘鹤龄(即刘鸣九),刘说这个事情你可要好好考虑,“老将”(指张作霖)这样震怒,能行吗?
话是有这么一段,但未得实行而郭氏夫妇已被杀。
1926年奉军进关。张学良任第三方面军军团长,韩麟春任第四方面军军团长。两军团合署办公。当时冯玉祥的西北军队在京汉铁路沿线,正面是国民第二军岳维峻部。奉军当时派有于珍、荣臻、赵恩臻三个军(当时称为三臻下河南)与岳维峻作战。当时河南老百姓到处都有“红枪会”的组织,由于奉军纪律坏,行动野蛮,到处遭到“红枪会”的袭击,再加上岳维峻的反攻,结果三个军几乎全部覆没。适张学良与韩麟春都在火车上听到这个败耗,张学良痛哭说:“假若郭茂宸在,不会遭到这样惨败”。尔后还不止一次的这样说,使韩麟春十分难堪和憋气。可见张学良对郭松龄思幕之情与信任之深了。内容来自《大东文史资料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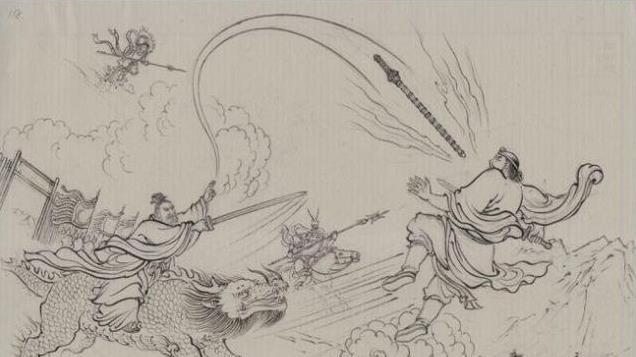



你抄的别人的回忆录?你是怎么有脸发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