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县东北50公里处,有个名为开慧镇开慧村的小村落,地处偏远却山清水秀,风光旖旎。
两座巍峨山峰间,一条清澈小河流过。村庄里,一座坐西朝东的方形土坯宅院,乃烈士杨开慧故居,门匾书“板仓”,为毛主席亲笔。

多年来,纪念杨开慧的群众纷至沓来,怀着深切怀念参观此地。了解毛主席与杨开慧的爱情故事后,众人常感叹:若杨开慧未牺牲,那该多好。
【遇见毛泽东,是她这一生最幸福的事情】
20世纪初期,中华大地遭列强侵略,国内变法亦告失败,文明受损,民众陷入苦难之中。
杨昌济先生自幼饱读诗书,深忧国家。他时刻牵挂国运,但感个人力微,遂隐居乡间,致力于教书育人。
杨开慧2岁时,其父杨昌济怀抱救国救民之志赴海外求学,历经英国、德国,苦读十年,终获成就,载誉归国。

杨昌济出国前夕,致信女儿,详述学习要点,嘱咐其遵循信中指导进行学习。
杨开慧自幼缺失父爱,却遵循父信教导,4岁熟读《三字经》,6岁能读《木兰赋》,7岁入读杨公庙官立第四十小学。
杨开慧出身书香门第,自幼对知识充满渴望。杨昌济回国后悉心教导女儿,促使杨开慧逐渐形成“为民出力”的坚定信念。

日后,她常言:“应做对社会有用之人,行事须有益于社会。”对此,杨昌济深感欣慰。
1913年,毛泽东赴长沙求学,成为杨昌济学生。自那时起至1918年,五年间,他一直视杨昌济为人生导师。
杨昌济满怀热情,结识毛泽东后,认为中国未来可期。因这青年学识渊博,勤奋异常,且对事物洞察独到,极为不凡。

毛泽东与蔡和森等人长期拜访杨昌济,于其家中共议时局,深入交流探索救国救民之道。
杨开慧对毛泽东有好感,但毛泽东与蔡和森均立誓,为救国救民,甘愿一生不娶。
向警予与蔡畅等杰出女学生亦表明决心:“我们誓以身许国,决定终身不嫁,矢志不渝。”
杨开慧对毛泽东深感敬佩,谈及与毛泽东的爱情时表示:“我未曾料想会与他成婚,因我曾决心终身不嫁。”

1918年夏,杨昌济受聘北京大学教授,携杨开慧赴京。同时,毛泽东自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经杨昌济推荐,至北京大学图书馆任职。
青年毛泽东视来北京为其人生的重要转折点,这一步对他的未来发展具有关键作用。
在北京,他结识了李大钊、陈独秀等杰出导师,受其影响,广泛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革命思想逐渐确立。

毛泽东非北大生,却以顽强好学、孜孜不倦闻名北大,此精神令杨昌济对他刮目相看。
1920年,杨昌济病危,嘱毛泽东照拂杨开慧,并致信章士钊,言救国须倚重二人,乃当世英才,望善待。
“二子”中的一位便是毛泽东,他是其中的重要人物。

杨昌济将杨开慧托付给毛泽东,既因在毛泽东身上看到希望,更因二人感情已日渐成熟。
在北大时,杨开慧每日探望毛泽东,并常相伴散步交谈。毛泽东深知她才华横溢,自己也爱阅读,故两人每次聊天皆十分投入,十分契合。

1921年,杨开慧追随毛泽东号召,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首批女共产党员。
入党后,杨开慧积极支持毛泽东工作,并肩负湖南地区党的交通联络重任,虽艰险重重,她仍不懈怠,努力搜集工人情报,传递党的关键文件。
自结婚至1927年,杨开慧随毛泽东辗转长沙、上海、广州、武汉等地。她不仅是毛泽东的妻子,更是其革命伙伴,两人志同道合,堪称天作之合。

1927年,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基于中国形势,率部前往井冈山。未料,因敌封锁,他与杨开慧断绝了联系。
1930年,毛泽东从报纸上得知杨开慧被害,心痛至极,回想分别场景,难以想象她这三年的经历。

【临终前的七个字,证明一切】
与毛泽东失联后,杨开慧日日怀念,坚持给丈夫写信,但因环境恶劣,所有信件均未能寄出。
她遵组织安排,携子秘返板仓开展地下工作,积极发展党组织,于长沙、平江、湘阴边界独自斗争三年。

她在生活中承受巨大压力,育有三子且杂事繁多,然而,她依旧坚持革命工作,未曾放弃。
1930年10月24日,杨开慧遭敌捕。敌人逼问她毛泽东行踪及党内情报,她坚决回答:“不知道”,始终未吐露任何信息。

杨开慧的大儿子毛岸英同样被捕入狱,但她坚贞不屈,对敌人言道:“死只能恐吓胆小之人,于我无所畏惧。”
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于长沙识字岭壮烈牺牲,年仅29岁,她死前坚毅表示:“砍头不过如风吹拂过一般。”
长沙民众得知毛泽东妻子杨开慧被杀,悲痛万分,毅然夺回其遗体,安葬于老宅后方。

毛泽东得知后,致信岳母:“开慧之逝,无法弥补,百身难赎。”
意为,即便百个我亦难换回你。白居易《祭崔相公文》云:未归田园,已舍馆舍。百身难赎,一梦不归。
毛泽东渴望以己命换妻命,却已无法挽回。他不能沉沦,因革命未竟,责任重大。

毛泽东与杨开慧感情之深,可从他为妻所作诗词中窥见一斑。诗词里蕴含着他对妻子的深情厚意,展现了两人情感的深度。
【毛主席思念杨开慧,一字一句真真切切】
毛泽东同志既是领袖也是诗人,对妻子情感深厚,曾创作多首诗词,其中给杨开慧的就达三首。
1921年,新婚不久的毛泽东外出考察,因思念杨开慧夜不能寐,遂于枕上起坐,创作了《虞美人·枕上》一词。

从“夜长难明,披衣起坐数寒星”可见,毛泽东对妻子满怀深情。
1923年,毛泽东创作《贺新郎·别友》,建国后发表。此词为杨开慧而作,情感真挚,风格近似“长亭送别”,令人动容。
重点提及第三首词,即著名的《蝶恋花·答李淑一》。

1957年,杨开慧同窗李淑一致信毛主席,忆及曾为杨开慧作词却遗忘内容,实则指《虞美人》,遂请主席重抄一遍。
但毛主席未选择抄写,而是亲自创作了一首诗赠予她,这首诗便是《蝶恋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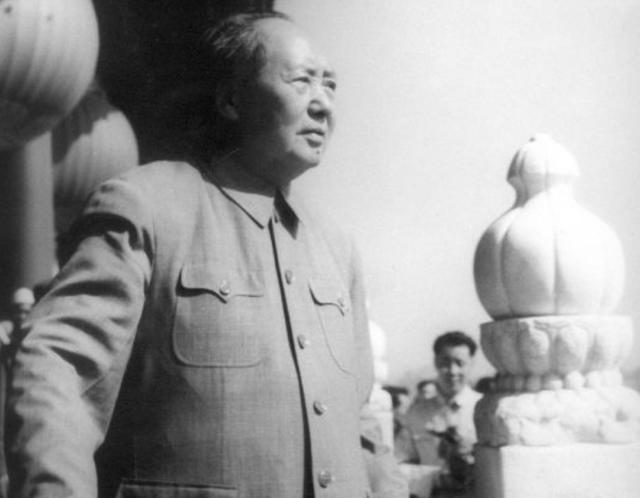
多年来,毛主席的这首词在情感表达上持续引发广泛争议。
毛主席未直接抄《虞美人》给李淑一,而是另作新词,此举或因原词意境、背景与个人情感表达需求不符。
有人认为毛主席或许忘了那首歌,实则不然。
毛主席一卫士回忆,60年代,毛主席曾亲笔写下这首词,并嘱咐卫士妥善保存。
重新创作的原因在于,它能够满足新的表达需求,创新内容形式,保持信息的时效性和吸引力,同时促进文化和艺术的持续发展。

毛主席一生所作诗词,多为豪放之作,他偏爱李白、苏轼等豪放派诗人,因此,其婉约风格的诗词创作数量极少。
但毛主席情感细腻,见亡妻好友信,不会草率回复。一因不愿再提那首“私密”之词,二因极度怀念杨开慧。

毛岸青忆述,曾请父亲重写《蝶恋花》。毛主席书“我失杨花”,岸青疑惑应为“骄杨”。望父亲时,已见老泪满面。
在毛主席心中,“杨花”或许更恰当,她作为温柔女子,是他毕生的挚爱。

【杨开慧手稿重见天日,遗憾主席未能见到】
1982年,长沙人员在修缮杨开慧故居板仓杨家老宅卧室时,于墙缝中发现其1928年前后手稿。
手稿藏于墙缝五十余载,纸张泛黄,字迹却清秀流畅,清晰可见。每位观者皆深感惊叹,无不为之动容。

杨开慧赋诗一句:“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此句表达了她对毛泽东的关切,询问其足疾是否痊愈,寒衣是否准备充足。
贺子珍忆及初见毛泽东时,他因长期步行患重“足疾”,每日需药水浸泡。这证实了杨开慧信件的时间与内容均属实。
遗憾的是,1976年毛主席已逝世,未能亲眼见到这些珍贵手稿。

若毛主席见这些手稿,或再被往事触动,亦可能催生更深情的诗词。
但历史不容假设。事实既定,无法更改,过往的轨迹不会因假设而偏移,只能从中汲取教训,面向未来。
杨开慧当年藏手稿乃明智之举,牺牲个人成就大局。为天下孩童,她作为母亲与共产党员,作出了最伟大的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