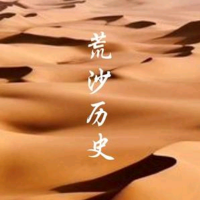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是个不寻常的年份。世界局势在变,大明王朝更是内忧外患,风雨飘摇。这一年,奥斯曼帝国的苏丹苏莱曼二世出生,意大利的天文学家伽利略却在教会的软禁中离世。
咱再看看中原大地,大明帝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崇祯皇帝朱由检 17 岁登基,接手的是个朝政昏聩、宦官专权的烂摊子。魏忠贤结党营私,只手遮天,还想把新皇帝玩弄于股掌之间。国家内政混乱不堪,外部环境更是岌岌可危。辽东有皇太极虎视眈眈,西北还有李自成、张献忠等领导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
这年二月,张献忠攻陷了安徽庐江和无为。本来丢两座城池也不算啥大事儿,可这次不一样啊!张献忠不仅攻城成功,还在巢湖搞起了军队拉练,而巢湖离明朝留都南京和凤阳皇陵可不远。南京要是丢了,明朝对南方的控制权可就没了;凤阳皇陵那可是老朱家的祖坟,要是被刨了,皇家的脸面往哪儿搁?崇祯皇帝能不发火吗?负责剿匪的官员也被严惩,凤阳总督一夜之间就被免职了,新总督马世英上任,肩负起抵抗敌军的重任。
马世英到任凤阳后,发现凤阳城防薄弱,守军不足千人,还都是老弱残兵。他就派手下将领李章玉回贵州老家招募援兵。李章玉还真挺能干,招募到了 7000 人。可募兵完成后,怎么把这些士兵带回凤阳成了难题。西北军事形势瞬息万变,原来走水路北上凤阳的路线因为李自成的起义军占领荆州走不通了。没办法,只能绕道江西,先顺着鄱阳湖边绕到江西九江,再渡江到对面的黄梅县,最后返回凤阳。谁知道张献忠的部队流窜到黄梅县休整,这条路也被阻断了。李章玉只好再次更改路线,从九江向东到江西乐平,途经江西祁门到徽州府,再从徽州府一路北上,这过程真是曲折复杂。

按照明朝军规,军队变更行军路线得提前向途经的州府道台及下辖乡镇报备。李章玉写信告知徽州府婺源县统军情况,请求通行。可在战时,农民起义军常伪造信件骗取通行,这封信就引起了婺源县的高度重视。兵备道官员对信的真伪存疑,就把书信转交给了巡按御史。巡按御史也认定送信部队是乱匪,想要蒙混过关。这下徽州府如临大敌,全城戒严,还招募乡勇组成了保卫团。
可已经提前报备的李章玉的部队却毫不知情,先头部队 700 人抵达祁门县时,被当地百姓当成乱匪,全部杀害,随行的 600 匹战马也没能幸免。李章玉得知消息后,那是又震惊又恼火,向兵部上书要求严惩凶手。可兵部却选择和稀泥,让徽州府赔付战马了事。没想到,徽州府拒不认错,坚称所杀为乱贼流寇,拒绝赔马。
这事儿闹到崇祯皇帝那儿,皇帝就让兵部派人调查。调查发现,这些明军在祁门县肆意抢劫、滋扰百姓,才引发当地乡勇反抗。兵部就把责任归咎于李章玉队伍军风不正。崇祯皇帝一方面对徽州府的态度怒不可遏,另一方面又担心处理不当激起民怨,民众揭竿起义。没办法,崇祯皇帝找了徽州府官员背锅,以治民不利、误伤友军为由,将其连降三级,并要求赔付马匹。可徽州府不接受这口黑锅,当地有影响力的乡绅金生质疑马世英给李章玉安排的行军路线。马世英就向皇帝上折子道明原委,原来是因为他和驻守池州的左良玉素来不睦,所以没让李章玉借道池州。

真相大白后,马世英在折子中却把责任都推给了左良玉,徽州府官员也纷纷附和。崇祯皇帝就选择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再追究此事。
这事儿看起来是个误会,可实际上在内外交困的局势下,明朝内部的官员们不仅没能齐心协力挽救危局,反而因个人恩怨和私利,导致了一系列荒诞事件的发生。明朝本就不多的国力,也让民众对朝廷的信任逐渐丧失。
大家说,这事儿到底是谁的错?是李章玉的队伍军风不正,还是徽州府官员的误判?或者是马世英和左良玉的个人恩怨?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