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县里换了新县长,全县人民都沸腾了。我妈却只是在电视机前擦了擦眼泪,然后继续择菜,跟没事人似的。
“咋了?感动啊?”我爸嘴上这么问,眼睛却一直盯着电视不放,生怕错过新县长讲话的每一个字。
我妈没说话,只是抹了抹额头的汗。那汗珠顺着额头滑下来,汇入她脸上细密的皱纹里。她今年才五十八,脸上的皱纹却比同龄人多得多。十五年的早起风吹日晒,给她的脸上刻下了属于山里人的印记。
“那不是黄家沟的小黄吗?”邻居刘婶突然冲进来,手里还拿着一把刚从地里拔的小葱。葱根上的泥土掉在我家的水泥地上,留下几个黑点。
“啊,是啊。”我妈终于开口,声音平静得出奇。
我爸却忍不住了:“那不就是——”
“行了,”我妈打断了他,“菜马上就好,你们等着吃饭吧。”
我知道个中缘由,却装作若无其事地玩着手机。十五年的故事,在我们县城这个小地方,早已变成了一段传奇。
我家在向阳镇,是个被山环绕的小地方。镇子不大,却有着令人瞩目的山水。我妈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从来没有出过远门。她一生只做过两件让人意外的事:一是嫁给了外地来的我爸,二是坚持十五年给邻村的哑巴送饭。
那个哑巴叫黄福,住在隔壁黄家沟村。黄家沟和我们村之间隔着一条潺潺的小溪,溪上有一座木桥,据说已经有几十年历史了。每逢下大雨,那座桥就摇摇晃晃,像是随时会倒塌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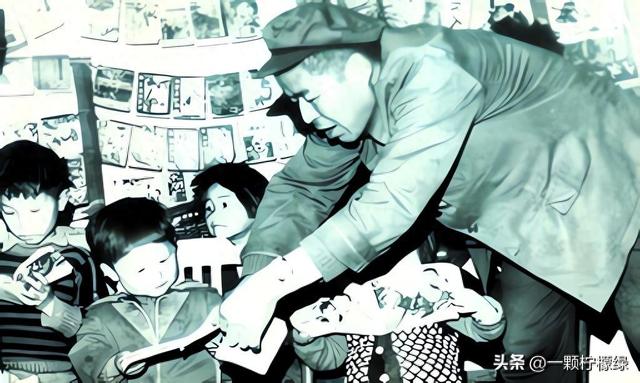
黄福从出生起就没法说话,据说是天生的喉咙有问题。他的老婆早年因病去世,留下他和儿子小黄相依为命。小黄那时候才七岁,瘦瘦小小的一个孩子,眼睛却特别有神。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2008年的夏天,一场特大暴雨把黄家沟的大坝冲垮了。水漫过村庄,许多房子倒塌,黄福家也被冲毁了大半。那天,黄福背着小黄涉水过来求救,浑身湿透,嘴唇发紫,却发不出一个完整的音节。
我妈那天恰好在家。看着浑身发抖的黄福和小黄,她二话不说就把他们领进了屋。给他们换上干衣服,煮了热汤面。我至今记得黄福那双手,粗糙得像树皮,指甲里还嵌着泥土。他吃面的样子极其狼狈,却又透着一种让人心疼的克制。
那顿饭后,我妈做了一个决定:每天给黄福送一顿饭。
“他是个哑巴,又没老婆,一个人带个孩子多不容易啊。”我妈这样解释,语气轻描淡写,好像只是决定每天多洗一件衣服那么简单。
我爸没反对,只是摸了摸有些花白的头发,叹了口气:“你做你的吧,但别太累着自己。”
从那以后,我妈的生活就多了一项固定任务:每天下午四点,带上一个铝饭盒,里面装着当天的饭菜,穿过那座摇摇晃晃的木桥,去黄家沟。
一开始,村里人议论纷纷。
“她图啥啊?”“是不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传出去多不好听。”
流言蜚语像野草一样疯长。我妈充耳不闻,依旧每天准时出门。我爸也从最初的沉默变成了坚定的支持者。

“我老婆心好,你们别乱说。”他一边喝着劣质白酒,一边对村口闲聊的几个老头说。
日子一天天过去,季节更替,年岁轮回。我妈的送饭活动成了村里的一道风景。渐渐地,人们不再议论,只是在看到我妈背着饭盒经过时,会笑着点点头。
那条通往黄家沟的小路,我妈走了无数次。夏天,她戴着草帽,汗水湿透了背心;冬天,她裹着厚棉袄,脚踩在结冰的小路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春天和秋天,她会在路边采些野菜,或者捡些板栗带给黄福和小黄。
有一次下大雨,木桥被冲垮了一半。我妈不顾家人反对,找了根长木棍,小心翼翼地趟过湍急的溪水。当她浑身湿透地回来时,我爸气得摔了碗,却又默默地给她烧了热水。
“你就这么惦记着那哑巴?”我爸问。
我妈把湿透的衣服挂在院子里的竹竿上,低着头说:“那孩子要上学,得有人照顾。”
那一刻,我看到我爸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复杂的光芒,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
黄福是个固执的人。一开始,他不愿接受我妈的好意,总是手脚笨拙地比划着拒绝。但我妈更固执,她就站在院子里,一动不动,直到黄福接过饭盒。
久而久之,黄福似乎也习惯了这份好意。每次我妈来,他就站在门口等着,一见到我妈就露出憨厚的笑容。他笑起来时,眼角的皱纹会挤在一起,像是山谷中的沟壑。
小黄从小就懂事。他总是安静地站在一旁,等我妈放下饭盒后,才说一声”谢谢阿姨”。他的声音清亮,和他那不能言语的父亲形成了鲜明对比。

我妈经常会多做些菜,有时候是红烧肉,有时候是清蒸鱼,还有时候是我最爱吃的糖醋排骨。每次我抱怨家里的好菜都给了黄福,我妈就瞪我一眼:“孩子要长身体,得多吃肉。”
我当时不理解,为什么我妈对一个不相干的人家如此上心。直到有一天,我无意中听到我妈和邻居刘婶的对话。
“我那个死去的弟弟,要是活着,也有小黄这么大了。”我妈轻声说,声音里带着我从未听过的哀伤。
我这才知道,原来我妈年轻时有个弟弟,出生时就有先天性疾病,没活过三岁。这是我妈心里的一个结,一个从未向我们提起过的伤口。
小黄很争气,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他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每次考试后,我妈总会第一时间问他考得怎么样,比问我还积极。
高考那年,小黄考了全县第一,被北京的一所名牌大学录取了。临走前,他专门来我家道别。
站在我家简陋的院子里,小黄显得有些局促不安。他穿着一件新买的衬衫,头发整齐地梳到脑后,像是要去参加什么重要场合。
“阿姨,谢谢您这么多年的照顾。”他说,声音有些哽咽。
我妈笑了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包:“拿着,上大学的路费。”
“不用了,阿姨,我——”

“拿着!”我妈难得强硬地打断他,“就当是我送你的礼物。”
小黄最终还是接过了红包。临走时,他深深地鞠了一躬,那一刻,我似乎看到了一种超越血缘的亲情。
小黄走后,我妈依然每天给黄福送饭。只是话变多了,总是叨叨絮絮地说着小黄在北京的所见所闻,虽然她自己从未去过那座城市。
“小黄昨天来信说,北京的天安门真大,站在前面觉得自己好渺小。”
“小黄说他们学校的图书馆有好几万本书,可以随便看。”
黄福从不打断她,只是专注地听着,时不时点点头,脸上带着欣慰的笑容。
有一年冬天特别冷,黄福生了场重病。医生说是肺炎,需要住院。我妈二话不说,拿出了积攒多年的老姜农家肥鸡和存折,带着黄福去了县医院。
住院期间,我妈几乎寸步不离地守在病床前。她甚至学会了用手机给小黄发信息,告诉他父亲的病情。小黄马上从北京赶了回来,看到的是我妈憔悴的面容和他虚弱的父亲。
“阿姨,您回去休息吧,我来照顾爸爸。”小黄劝道。
我妈摇摇头:“你得上学,耽误不得。我在这儿守着就行。”

那晚,医院走廊的灯特别暗,投下一道长长的影子。我妈坐在硬邦邦的椅子上,头一点一点地打着瞌睡,却始终没有躺下。隔壁病床的老人看不下去了,让出半张床给我妈。
“大姐,你这是何必呢?又不是自家人。”老人叹息道。
我妈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都是一个村的,还分什么自家不自家。”
黄福的病好了后,生活又恢复了平静。小黄毕业后在北京一家大公司工作,据说薪水很高。他时常给父亲寄钱和礼物,也没忘记我妈。每逢节日,我家都会收到来自北京的包裹,里面装着各种各样的东西:丝巾、保健品、小家电……
我妈收到这些礼物时,脸上总是带着藏不住的骄傲,好像那是她亲生儿子送的一样。
有天晚上,我问我妈:“你为啥要对黄家这么好?就因为小黄让你想起你弟弟?”
我妈正在给我爸缝补一件旧毛衣,听到我的问题,手上的动作停了下来。她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带着一丝我看不懂的情绪。
“人这一辈子啊,能帮就帮一把。”她轻声说,然后又低下头,继续手中的活计。
我知道我妈不会说更多了。在我们这个小地方,人们不习惯把情感宣之于口。爱,就是一日三餐;牵挂,就是问一句”吃了没”;感谢,就是一个点头或一声叹息。

去年夏天,黄福安详地走了。那天,整个村子的人都去了,连村口那个平时最爱说闲话的老王也来了。
黄福走得很平静,就像他生前那样,不声不响。小黄从北京赶回来,站在灵堂前,眼泪无声地流下。我妈站在一旁,给每一个来吊唁的人递上一杯热茶,脸上看不出太多表情。
只有我知道,那天晚上,我妈独自坐在院子里,对着星空哭了很久很久。第二天,她的眼睛红肿得像两个熟透的桃子,但她只说是被蚊子咬的。
葬礼后,小黄来我家道别。他说他要回北京了,但会时常回来看看。
“阿姨,这些年,谢谢您。”小黄说,声音很低。
我妈摆摆手:“别说这些客套话,路上小心点。”
小黄点点头,临走前又回头看了我妈一眼,目光复杂。
后来,我们听说小黄在北京的事业越做越大,还进了政府部门。再后来,他回到了县里,成了县里的一个小干部。村里人都夸他有出息,说他不忘本。
我妈听到这些消息,只是淡淡地笑笑,继续做她的家务。我知道她心里高兴,但她不会表现出来。这就是我妈,把最深的情感都藏在心底。
直到昨天,电视里宣布了新任县长的名字——黄小伟,也就是我们口中的”小黄”。

全县震动了。一个从黄家沟出去的孩子,居然成了县长!
我家的电话响个不停,都是来祝贺我妈的。毕竟,在所有人眼里,小黄能有今天,我妈功不可没。
我爸兴奋地在院子里来回踱步,一边抽烟一边说:“早知道当年就多送几顿饭了,说不定现在就能当市长了!”
我妈白了他一眼,没说话。
电视上,小黄正在发表就职演讲。他西装革履,举止得体,哪还有当年那个瘦小男孩的影子?
“……我要特别感谢一个人,一个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予我无私帮助的人。她不是我的亲人,却胜似亲人……”
我妈突然站起来,关掉了电视。
“干嘛呢?正听着呢!”我爸不满地抗议。
“有啥好听的,不就是客套话嘛。”我妈转身进了厨房,“饭快好了,来吃饭吧。”
今天一大早,我妈就起床了。她换上了那件深蓝色的外套,那是她最好的一件衣服,只有逢年过节才会穿。

“这么早起来干嘛?”我爸揉着惺忪的眼睛问。
“去黄家沟。”我妈简短地回答。
“去那干嘛?黄福都不在了。”
我妈系好鞋带,站起身来:“去看看他的坟,顺便把院子打扫一下。小黄忙,估计没时间。”
说完,她拿起扫帚和铲子,往门外走去。阳光透过门缝洒进来,在地面上形成一道金色的线条。我妈的背影在阳光中显得格外单薄,却又挺拔如松。
这就是我妈,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做了十五年看似平凡的小事,却在无形中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也可能改变了一个县的未来。
她不求回报,不图名利,只是遵循着内心最朴素的善良。就像她曾经对我说的:“人活这一辈子,能帮就帮一把。”
这句话,成了我这一生最宝贵的财富。
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像我妈这样的人或许并不起眼,但正是他们,用最平凡的行动,诠释了最伟大的爱。
至于那个哑巴的儿子成了县长这件事,我妈似乎并不太在意。对她来说,无论小黄是县长还是普通人,她都会一如既往地关心他,就像过去的十五年一样。
因为在我妈心里,小黄永远是那个站在门口,轻声说着”谢谢阿姨”的瘦小男孩。
而这,大概就是爱的本质吧——不求回报,不计得失,只是单纯地给予和守护。
电视上,新县长的就职典礼还在继续。我妈却已经走在去黄家沟的路上,阳光洒在她的身上,留下一道长长的影子。那影子随着她的脚步,缓缓地延伸,像是一段永不结束的故事,继续在这片土地上书写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