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华夏素以礼仪之邦闻名,重礼乐、重教化、重规矩,纵使放到王朝更替这样的大事上面也是一样得有规矩,讲究一个“合法性”,满足了“合法性”,也就意味着“得国正”。近代史学家孟森在《明史演义》中提出“三代以后,得国最正者,惟汉与明”。这一论断引发了广泛讨论,至今未休。
汉高帝刘邦和明太祖朱元璋建立的王朝,为何能被孟老称为“最正”?其背后既有对“吊民伐罪”之传统的继承,也包含了对权力来源合法性的深刻思考。本文将从历史背景和伦理基础两个维度解析汉、明两朝得国之“正”的独特性,并对比其它王朝的合法性困境,将古代“合法性”问题展开说一说。

明太祖朱元璋
一、“得国正”的核心标准:布衣起事与为民除暴1. 出身微贱,无前朝荫庇
孟老提的第一个标准是“匹夫起事,无凭借威柄之嫌”,汉高帝刘邦虽说曾任秦朝的亭长,但其家族传至其父手里已然属于编户农民,而且亭长也算不上“官”,充其量只是不入流的“吏”。他能建立汉朝主要凭借的是他的个人能力和时代际遇,而非世族背景或前朝权位。正所谓“君既起布衣,其臣亦多亡命无赖之徒”,可以说他一手打破了持续千年的世侯世卿之旧格局。
明太祖朱元璋更是“开局一个碗”的极端案例,父母早亡、出家为僧、化缘求生,其崛起完全脱离体制框架,正所谓“崛起布衣,奄奠海宇,西汉以后所未有也”。相较之下,隋文帝杨坚、唐高祖李渊和宋太祖赵匡胤均为前朝权贵,皆依托既有权力网络上位,有点儿“吃老板的饭,砸老板的锅”的意思,确实不满足这第一条标准。

汉高帝刘邦
2. 为民除暴,非预谋篡位
孟老提的第二个标准是“为民除暴,无预窥神器之意”,汉高帝刘邦聚众起兵的根源在于秦朝末年的“天下苦秦久矣”,“欲为乱者十家而七”,其最初的目标仅为带着兄弟们在乱世中寻得一线生机,顺带响应天下熙攘的反秦之势,绝没有想到自己要去谋夺皇帝宝座。
明太祖朱元璋加入红巾军时仅是因为自己生活无依,恰好幼时小伙伴汤和来邀,便投军求生,自成为义军大帅,扫灭江南群雄后,才有了一统天喜啊的格局。他俩的这种“被动逐鹿”与曹丕、司马炎等权臣“预窥神器”形成鲜明对比,曹丕之父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司马炎之父司马昭又是路人皆知,其权力更迭的本质是集团内部分解。

朱元璋加入了以反元为宗旨的红巾军
二、汉明两朝得国之“正”的伦理实践1、汉朝:终结贵族格局,开启布衣时代
汉高帝刘邦的胜利不仅是军事层面的成功,更是zheng治模式的革命,他比秦朝更为彻底地打破了夏商周三朝以来的“世卿世禄制”,以白马之盟的温和手段确立“非刘不王、非功不侯”的上层建筑格局,将统治基础从以血缘关系为依托的贵族阶层转向军功阶层,其中多为底层平民或小地主、小官僚出身,比如屠狗之辈樊哙和贩缯之徒灌婴等。
这种变革使社会阶层的流动成为可能,换作前代,谁能想到一个骑奴能够跃为赫赫有名的大将军。从最初的约法三章到开放秦朝皇家园林给百姓耕种、再到以身作则、注重节俭、轻徭薄赋,并将秦朝的乡级“三老”制拔高至县级,这一桩桩、一件件,汇总到一起就是“与民休息”,由此将王朝合法性与改善民生直接挂钩。奠定了汉朝盛世的基础。

完成阶层跨越的樊哙
2、明朝:驱逐异族统治,重构华夏正统
明太祖朱元璋的“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同样不只是单纯的武功,在“华夷之辨”的大环境下,这称得上是华夏文明的复兴。他在北伐诏书在提到自古只有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激励汉家儿郎“雪中国之耻”,满满的都是血性和他对华夏正统的宣示,可谓气势磅礴。回顾前代,有以华夏同化夷狄者,没有像朱元璋这样在神州沉沦于夷狄之际而驱逐夷狄的。
军事目标完成后,朱元璋开始逐步落实文化复兴,他令人编撰《大明集礼》,旨在尽快摒除元朝文化的影响和冲击,恢复汉家礼仪文化,并采取了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比如废除蒙古文化中的胡跪,恢复汉家的即顿首和稽首之礼;禁止使用胡语,制定《洪武正韵》;循唐制衣冠而制定大明冠服制度。用行政的力量推动文化的复兴,朱元璋成功革除了蒙元的阴影,重新建构了华夏正统。

朱元璋派徐达北伐
三、对比视域下的“不正”王朝:合法性危机之源1、权臣篡位:伦理背叛的先天缺陷
新莽篡汉、曹魏代汉、司马代魏、北齐代魏、杨坚篡周、赵匡胤黄袍加身,均属权臣利用体制内地位谋夺皇权。此类王朝虽可通过“禅让”仪式粉饰合法性,但其权力来源始终带有“弑主”原罪。如司马昭当街弑君,赵匡胤欺后周孤儿寡母,均被后世视为道德污点。先天不足,那就后天来补。
王莽、司马炎和赵匡胤不都陷入了合法性的焦虑之中吗?王莽为了彰显自己的天命所归,选择托古改制,搅得天下大乱;司马炎为巩固统治而分封家族成员,却因此引发了导致永嘉南渡的八王之乱,半壁江山落入胡骑之手。赵匡胤为了防范风险,将“重文抑武”搞成了极端,使得宋朝军事孱弱不堪。这些后天路数的扭曲,皆可追溯至权力来源的先天不足。

陈桥驿之变—赵匡胤黄袍加身
2、异族征服:文明冲突下的合法性争议
鲜卑、契丹、女真、蒙古以武力入主中原,其统治者始终面临“夷夏之辨”的质疑。拓跋鲜卑改革,积极推广汉家礼制,最终在文化的交融过程中湮没于历史;契丹主耶律德光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汴京,改国号为辽,旨在宣示合法,结果不到1年的时间就仓皇北撤,抱憾而终。完颜女真为削弱中原汉人的抵抗,一方面将汉人移民至东北辽东等地,视他们为奴隶,一方面推崇儒家文化。
同时,女真人还循五德之说将自身定义为承继宋之火德的土德(开始说金德,后改之),眼见同化现象愈发严重,其上层统治者又感危机,持续强制治下汉人接受女真礼俗,让汉人搞什么“薙发左衽”;蒙元同样如此,在推崇儒学的同时致力于将汉人边缘化。相比之下,汉、明两大王朝均以“华夏守护者”自居,其合法性建立在文明共同体认同之上。

南迁改革的北魏孝文帝
四、合法性标准的历史功能与局限1、积极功能:秩序稳定
关于王朝合法性,除了孟老提出的两条外,历史上还存有另外的标准考量,比如天命观(比如周武王以德配天)、血统论(比如李渊自称西凉太祖李暠后裔)、制度传承(比如王莽复周礼)。这些标准的本质是统治集团的话语建构,例如朱棣在靖难之变后修改史书,将自己塑造为朱元璋属意的接班人。
统治者通过这些抽象的概念,使民众自愿服从权力,便于稳定社会秩序,降低统治成本。不去讲合法性,但凡有点什么差错,都得给人上纲上线,弄个不好就成了被围殴的对象,比如袁术。讲合法性,除上述好处外,还能构建集体认同,比如元朝和四大汗国之争,元朝就通过讲合法性来凝聚汉地精英,清朝同样如此,以“大一统”来叙事整合多民族帝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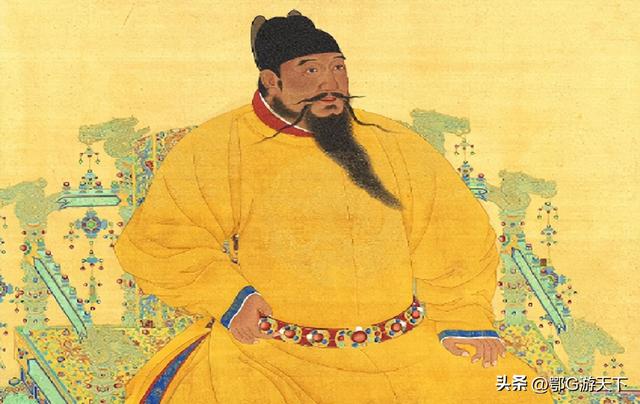
存在合法性焦虑的朱棣
2、历史局限:内在矛盾
展开来看,合法性标准落到实处的时候往往就是依赖“成王败寇”的终极逻辑,陈胜明明喊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却又不得不制造“鱼腹丹书”。黄巢、李自成失败后被斥为“流寇”,成功则可自诩“替天行道”。这种逻辑使合法性沦为对既成事实的事后解释,而非客观评判标准。
另外,那些宣称爱民如子、以民为水的王朝,多数时期仍维持压迫状态。李自成席卷中原时,百姓甚至高喊,“闯王来了不纳粮”,明显揭示了合法性叙事的脆弱性,而且当不同标准发生冲突时,合法性体系即陷入混乱,最终仍以实力定胜负,比如蒙古灭宋,符合武力征服,但违背华夷之辨。

受到欢迎的李自成
结语:正当性的双重维度与当代启示汉、明两朝得国之“正”,既体现为程序正义(非篡夺、非异族),更蕴含实质正义(解民倒悬、文明复兴)。这种双重正当性,使其成为华夏历史上罕见的兼具“ge命性”与“建设性”的王朝。
在当代语境下,这一历史命题的启示在于:国家的生命力不仅依赖武力或权谋,更需扎根于对文明价值的捍卫与对民本诉求的回应。正如朱元璋在《谕中原檄》中所言:“立纲陈纪,救济斯民”,或许这才是“得国正者”超越时代的精神内核。
参考文献:
《史记》
《中国通史》
《明史讲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