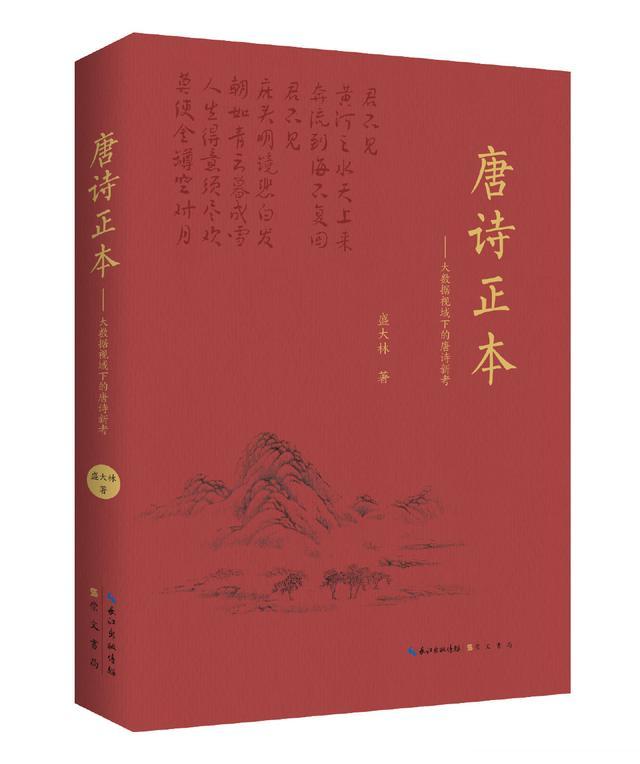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床头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云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天生吾桐为俊才,千金散尽还复来。
烹羊宰牛宜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岑夫子,丹丘生,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
钟鼎玉帛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
古来圣贤皆死尽,惟有饮者留其名。
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
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将进酒》篇幅较长,异文太多,但有些异文无关紧要,比如“君不见”“又不见”、“钟鼓馔玉”“钟鼎玉帛”、“不足贵”“岂足贵”、“不用醒”“不复醒”“不长醒”“不愿醒”、“圣贤”“贤圣”“贤达”之类,姑且略过。
(一) 关于“床头”和“高堂”
“床头”仅见于3个敦煌写本,其他所有的版本均为“高堂”。也就是说,在1900年敦煌的那些卷子重见天日之前,“高堂明镜悲白发”就不存在异文。但当“床头”出现之后,两相对比,不得不说,“床头”应该是正版,因为“床头明镜”比“高堂明镜”更妥帖。三个人不约而同地写为“床头”,说明当时流传的版本就是这样。而且“明镜”本来就应该安在床头,至少是在卧室之内。早上起来,女人要梳妆打扮,“对镜贴花黄”,男人也要照照镜子,梳头理须,拾掇利索,方才出门。就风水学而论,中式厅堂需严格对称,若放一把镜子,只能置于上方正中,即正对着门的位置,但那是“天地君亲师”的供位。若把镜子置于正中,等于让人一进门就照镜子;抑或厅堂两侧各置一镜,相互对照,这都是不可相像的。虽然公堂常挂“明镜高悬”之匾,但此所谓“明镜”只是比喻,而且那是衙门“公堂”,而不是自家“高堂”。

具体到本诗,前两句的意思就是感叹:岁月匆匆,人生短暂,犹如黄河之水,奔流咆哮而去,不过朝暮之间,黑发就成白雪,临镜而生悲叹,既然如此这般,何不及时行乐?这两句是为后面的“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作铺垫。试想一下:对着镜子悲叹,是在“高堂”合适,还是应在内间?
的确,“床头”二字没有“高堂”那么响亮,甚至不太高雅。这可能就是后人把“床头”改为“高堂”的原因。李白《静夜思》首句中的“床前”有作“窗前”,可能也有这个方面的原因。只要视觉的美观,不管诗意之内涵,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王之涣《凉州词》首句“黄沙直上白云间”被改为“黄河远上白云间”,很多人就因为“壮美”而支持“黄河远上”,殊不知所谓“壮美”与全诗的基调和旨归格格不入(详见本书第215页《王之涣<凉州词>通考通辨》)。
邱燮友在《新译唐诗三百首》中说,本诗中的“高堂”指的是“父母长一辈的人”,意思是“上一辈的人因为从镜子里看到白发而悲伤”。这种诠释不仅非常牵强,而且有对父母长辈不敬之嫌。
四部丛刊明翻宋本《河岳英灵集》中《将进酒》标注了3处异文,宋蜀本《李太白文集》中《将进酒》标注的异文更是多达8处,但都未提“床头”。后世其他版本,也都没有标注,这意味着这些文献的编者都没有见过“床头”,也就是说《将进酒》中的“床头”早在唐代可能就已经失传了。
(本文节选自拙著《唐诗正本——大数据视域下的唐诗新考》中的《李白<将进酒>的异读和异议辨析》一文,全文2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