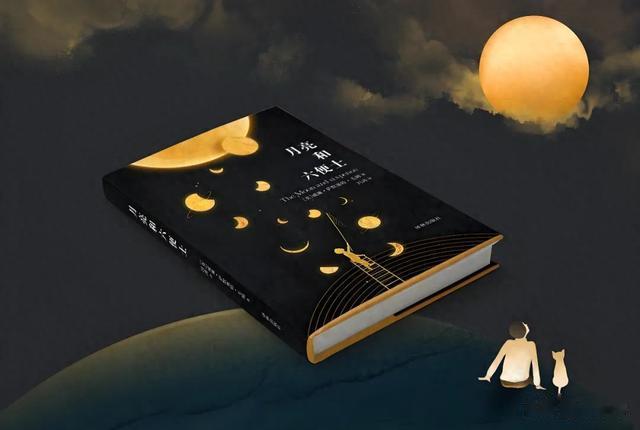
如果有人问你:你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吗?
可能你会犹豫。毕竟,从小到大,我们总被教育要“合群”——上学时选热门的专业,工作时找稳定的岗位,到了年龄就结婚生子。
人生像被设定好的程序,每一步都有人告诉你“该怎么做”。
可偏偏有些人,他们放弃体面的工作、优渥的生活,甚至抛家舍业,只为追寻旁人眼中虚无缥缈的东西。
比如《月亮与六便士》里的斯特里克兰德,一个证券经纪人,突然抛下妻子和孩子,跑到巴黎学画画,最后在塔希提岛去世。
有人骂他自私,有人说他疯了,但毛姆却说:“他像被魔鬼附了体。”
这种“魔鬼”,或许就是特立独行者的共性:当全世界都在教他们“应该怎么活”时,他们却清醒地知道自己“必须怎么活”。
哪怕代价是众叛亲离,是颠沛流离,是穷困潦倒。
活得特立独行的人,不是天生反骨,而是早早看清了一件事:人生只有一种成功,就是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一、放弃安稳
斯特里克兰德的前半生,活成了世俗的“模板”。
他工作体面,家庭美满,住在伦敦的富人区,周末和太太参加社交晚宴。
可某天,他突然留下一张字条,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他说:“我必须画画,就像溺水的人必须挣扎。”
外人觉得他疯了,但毛姆却说:“他的灵魂中仿佛有什么东西在生长,像肿瘤一样压迫着他。”
这种压迫感就像一种“警报声”,提醒他不能再麻木地活在别人的期待里。
现实中,很多人也听过这种“警报声”。
日本作家村上春树,30岁前经营着一家爵士酒吧。虽然收入不错,但他总觉得“心里缺了一块”。
直到某天看比赛时,他突然想写小说。就是从那天,他开始写作。
朋友劝他:“写小说能养活自己吗?”他却说:“就算失败,我也想知道自己倒在离终点多远的地方。”
特立独行的人,不是不爱安稳,而是无法忍受灵魂的饥饿。
就像斯特里克兰德说的,我告诉你,我必须画画,我身不由己。
一个人掉进水里,游泳游得好不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必须挣扎,不然就会被淹死。
二、无视评价
斯特里克兰德在巴黎学画时,穷得吃不起饭,经常靠朋友接济度日。
别人问他:“你画这些没人看得懂的东西,图什么?”
他回答:“我画画不是为了被理解,而是为了理解自己。”
现实中,许多人活在他人的“坐标系”里:用工资、职位、房子来衡量人生价值。
但也有人早已建立了自己的“坐标系”。
外界的评价像一阵风,吹过就散了;而内心的声音,却是扎根在土壤里的树。
斯特里克兰德在塔希提岛染上麻风病,双目失明,仍坚持在墙上作画。
临死前,他让妻子烧掉了所有作品。
有人问:“你不在乎自己的画被认可吗?”他说:“我画完了,它们对我没用了。”
三、敢做取舍
有人说斯特里克兰德冷血,但就像毛姆说的,他像一个人虔诚的朝圣者,每一步都走向自己的圣地。
特立独行的人,不是不懂权衡利弊,而是算清了人生的“总账”,有些东西可以丢,但丢了自我,人生就成了一笔烂账。
斯特里克兰德烧掉了画,却留下了对艺术的极致追求。
人这一生,最怕的不是失去,而是从没为自己活过。
就像书中的斯特里克兰德,哪怕最后死在破木屋里,但他没有遗憾了,因为他终于完成了想做的事。

四、活得“自私”
斯特里克兰德的故事,总被贴上“自私”的标签。但是“难道为自己而活,就是自私吗?”
作家李娟曾经一边经营小卖部,一边放羊,一边写作。有人说她:“不务正业,迟早饿死。”
她却说:“我不是在放羊,我是在养活我的精神。”
如今,她的书感动了无数人。
真正的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不想做什么时,有勇气说“不”。
斯特里克兰德放弃了丈夫、父亲的身份,看似冷酷,却守住了艺术家的纯粹。
我最喜欢的一部电影《海上钢琴师》,1900宁愿死在船上,也不愿踏入陆地。
他说:“陆地对我来说是一艘太大的船,是太美的女人,是太长的航程。”这种选择,何尝不是一种清醒?
做自己最想做的事,生活在自己喜爱的环境里,这难道是糟蹋自己吗?
斯特里克兰德们的故事,从来不是教你抛家弃子、离经叛道,而是告诉你:人生的方向盘,必须握在自己手里。
有人活在父母的期待里,有人困在伴侣的梦想里,有人卡在社会的标准里,而特立独行的人,只活在自己的信仰里。
他们像旷野上的树,不依傍他物,只管向着天空生长。
如果你也曾被内心的“警报声”惊醒,不用害怕。
这世上总有人告诉你“该走哪条路”,但只有你知道“哪条路能让灵魂歌唱”。
记住,人生的答案,从来不在别人的嘴里,而在你放下六便士、抬头看月亮的那一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