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伯涛的双眼,直直地看着房顶,看着横的檩条、竖的椽子间,密密麻麻呈“人”字形而规规矩矩地挤在一起的一根根木条,这里的建筑模式大体上和老家的相同,只是椽子内填补的这些木条,看上去要比老家用细竹竿编织而成的簿强了不少,看上去也结实得多,更能让人幻发出一些意想不到的图案来。在杨伯涛的眼中,那就是冲锋的箭头,是构筑的固工,是搏杀的山头,是一具具死亡的尸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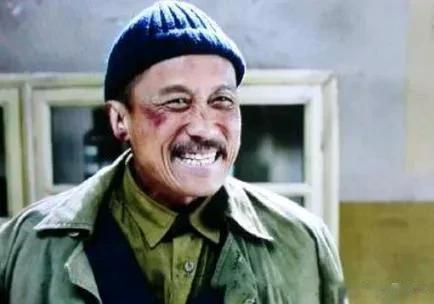
杨伯涛没有再想下去,他猛然觉得,他已经远离了战场,远离了战争,远离了用鲜血编织的罪恶的花环。他内心里已经极度地讨厌战争,在整个的发言中,他一直表着自己的态度,吴绍周说得好,我赞成;王元直说得好,我赞成;林伟俦说得好,我赞成;邹玉亭说得好,我赞成……最后,他还一直说,大伙说得都好,我都赞成。
杨伯涛的内心里,却如油锅般翻滚着,他觉得,讨论战场上的成败得失,对于他而言,已经没有了任何好处或者坏处,因为他已经不可能再回到他戎马半生为之奋斗的战场,他的人生归宿,或许是共产党赏给自己的一颗子弹,或许是终老于监牢之中。当然,这些日子,杨伯涛一直在做着同一个梦,那就是和妻子罗启芝,回家经营母亲撇下的土地,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抚养儿孙,终老于祖屋,梦醒时分,他已经是泪流满面,他知道,这个梦想,对于他而言,是何等的奢望。
睡在1号床的王伟杰还没有进入被窝,他往火炉里添了一些煤核,又到门口看了看烟囱,这才又坐了下来,继续誉写他的学习记录。杨伯涛突然感到,这个王伟杰有些神秘,更有几分可怜,如果以他的少将军衔和政工室主任的职务论之,他应当是一个不错的知识分子,可从这两天的表现来看,他的文化水平并不太高,文字功力也不太深。他甚至不能听出大才子侯吉珲对他的调侃,不能听出宋瑞珂的话中有话,不能完整地理解众人所说的话中含义,可他却在努力地做着,虽然有些装腔作势,有些夜郎自大,有些自以为是,甚至是把自己当成了解放军的干部。
杨伯涛为自己的想法,感觉到几分好笑,他轻轻地闭上自己的眼睛,准备睡觉了,也准备再一次进入他相同的梦境,看一眼妻子是不是在整理那棵枇杷树,是不是在轻轻抚摸蜜橘树上的果子,是不是轻轻横起那根长长的晾衣秆,为她的丈夫晾晒起遮挡风雨的老蓑衣。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睡在最里面的邹玉亭却突然猛地一下把被子踢到了地上,嘴里不停地说着:“她没藏钱,她没藏钱,钱,都被别人骗去了,宝贝,也被别人骗去了,她没藏钱,给她们点吃的吧……”
王伟杰急忙放下手中的笔,快步走了过去,给赤裸着身子的邹玉亭盖上了被子,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了声:“老邹,睡吧,睡吧,新政府,不会让他们母子挨饿的,不会的,不会的。”王伟杰说着话,慢慢地往门口起来,杨伯涛猛然发现,那张年轻的面孔,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苍老了许多,也失去了一层一层的光环。

王伟杰以极轻的声音,叹了一口气,看了看火炉,封上了盖子,合上了他的会议记录本,又曲起身子,做贼般地往里面看了看早已打起呼噜的男人们,这才轻轻地伏下身子,在灰斗里拨弄了几下,极其熟练地捡拾起几只烟屁股来,迅速地剥开了,集中倒在手中已经折成一道槽的一张废纸条上,又快速而熟练地卷了几下,一个标准的大烟炮便成了。王伟杰看了看自己手中的大烟炮,苦笑一声,又回头看了看房间内已经睡熟了的男人们,这才又重新揭开火炉上的盖子,引着了手中的大烟炮,猛地吸上一口,狠狠地吞咽着,如同要把自己和这个世界吞咽掉一般。

杨伯涛僵直地躺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他觉得自己的半个身子已经麻木了,他的右臂也隐隐生疼,可是他不敢也不愿意翻一下身子,调整一下睡姿,他不忍心拆穿一个男人的秘密,更不忍心触动他人的隐痛,他内心再一次翻滚起来,为了自己面前这个勉强支撑起来的虚伪肢体,和这架虚伪肢体之下真实的灵魂。王伟杰,到底是一个幻影,还是一个真实的存在,杨伯涛感觉到很迷茫,如同自己的梦境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