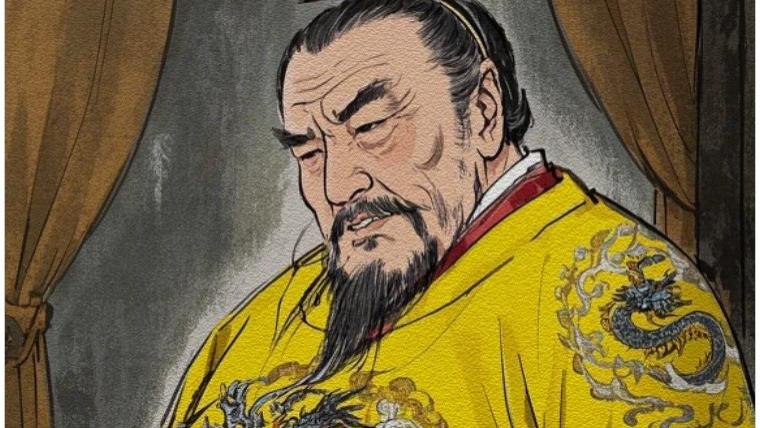本文参考历史资料结合个人观点进行撰写,文末已标注相关文献来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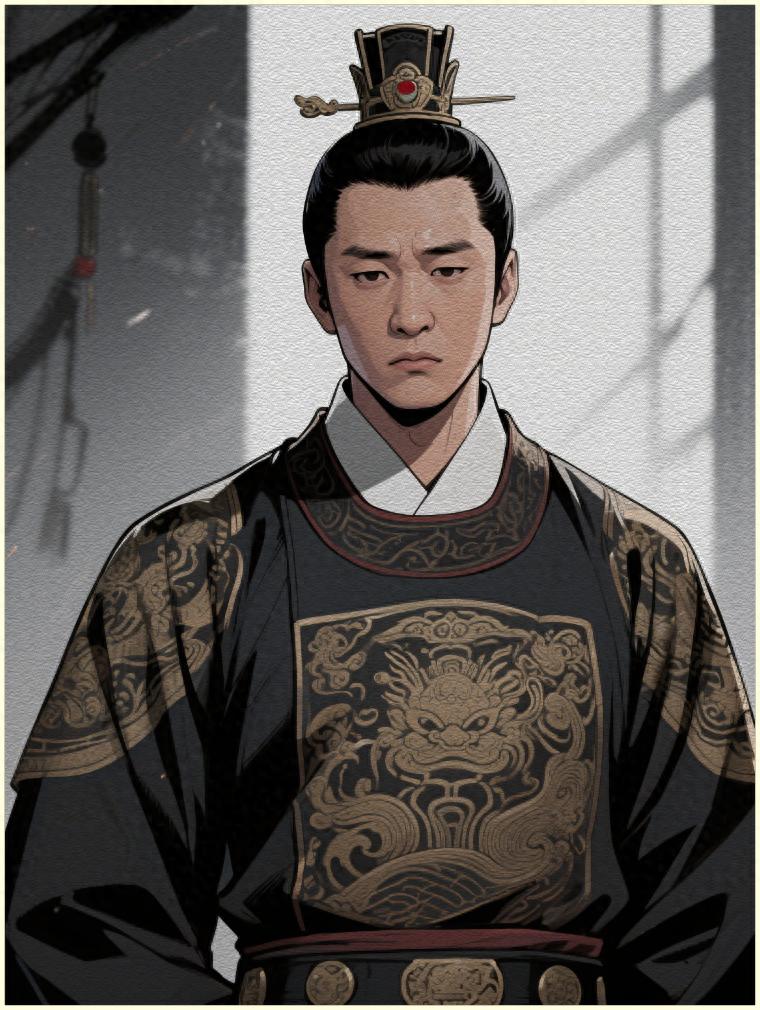
(优柔寡断 后梁末帝 朱友贞)
刘鄩死了,朱友谦也投降了,忠武镇,河中镇也丢了,朱友贞干了一堆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儿,后梁王朝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时间到龙德元年,又有大事发生,那就是河北三镇之一的成德镇兵变了。
成德镇的节度使,原本是王镕,这个王镕,夹在这么个频繁交战的地方,反复横跳,一会依附朱梁,一会又依附河东李氏,当然后来王镕看出来了,后梁真是要凉了,所以他最终决定,还是要依附李存勖。
王镕这个人,首先说他不具有成为一代枭雄的气质,无论是在地缘形势上决定了他必须在后梁和河东两个大势力中左右斡旋,还是说他本人总是想着要依附大佬,找个靠山,都说明他这个人,心智不坚定。
其次,王镕的性格,有点过于软弱了,我们知道薛居正的《旧五代史》和欧阳修的《新五代史》,虽然都是记叙五代十国时期的史料,但是这两本书出入很大,有时候记录的是同一件事,但是时间,人物,结果,动机等等,都有很大不同,甚至是自相矛盾,但是有意思的是,新旧五代史对于王镕的评价,却是出奇的一致,那就是说他“仁而无武”,就是说他人性还行,人品还可以,算上不什么特别坏的军阀,但是他能力不行,水平不到位。
最后,除了没能力之外,王镕小毛病也不少,第一是他宴安鸩毒,极好享乐,每天就是吃喝玩乐造,一点正事儿也没有。
第二是他牖中窥日,目光短浅,拥有成德镇这么一块地方他就满足了,从来没考虑过对外扩张和可持续发展。
第三是他垂拱而治,政怠宦成,他本人比较懒惰,政务不处理,还重用宦官,因此官僚体系长期处于混乱状态。

(志得意满 成德军阀 王镕)
天下之势不盛则衰,天下之治不进则退。
这是五代十国啊大兄弟,你只是个割据军阀,别说汉唐那种一统的朝代了,你就连东晋南宋那种偏安一隅的小朝廷你都算不上,你怎么能这么松弛,这么悠闲,这么躺平呢?
在乱世中毫无警觉,不懂进取的王镕,很快死于一个叫做张文礼的部将发动的兵变。
张文礼杀掉王镕,消除了王镕的势力之后,他侵占了成德,成为了新一代军阀。
张文礼,河北人,最开始是幽州军阀刘仁恭刘守光的部下,他这个人,天生凶狠,性格奸诈,而且不甘于人下,可以说很有野心,久怀异志。
他在刘氏父子手下的时候,就发动过一场兵变,想要取刘氏父子而代之,要占据幽州,但是因为准备不足,失败了。
那既然兵变失败,刘氏父子手下肯定是混不下去了,所以张文礼收拾行李,很快投奔了成德的王镕。
您别看张文礼蛮横无德,但是他还很会包装自己,到了王镕帐下之后,他时常和王镕吹嘘自己有大将之才,说什么韩信不如自己,白起不如自己,孙武不如自己,吴起也不如自己,反正就是遍翻史书,就他张文礼最牛。
你要稍微吹点牛,你说在这乱世之际,我张文礼谁都不惧,谁都不怕,那或许还有点可信度,但是你非要和韩信之流碰瓷,你说谁能相信呐?
你有韩信十分之一,至于这么多年还混成这样么?
可是您别说,王镕就相信了,王镕一听好家伙,这不是神级武将,SSR级别的?所以王镕对张文礼非常欣赏,直接就委以重用。
可是说实在的,张文礼没有什么文化,也没有什么谋略,真刀真枪的打仗,他也不行,他唯一的长处,就是擅长蛊惑别人,他在王镕面前,极力包装自己,把自己抬高成了一流名将,而在将士们中,他也没闲着他这张嘴,整天是东家长来西家短,级别比他低的武将,他极力打压,说他们啥也不是,水平不如自己,而级别比他高的武将,他就极力抹黑,说他上边的这些人,都是酒囊饭袋,都不如自己。

(狼子野心 镇州防城使 张文礼)
张文礼整天抬高自己,编排别人,其实这一招很卑劣,但是您别说,挺管用的,他这么一顿操作下来,很快就在军中树立了极高的威望,甚至于说是拉拢到一大批为他效命的人,吸纳了很多的党羽,所以后来等到时机成熟了,张文礼立刻悍然兵变,杀掉了王镕,自己做上了成德军阀。
不知道张文礼的这个名字,是谁给他起的,实在是名不符实,他不应该叫张文礼,而应该叫做张无礼,或者张无德。
因为王镕当时事河东,是跟着李存勖混的,张文礼拿下成德之后,他也不想要和李存勖撕破脸,也上表请求李存勖的册封和认可。
李存勖当然不喜欢张文礼这种悖主弑君,以下犯上的小人,如果册封他,认可他,那就代表了自己对这种行为的准许和漠视,这样影响很不好。
李存勖的立身之本是什么?不是他父亲李克用给他打下的基业,而是他们李氏一直在强调的“复兴唐室”的旗号,这是一种忠义伦理叙事,而张文礼杀掉王镕自立,这是什么行为?这是不仁不义,不忠不孝,这和李存勖的政治叙事是截然相反的,有冲突。
你李存勖如果承认了张文礼的篡逆,会不会引起其他附庸藩镇,甚至是河东臣公们的效仿?
你纵容张文礼的兵变,那么兵变有没有可能,某天也会落到你李存勖头上?
所以,李存勖看到张文礼的使者来到的时候,他的态度是“姑示含容”,就是很不痛快,很不乐意,但是最后李存勖还是“乃可其请”,还是选择了认可和接纳张文礼。
无他,只因为成德镇是河朔三镇之一,这个地方不能丢,非常重要,张文礼这是来投奔自己了,自己还有个选择回旋的余地,这要是奔着朱友贞去了,这还得了?
对李存勖来说,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他必须在传统现实与政治理想中找到平衡。
李存勖要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儿,有时候他不得不背离自己的人格。

(欲取天下 河东霸主 李存勖)
只是,李存勖做足了思想斗争,准备真心实意的接纳张文礼,可谁知道这个张文礼,他不老实,他投奔李存勖只是虚晃一枪,只是暂时的外交策略,实际上他表面上臣服李存勖,可实际上他和后梁也暗自勾结,别说后梁了,张文礼结盟的书信都送到辽朝去了,他和契丹人竟然也保持着十分隐秘的来往。
我们先说后梁方面,张文礼的结盟密信送到的时候,宰相敬翔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曙后孤星,千载难逢的机会,敬翔立刻建议,朝廷应该出兵帮助张文礼,是真心帮助张文礼也好,还是借助他的力量,把他当做傀儡也好,反正这是趁机收复河北的的最好时机了。
事实真的是如此吗?其实也不一定,神机妙算的诸葛亮也有打败仗的时候呢,战场上的情况变化太多,人会变,事情会变,局势会变,敬翔也不能说自己的这个思路一定就是对的。
只是,站在当时来考量,河北几乎沦陷,战场上接连失利,损兵败卒,就这种情况下去,对后梁极为不利,只能是慢性死亡,所以在这个时候,宁愿犯错,也不能什么都不做,这个时候,那就必须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绝不能再这么混着了。
因为,在凸显僵持或者是颓败的战争中,不作为带来的时间损耗,那本身就是最大的风险。
当局者迷嘛,朱友贞是当事人,他在局中,他往往就没有大局观,也开不了上帝视角,所以他意识不到,在常规的战争维度中,后梁已经处于很大的劣势,在这种劣势下,也只有通过敬翔的这种非常规的战略手段,才能重构战场的格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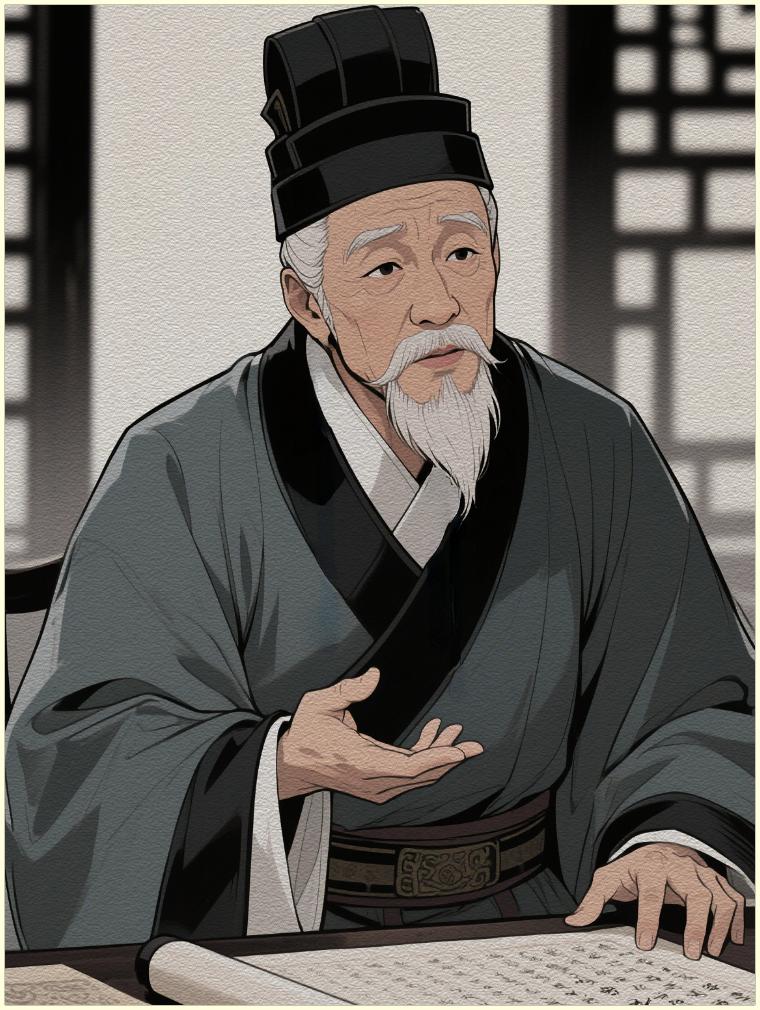
(忠心辅国 后梁宰相 敬翔)
上次没听敬翔的,朱友贞非去祭天祭祖,结果就吃亏了,所以这次敬翔把这个建议一拿出来,朱友贞很认可,赶紧就着手要派兵支援张文礼。
通常没有意外的话,意外就发生了。
一个已经千疮百孔,风雨飘摇的政权,就好像一个固定的模板一样。
一定存在一个趑趄嗫嚅的君王,比如朱友贞,也一定会出现想要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忠臣,比如敬翔。
那君王和忠臣有了,自然也会衍生出奸佞之臣,忠臣是明堂立柱投下的影子,用道德铁律浇筑了支撑穹顶的骨架,而奸臣则是藻井缝隙渗下的雨露,以人性弱点滋养着金漆剥落后的朽木,后梁的这个奸臣,不是别人,正是当年帮助朱友贞即位的驸马,赵岩。
阅读历史时,我们对奸佞贼子恨之入骨,他们对他们不屑,因为他们通常不忠诚,没有品节,而且基本上都很自私,只顾自己的个人利益而践踏家国兴亡,我们也很容易把他们忽略掉,对他们的评价往往两个字就概括了,那就是——坏人。
可是,当我们走进这个坏人的内心世界时,我们才会发现,像赵岩这样的人,必然存在,也一定存在,而且他绝不止坏人,这么简单...
参考资料:
《唐书·卷六十二》、《新五代史·卷三十九》
《旧五代史·梁末帝纪》、《五代会要·卷二》
吴树航.唐末五代河北三镇割据的衰亡.河北大学,2015
张明.唐五代牙兵与亲军关系再认识——兼论晚唐五代的治军理念.唐史论丛,2023
王美华.皇帝祭天礼与五代十国的正统意识.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