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第十一世的王:姒不降
第一段:王位怎么来的?
老丘城头,飘着白幡。十九岁的姒不降,跪在父亲灵前,听着巫师,轻轻地敲响青铜铃铛。他爹姒泄,在位十六载,将东夷西羌治理得井井有条,不过却在壮年之时,突然病逝。
这时候的夏王朝,刚历经了太康失国的动荡,恰似暴雨过后的茅草屋那样,看着颇为稳固;不过实际上,其根基却在摇晃。依照祖制,王位本应传给嫡长子,可在朝堂之上,竟然有人嘀嘀咕咕道:“不降太年轻,并且或许难以压制住九夷。”
紧要关头,担任三朝老臣的豕韦彭伯,缓缓地用手扶着那根象牙拐杖,慢慢地站了起来。“当年禹王开凿龙门的时候,才仅仅二十岁呢!”这句话非常有分量,使得反对派立刻就安静了下来。他们竟然不自觉地缩了缩脖子,脸上浮现出了些许不安以及慌张的表情。
加冕的那天,不降身穿着染为黑色的麻布祭服,稳稳地、高高地举起传承至第十一代的青铜钺,缓缓地朝向祭坛走去。九支牛角号同时吹响,那声音异常洪亮。他注视着台下黑压压的诸侯,忽然想起,父亲临终之时紧紧握住他的手说道:“千万不能让祖宗的基业在我们手中衰败。”
第二段:治国五十九年
头六年过得像是在走独木桥一般。东南的九苑部落,趁着新君继位之际,抢了三个盐池,而且还将夏朝使臣绑在旗杆上予以羞辱。那年春天,柳絮飘飞之时,不降居然亲自率领着三百乘战车踏上了出征之路。
将士们举着那画有太阳纹的皮鼓,将九苑人逼至涂山脚下。史官在龟甲上刻着:“丙午日王于辕门执九苑酋长。”
到在位第三十年,夏朝疆域东到大海,西至昆仑,南抵云梦泽。商队从西羌带来青金石,东夷人献上能占卜的龟甲。
有个从羽山来的巫师偷偷说:"王的气运比大禹还旺",不降听见却把酒樽摔了:"再敢胡诌就割舌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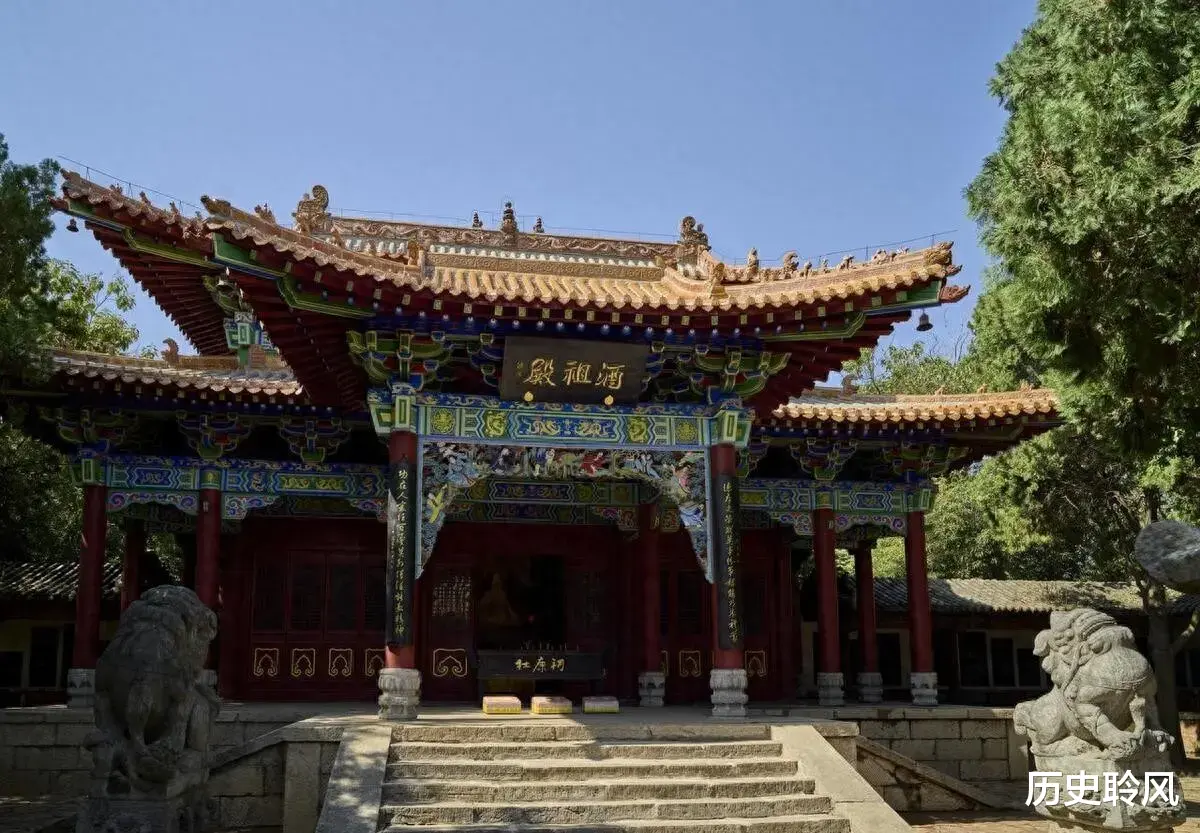
第三段:王位传给谁?
眼看着白发缓缓爬上鬓角,不降却在深夜中对着那星图轻轻叹气。长子孔甲整天都带着侍从去斗兽,有那么一次,他居然差点被犀牛给顶死。
更糟糕的是,在去年的秋祭之时,孔甲竟然将祭肉喂给了猎犬。宗正气得浑身直哆嗦:“这简直是要遭天谴的啊!”
在古时候,“宗正”这个职位,是在中国朝廷中负责管理、统筹比如说皇帝亲族以及外戚贵族等相关事务的。而且在先秦时期,就已然设置了这个职务,它的主要职责包含:整理皇室宗族的族谱;筹划并举办,祭祀仪式;同时处理,各种与爵位和俸禄有关的事情,这样的话是为了保证,皇室血统的纯正以及体系架构的稳定。
五十九年腊月,大雪压折了宫墙边的老柏树。不降把弟弟扃召到暖阁,炭火映着两人的影子在墙上摇晃。"明日你穿我的衮服上朝",他说着解下玄玉腰带
扃吓得跪地磕头,额头竟都磕出了血印子。第二天黎明,而且当群臣看到扃捧着传国玉玺走出来时,竟然突然集体哑了声。
第四段:九夷的青铜枷
黄河水哗啦啦地响着;不降踩着泥滩上的贝壳,紧紧地盯着对岸九夷人的篝火。那帮蛮子,居然将夏朝边境视作自家后院,(在春天抢麦子在秋天偷盐巴。
不降却把新铸造的青铜犁头,分给了边境的农户,而且还派士兵帮他们挖水渠。九夷的探子,看得眼红,趁着那月黑风高之际,摸了过来偷犁,正巧撞上了埋伏的夏军。
史官在竹简上记:“癸未年王擒九夷酋,十八人被铸铁链,囚于阳城。”被锁在太阳底下暴晒的酋长们,眼看着自家部落送来三百车粟米,用以换人。而那青铜犁,早已被夏朝农户使唤得油光发亮。
第五段:西羌的雪豹皮
昆仑山飘雪的那一年,西羌使者慢慢儿地,牵着白牦牛,走进了老丘。牛背上稳稳地,驮着九张雪豹皮,那些豹眼,竟然还镶嵌着绿松石。
使者恭恭敬敬地,跪下严肃地说道:“恳请大王给我们三十车粟种。”不降稍稍碰了碰豹皮上的冰碴,接下来好奇地问道:“听说你们山里人,是不是真的能拿羊毛编织地毯?”
三个月过后,夏朝的工匠,手持织机,缓缓走进山林。到了第二年春天,西羌人不但将粟种完好地归还了,而且送来了会跳舞的羚羊。
此期间一个叫乌木的羌族少年,被选中留在王宫,充当侍卫。十年时光,悄然过去,;他携着夏朝的犁铧,回到部落,把那些荒芜的土地,都改造成了整齐的梯田。
史书里轻飘飘写着一句:"羌人自此朝贡不绝",却没人提那年冬天不降把自己衮服里的丝绵掏出来,给织工换了五十斤羊毛。
第六段:宫墙里的秘密
嫡长子孔甲二十岁那年,在猎场射死了最后一只白犀牛。不降罚他在宗庙跪了三天,出来时孔甲冲着太阳发誓:"等我继位,定要造个比云台还高的兽笼!"这话被添油加醋传进王宫,吓得掌膳官打翻了祭祀用的酒
最让不降极为烦恼的,是小女儿姒姚。这丫头悄然地跟巫医研习星象,有一回竟然指向紫微星大声嚷道:“爹爹的帝星旁侧有颗恶星!”当晚观星台竟然就遭受了雷击,烧毁了三十册龟甲。
老臣们跪在殿外恳请他确立储君,不降反倒将传位诏书锁进青铜匣子,并且把钥匙丢进了护城河中。
第七段:青铜鼎上的裂纹
祭祀所用的司母戊鼎,突然间出现了一道裂缝;羊血顺着那道缝隙,缓缓地渗进了火塘之中,滋滋啦啦地,冒起了黑烟。
大巫高高举起那被烧焦的龟甲,猛地闯进了寝宫,说道:“天象已经发出警示,大王理应前往泰山进行封禅!”
不降却让人把裂鼎给熔了,而且接下来还掺进新铜,铸了十二面战鼓。鼓面蒙着那厚实的犀牛皮,敲起来的时候,竟然震得宫瓦簌簌地落灰。
第二年春天,东夷送来九车蚌壳,用以赔罪。其实他们听闻夏王竟连镇国宝鼎都胆敢熔化,于是慌乱地连夜将越境的渔船全部撤走了。
史官在甲骨上刻得用力,“王用霹雳般的手段展现出菩萨般的心肠,不过却偷偷地将崩飞的玉刀藏进了袖口,刚才刻字的时候因为用力过猛把刀给磕断了。”
第八段:最后的巡狩
七十岁的不降,忽然决意要去各处游历。
他乘着一辆,由八匹马拉动的,较为轻盈的马车,那马车的车轮上,缠绕着青铜片。
经过涂山之际,他指着当年与九苑剧烈战斗过的那个山谷,缓缓地说道:“此地方需立一块石碑。”接着石匠即刻开始劳作,雕琢出一块,高三丈的花岗岩碑
抵达羽山之后,他执意要去察看鲧(gǔn被处死之地,未曾想当天晚上竟突然发起高烧,言语也变得不清,口中呼喊着:“四岳九牧皆已背离!”,话语间满是焦急
最为奇妙的是,于河洛交汇之处,夜半时分,他独自一人踏入了芦苇丛。天亮之际,浑身湿漉漉地归来,怀中紧抱着一块镌刻着星图的石板。
其后此石板被镶嵌于观星台的地基之中,直至商汤灭夏之际,方才重现于世。而且其上所绘之图案竟为二十八宿的完整分布情况。
第九段:雪夜传位
腊月二十三,大雪把老丘城埋得,只剩旗杆尖。不降将弟弟扃按在那冰凉的青铜宝座之上,自己则裹着羊皮袄,蹲在炭盆旁边,烤着栗子。
你坐满三十年,接下来传给胤甲,而且这小子虽说瘸腿,不过其实他的脑子比孔甲更加清楚。
扃摸着王座扶手上,那上面有着深深的手指印,这些手指印是历代夏王在紧张时掐出来的。突然宫门外传来了撞钟声,是九长六短的那种,而且说真的,是嫡长子孔甲在带人冲击宫门。
不降抄起那烧红的火钳,接着便往殿外走去,青铜钺在他手中舞动着,发出呼呼的声响,而且在雪地上,居然顿时绽开了朵朵如同红梅般的痕迹。
青铜时代的生存美学——夏王不降的统治之道
在青铜那个年代,夏王不降的统治,很自然地,开开心心地散发出独有的生存美学,而且还融入了一些古老文明的特质。他所展现出来的风格,简洁明了充满了鲜明的个性特点。
青铜器的双重隐喻
青铜器对于不降而言,有着双重面孔。它既可以熔铸成为,战争的那种杀器,又能够打造成,象征着文明的那样神器。这暗示出,在夏王朝的统治里,暴力与文明,需要达成一种平衡。
战争有时是开拓疆土、维持统治的方式;其实最终还是得依托文明的力量,比如说农业生产这类的,以此来巩固并发展国家。
世袭制下的权力变通
不降在其位上,时长竟达五十九年,乃是夏朝在位时间最为长久的君主。据《竹书纪年》所记载于晚年之时,因其儿子孔甲性情乖张且不合宜继承王位,所以他打破了常规之举,把王位传予了其弟扃。
这种内禅的方式,看似是对尧舜禅让制的效仿,实则是在家族内部,完成权力的平稳交接,是对世袭制的一种清醒认知和灵活运用。
这一选择,犹如驯服凶猛野兽,既要有力的手段,而且又要巧妙的策略,治国亦是如此,恩威并施,才能让国家稳定发展。
观点
不降的治国理念,而且传位决策,都反映出了他针对当时那历史局势所拥有的深切洞察。其中“治国理念”被替换为“理政思想”,“具备”被替换为“拥有”使用了逗号分隔句子,且通过“而且”这个口语化衔接词使句子更连贯。
他用五十九年的统治经历,诠释了在那个时代,所谓的黄金时代”,需要统治者将统治手段运用得更加灵活、柔软让尖锐的王朝矛盾得到缓和,使国家能够稳步前行。
他的这些行为,最后都融入到了,历史的长河里,塑造着夏王朝的前行轨迹,这个时候,也给后人探究,那个时期的历史和文化,呈现出了独特的观察角度。
【相关权威参考来源和文献:《史记·夏本纪》《竹书纪年》《纲鉴易知录》《资治通鉴外纪》《路史》《绎史》《帝王世纪》《通志·氏族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