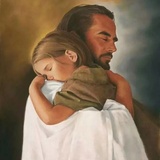前几天,一则普惠式医疗险广告,在小红书刷了屏。
作为全球最大保险市场,有着全球独一档的保险份额,且以发达著称。还能有啥,是这个最大市场没有的产品?或者说这款网红医疗险何以可言,美国没有?
背景,当是两国不同的社会保障体系,及因此而生的商业保险在期间的定位。

事实上,近年来随着线上跨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以及来华工作、旅行、生活的外国人增多,中外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差异对比时常成为网络热议话题。
尤其是2025年初,随着因TikTok禁令涌入小红书的美国用户及来华游客增多,玩起了“对账”,医疗保险也是个不可避免的话题。
美国网民分享的天价医疗账单以及保险的报销比例,让人感到惊讶。中国小红薯们也忙着给新老外“科普”中国医疗医保的实惠,以及每年几百块就能保上百万的现象级产品“百万医疗险”。
其实,保险尤其是医保,美国人自己吐槽了好多年看病贵,保险也贵的问题。从1912年泰迪·罗斯福想搞国家健康保险 (NHI) 制度,到100年后的奥巴马医保,但看病贵、保险贵的问题,依旧那样。
站在保险行业的角度看,为什么美国的医疗保险既昂贵又难以实现全民覆盖? 中美间医保体系又有什么样的不同?或许,这款产品以及广告语“美国不可能有”的逻辑,诉说的当是眼下中国式普惠医疗险的路子,和空间吧。
1 政府主导vs.市场驱动,中美医保体系的不同起点美国的医疗保险在世界上是特殊的存在。
最大的经济体,最强的国家,但几乎也是唯一一个没有国家主导的医保的大国。
和同为西方体系的欧洲相比,美国医疗保健的成本显著高于欧洲国家,其医疗保健支出占GDP的比例超过16%,而欧盟国家则为9-12%。按人均计算,美国每年的医疗保健支出约为1.2万美元,几乎是德、法等国的两倍。
这说来话长。
二战后,美国雇主开始将医疗保险作为一种附加福利来吸引工人,而美国缺乏一个强大的劳工政党来倡导全民医疗保健,只好选择一种权力分散、市场驱动的模式,这奠定了商业保险在劳动年龄人口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基础,并最终形成了如今以雇主为基础的保障体系。
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因素,二战后的社会格局不过是加速了这一态势的形成。
而这种保障体系,又产生了一个“碎片化”的医保体系,说大白话,就是“非统筹”。
其特点是覆盖范围不一致,存在大量医疗保险中间商,为雇主提供的医疗保险计划分配医疗资源,而这些机构往往以获取利润为目的。
即便在2010年通过了《平价医疗法案》(ACA),试图打破就业与保险保障之间的链接,并要求保险公司覆盖既往症患者,但由于既有保障体系各方间的复杂关系和结构,“碎片化”的格局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公共医保仅通过Medicare和Medicaid覆盖老年人和低收入群体,相当一部分人口仍然存在保障缺口。
与美国以市场为主导的模式不同,无论是欧洲还是我国,政府都在医疗保险改革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比如我们国家,以建立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为目标,通过强制性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以政府补贴为主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已实现了超95%的人群覆盖。
同时,在保证了基本的覆盖后,利用市场机制的效率和创新潜力,鼓励商业保险公司为保险保障“添砖加瓦”,建立起包含“社会医疗保险”“补充医疗保险”“百万医疗保险”“中高端医疗保险”和“高端医疗险”的多层次保险保障体系。
基本医保保基本,商业保险做补充。这种先考虑全民基本保障,再让市场发挥优势做补充,是我国医疗保障体系与美国以商业保险为主的一大制度性差异。
2 制度这个起点不同,后续的风险分摊逻辑也就不同医疗保险的制度不同,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保谁,不保谁”。
也就意味着风险分摊的机制大为不同,这决定了商业医疗险覆盖人群的广度和深度。
保险尤其是健康险,经常存在“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等挑战,受“大数定理”的影响很大,所以只有参保人数上来了,才能将项目持续地运营下去。
这就是医疗保障中效率与普惠相统一的一面。
诚然,诸如凯撒医疗以及“保险×养老”等模式构建了极佳的“保险-医疗”保障闭环,甚至成为当前我国商业保险和医疗、养老服务进行融合的范式样本。
但是,当一般保障和雇主支付挂上钩时,效率和普惠就产生了矛盾:
并非所有人都在大公司,也并非所有的人都在公司上班。
当医保成了雇主的福利,而不是公民的权利,公平就成了奢侈品。
这也是当前美国医疗保险的一大困境。
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统计,2023年约有2800万美国人处于医保“裸奔”状态。
目前雇主提供的团体保险覆盖64%的65岁以下人群,但失业者、自由职业者等群体面临“保障真空”;同时,对于中低收入者而言,每年高达8000美元的保险费用绝不是一个轻松支付的小数目。
根据KEF信息显示,2023年雇主提供的单人覆盖年均总保费约8393美元,员工平均缴纳1520美元;家庭计划年均总保费23968美元,员工平均缴纳6575美元。
而由于其医保体系中商业保险的主导地位,天然存在对利润的追求,再加上政府在医保体系中的话语权缺位,使得诸如惠民保等“政策性普惠保险”难以获得真金白银的财政支持,从而使得全民保险保障持续存在缺口。
尽管美国通过《平价医疗法案》(ACA)禁止拒保既往症,但相关产品保费高昂,且未针对慢病群体设计专属产品。
不可否认,如同前文提到的美国保险和医疗、养老的深度融合,我国商业保险如何实现医疗、养老服务的融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就普惠和效率的统一而言,依靠政府的财政、政策支持,已经显示出较强的比较优势。
事实上,唯有受益于城乡居民医保的广覆盖,作为其补充的商业医疗保险方可“轻装上阵”。同时,我国人口之巨也使得商业医疗保险有极大的创新积极性:被更多的客户认可,也就意味着获得了更大的市场。
正是在这种基本医保与商业保险协同发展的制度环境下,叠加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带来的市场机遇,商业医疗保险的创新得以蓬勃发展,不断迭代以满足更广泛人群的需求。
诸如中国人保、中国平安、太平洋保险、众安保险等险企推出的百万医疗险便是典型例证,其不断的迭代演进极大地提升了商业健康险的可及性。此外,近年来,针对既往症人群、慢病患者等特定群体的保障需求,市场上还涌现出新一代产品。
比如,说“美国不可能有”的众民保,便尝试将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既往症纳入保障范围,并将慢病管理服务融入产品设计,力求覆盖更广的年龄段和健康状况人群。
3 不同的基础,相异的逻辑,也就有了“美国不可能有”的普惠体系事实上,我国医保体系的广覆盖和普惠性,并非仅仅是因为基础医保的广泛覆盖为商业保险创造了空间。
更重要的是一个由系统性成本控制、明确政策导向、技术基础设施和社会文化共同作用的独特环境,催生并强化了商业健康险的普惠属性,形成了与美国模式显著不同的“协同效应”。
总结来看,最最重要的就是:
国家层面的系统性成本控制为普惠型商保奠定了基础。
这种系统性的成本控制,使得商业保险公司在设计产品时,无需像美国同行那样过度依赖复杂的精算博弈来规避高风险、高成本场景,可以将更多精力聚焦于扩大覆盖面和服务创新,从而降低了诸如百万医疗险等普惠型产品的定价门槛和运营风险。
同时,明确的政策导向与监管框架,也为商保塑造了该有的定位与市场秩序。
我国不仅通过“普惠金融”等顶层设计引导商业健康险服务更广泛人群、补充基本保障,还通过具体的监管措施规范市场。
比如,《健康保险管理办法》等法规要求保险公司强制披露条款、明确责任免除(如“五大既往症”),并建立行业黑名单制度,这提升了产品的透明度和消费者的信任度。
不得不说,相比之下,美国虽然鼓励市场创新,但缺乏统一标准导致产品复杂化,且在虚假宣传、拒保纠纷等方面的监管相对滞后,不利于建立广泛的信任基础和推动真正的普惠。
再说了,“政府指导、市场补充、社会监督”的模式早已成为各行各业行之有效的发展方式。
而这样一种“政府-企业-消费者”协同模式又反过来强化了保险的普惠共识,保险公司也更愿意通过提升服务和满足特定需求来赢得市场和社会的信任。
所以,中国的商业健康险之所以能呈现出“美国不可能有”的普惠特征,并非偶然,这是一个体系下的“水到渠成”。
这是国家主导的基础保障、系统性成本控制、明确的政策与监管引导、广泛链接的数字化基建以及独特的社会文化协同作用下的产物。
这种多重要素构成的“中国特色”发展环境,使得商业保险得以在效率与公平之间找到一个独特的平衡点,聚焦于补充保障和满足更广泛人群的需求,从而展现出强大的普惠发展潜力。
后记:要效率,更要公平诚然,美国需解决成本控制与全民覆盖的难题,而我国也面对在高端医疗技术和医养结合等方面的痛点,还面对着老龄化持续迫近的压力。
中美两国在医疗保障领域都面临各自的挑战。
但彼此并非绝缘的孤岛,未来的全球医疗保障体系,或许正需要从这种差异中寻求共同的智慧。
中国模式的普惠性与创新实践,为解决“看病贵、看病难”提供了东方智慧;而美国在养老、健康服务方面的实践以及在技术前沿的突破,则指明了提升医疗服务质量的方向。
最终,医疗保障的完善,是一个持续在社会公平与技术进步、制度效率与市场活力、当下福祉与长远可持续之间进行哲学式权衡的过程。
中国的经验,尤其是在大国背景下如何实现广覆盖和通过市场创新增强保障韧性方面,无疑为全球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意义,彰显了健康险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的本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