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女孩的朋友被人欺负时,
女孩想也不想,
立刻拿把刀冲上去,
抵住施暴者的喉咙大喊:
“老娘是从监狱里出来的,你不弄死我,我就捅死你”。

当女孩被盗窃团伙老大威胁时,
不管对方多少人,
女孩拿了烟灰缸就毫不犹豫地狠砸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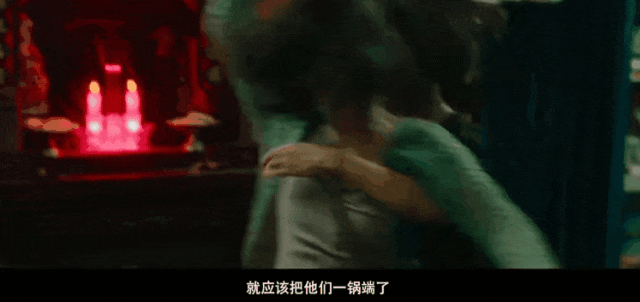
我们有多久没在大荧幕上看到如此生猛的女性角色了。
在冯小刚执导的《向阳花》里,
赵丽颖饰演的高月香让人感受到一种被生活逼至绝境的绝望呐喊。
《向阳花》的叙事主线聚焦于高月香(赵丽颖饰)和黑妹(兰西雅饰)两位刑满释放女性的生存挣扎。
前者为给失聪女儿筹钱装人工耳蜗误入歧途,
后者因出身贼窝被迫行窃入狱。
出狱后,
她们在职场霸凌、身份歧视、经济困顿中努力“活得像个人”。
擦玻璃、卖酒、试药,甚至冒充警察行骗。
影片以大量细节堆砌底层生存的艰辛:
20万的耳蜗、400元的日薪、被保安脱衣搜身的羞辱……
冯小刚用这些数字与场景,
试图构筑一个“豁出去,活下来”的生存寓言。

然而,
也许是导演想要表达的太多,
影片中苦难被扎堆成“符号化”处理。
人工耳蜗、聋哑身份、代孕勒索等极端事件被密集堆砌,
看似“真实”的苦难实则沦为满足窥视欲的奇观。
更割裂的是,
影片试图以“姐妹互助”对冲个体悲剧,
但高月香与黑妹的情感联结始终停留在“共同受难”的被动层面。
例如,
两人因手语结缘,
却在矛盾爆发时以“江湖叩拜关公”的男性化仪式和解,
这种强行植入的“义气”逻辑,
让整部影片看起来颇有些短视频逆袭的感觉。

《向阳花》里,
赵丽颖的表现堪称一次高风险转型。
她褪去“甜妹”滤镜,
以素颜、方言、暴戾眼神重塑高月香这一复杂角色。面对女儿被领养的绝望,
她爬上电线塔崩溃嘶吼。
面对黑妹的背叛,
她雨中踉跄追赶,
这些片段都展现了她对角色情感张力的精准把控。
然而,
影片对角色塑造的矛盾性削弱了表演的完整性:
前一秒为钱擦边行骗,
下一秒因“善良”放弃交易;
穷到买不起卫生巾却花钱假扮警察。
这种“何不食肉糜”的行为逻辑,
让角色在“狠戾母亲”与“江湖侠女”之间摇摆不定。

而更大的争议来自赵丽颖的方言台词。
尽管她努力模仿北方口音,
但生硬的发音与刻意压低的气声,
让部分台词(如“捅死你们”)显得像背诵广告词,
缺乏底层女性的粗粝感。
相比之下,
兰西雅饰演的黑妹以沉默的手语和爆发式的肢体语言,
反而更贴近聋哑人的真实状态,
成为影片中少有的“无声胜有声”的亮点。

目前,
《向阳花》在豆瓣上评分两极分化,
支持者盛赞其“为边缘女性发声”,
质疑者则痛斥其“消费苦难”。
导演冯小刚试图通过全女性阵容颠覆男权凝视,
但影片中男性视角的渗透依旧明显,
黑妹被侵犯时镜头对其身体的凝视、高月香卖酒时刻意暴露的穿着,
这些设计与其说是批判,
不如说是对女性苦难的二次剥削。
而影片更大的问题在于导演试图用“女性互助”解构结构性压迫,
但因为各种原因未触及制度性歧视的根源。
例如,
高月香因案底被职场排斥的情节本可深挖,
但影片仅以“努力就能逆袭”的鸡汤式逻辑草草收场。
这种对现实问题的回避,
使得“向阳花”的隐喻最终沦为一场自我感动的表演。
《向阳花》的争议,
映射了当下女性题材创作的集体焦虑:
如何在迎合市场与坚守真实之间找到平衡?
赵丽颖的“狠”撕裂了甜美女星的固有标签,
却未能刺穿叙事逻辑的虚浮。
冯小刚的镜头捕捉了底层的挣扎,
却沉溺于苦难的奇观化展示。
或许,真正的“向阳花”不应是被人工肥料催熟的大棚产物,
而是从现实的裂缝中野蛮生长的野花,
即使沾满泥泞,
也要直面阳光的灼烧与阴影的吞噬。

那么,
各位亲爱的朋友,
你们喜欢《向阳花》这部电影吗?
欢迎留言讨论,我们一起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