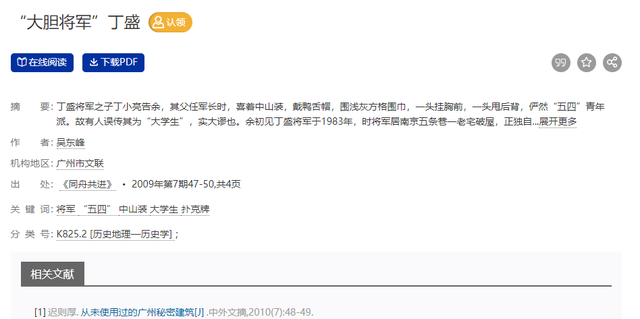1949年金秋十月,在湖南中部的衡宝(衡阳至宝庆,今邵阳)地区,国民党军“小诸葛”白崇禧指挥的桂系主力部队,凭借其多年经营的工事和相对完整的建制,仍在进行最后的顽抗,构筑起一道阻碍第四野战军主力南下的重要屏障。
时任第四野战军第45军135师师长的丁盛,率领本部兵马,如同一把尖刀,大胆穿插至敌军战线的纵深地带,执行分割、迂回、打乱敌军部署的作战计划。由于通讯联络的不畅和情报获取的滞后,加之部队推进速度过快,135师在穿插过程中,未能及时准确掌握敌军主力的动向和部署调整。

当部队抵达衡宝公路以南的灵官殿、沙坪地区时,竟一头撞进了白崇禧精心布置的陷阱。桂系的第7军、第48军等四个精锐师,如同合拢的铁钳,迅速从四面八方围拢过来,将135师紧紧包围在核心区域。向沉稳的司令员林彪在得知135师的危急处境后,也难掩焦虑之情,前线的态势似乎已经无可挽回,135师的命运悬于一线。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绝境,身处包围圈核心的丁盛,在仔细分析了战场态势和敌我双方的特点后,作出了一个极其大胆的决定:变被动为主动,反客为主,利用敌人包围圈尚未完全合拢、各部队之间协同必然存在缝隙和混乱的弱点,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军薄弱环节,实施猛烈反击和穿插分割。

桂系军队虽然兵力占优,但在仓促合围之下,指挥系统和部队协同必然存在问题,这正是可以利用的机会。丁盛迅速调整部署,命令部队收缩阵地,集中力量,以团、营为单位,像一把把锋利的匕首,利用夜暗和复杂地形,向着敌军结合部和指挥系统所在地,发起了猛烈的反向穿插攻击。
桂系军队的包围圈被丁盛的部队撕开了一个又一个口子,各部队之间的联系被切断,指挥系统陷入混乱。尤其是被白崇禧视为“钢军”的王牌部队——国民党军第7军,在135师灵活机动、猛打猛冲的打击下,阵脚大乱,建制被打散,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

此役共歼灭桂系精锐部队达1.75万人,其中包括击毙敌军师长、俘虏敌第七军副军长凌云上等高级军官。捷报传到北京,毛泽东主席在听取战报后,对丁盛的果敢指挥和135师的英勇作战给予了高度评价。
雪域扬威,瓦弄奇袭震印军
进入1962年,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东段越过“麦克马洪线”,不断蚕食中国领土,并最终挑起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在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严重威胁的关键时刻,已经从师长成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4军军长的丁盛,再次受命于危难之际,率领他麾下的这支王牌部队,紧急奔赴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藏东南地区,担负起在中印边境东段实施自卫反击作战的重任。

战斗发起前夕,瓦弄地区的天气条件变得异常恶劣,浓雾弥漫,能见度极低,有时甚至不足十米。印军依仗坚固工事和有利地形,认为解放军在这样恶劣的天气下难以发起有效进攻。54军的一些指挥员也心存顾虑,考虑到部队初到高原,重型火炮等支援武器尚未全部到位,且大雾严重影响炮兵观察和射击效果,便向军长丁盛请示,建议是否等待天气好转、或者后续重炮部队抵达提供更充分的火力准备之后,再行发起攻击。
丁盛在仔细勘察了地形、分析了敌情和我军状况后,认为眼前的漫天大雾,在常人看来是进攻的阻碍,但在他眼中,却成为了最好的天然掩护。大雾不仅会限制解放军的观察,同样也会让占据高地、视野开阔的印军变成“睁眼瞎”,无法有效发挥其火力优势,同时也为解放军隐蔽接敌、发起突然袭击提供了绝佳的条件。

随着丁盛一声令下,第54军的将士们利用熟悉的山地游击战术,巧妙地穿插迂回,分割包围据守瓦弄各个据点的印军部队。丁盛亲临前线指挥所,根据战场实时情况,灵活调整兵力部署,指挥部队多路并进,大胆实施近战、夜战,将印军的防御体系搅得七零八落。
经过大约十个小时的激烈战斗,解放军第54军成功攻占了瓦弄地区所有印军据点,彻底击溃了该地区的印军主力,取得了瓦弄大捷。据传闻,此战给印度军方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印军内部仍将“54军”的番号作为假想敌的代号,足见此战对其造成的心理冲击。

风云突变,上海之行定沉浮
丁盛先后担任过军长、兵团副司令员等级别职务,并最终在和平建设时期,被委以重任,成为镇守南疆的广州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战略地位重要,丁盛在此主政期间,励精图治,使得军区各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深得上下信任,可以说是他军旅生涯中一段相对顺遂和能够充分施展才华的时期。
1973年,为了贯彻“军队干部互相交流”的原则,中央军委决定对八大军区的司令员进行对调。丁盛接到通知,与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以性格刚烈著称的许世友将军互换岗位,前往六朝古都南京履新。

真正的风暴在三年后,也就是1976年降临。这一年,丁盛因公前往上海。期间,他下榻于上海市中心的延安饭店。在某天深夜,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的马天水,以及其他几位上海市的领导人物,前往延安饭店拜访了丁盛。这几个月后,丁盛在1976年上海延安饭店的那次深夜会面,以及此前可能涉及到的上海地区某些与武装力量相关的事件成为了审查的焦点。他被迅速卷入了这场政治风暴的中心。
审查期间,丁盛被指控参与了他们策划“反革命武装暴乱”的阴谋。面对这些极其严重的政治指控,丁盛多次向组织申辩,极力说明自己与所谓的“武装暴乱”阴谋毫无关联,反复强调诸如“他们(指上海方面的人)发枪的事情,与我有什么关系?”等言辞,试图澄清事实,证明自己的清白。

在当时“两个凡是”思想依然占据主导地位、政治清查运动带有扩大化倾向的特定历史背景下,个人的辩解往往显得苍白无力。丁盛的申辩未能改变审查部门的结论。1977年,相关的审查结论和处理决定最终形成并下达:丁盛被认定犯有严重政治错误,决定开除其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他被强制离开军队,生活待遇也一落千丈,据称每月只能领取大约150元的生活费来维持生计。
晚景落寞,将军风骨未曾改
尽管身处逆境,被组织“抛弃”,但丁盛内心深处对党、对军队的忠诚以及对自己清白的坚信,从未有过丝毫动摇。他坚信自己是清白的,所遭受的处分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冤屈。他几乎每周都会提笔,给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等相关部门写信,详细陈述自己的情况,辩驳那些强加于他的不实指控,要求组织重新审查他的问题,恢复他的党籍和名誉。

1998年,他接到了一位特殊人物的邀请——他的老战友、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黄火青。这次北京之行,最终未能实现他恢复党籍的核心愿望。但在老战友们的关心和帮助下,他的生活待遇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回到南京后不久,原广州军区考虑到他的历史贡献和实际困难,为他调整安排了符合师级干部标准的住房,使他的居住条件有了显著提升。
1999年9月,他因病重被送入医院救治。尽管医护人员尽力抢救,但终究未能挽留住这位老将军的生命。丁盛将军戎马一生,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红小鬼,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的骁勇战将,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高级指挥员,他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人民军队的建设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在他逝世后,为其举行一个符合其历史地位和贡献的追悼会,是合情合理的。

由于他特殊的政治遭遇和直到去世也未能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如何为他举办追悼会,特别是如何确定其称谓,成了一个颇为棘手和敏感的问题。有关方面在接到家属关于追悼会事宜的请示后,给予的答复是:追悼会主要由亲属自行办理。
既然要举行追悼会,就必须拟定讣告,布置灵堂,而讣告和灵堂横幅上的称谓,则是对逝者身份和评价的最直接体现。丁盛的亲属们,按照长期以来党内和军内的习惯,首先拟写了“丁盛同志”的称谓。这个最常规的称谓,在报请审查时,得到的回复却是:不能使用“同志”二字。理由很简单,丁盛已于1977年被开除党籍,直到去世也未恢复。

家属们无奈,考虑到丁盛生前曾是战功卓著的高级将领,于是又提议使用“丁盛将军”的称谓。但这个提议同样遭到了否定,或许是因为他被撤销了一切职务,其将军的军衔和身份在官方层面已不被承认。随后,又有人提出,丁盛是1930年参加红军的老革命,是否可以使用“老红军”的称号?这代表着他在革命早期的资历和贡献。这个提议似乎也未能获得通过。
最后,在反复沟通和权衡之下,不知是谁提出了一个相对中性、不涉及政治评价、又能表达对长者尊敬的称谓——“老人”。最终,这个看似平淡无奇的称谓被采纳,“丁盛老人”成为了官方认可的、可以在公开场合使用的对其的称呼。
参考资料:[1]吴东峰.“大胆将军”丁盛[J].同舟共进,2009(7):47-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