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缘起
作为中国古代最具典型意义和阐释价值的知识分子群体[1],“竹林七贤”历经一千七百余年的时光淘洗,不仅没有在国人的精神版图上日渐黯淡,反而历久弥新,愈益散发出其夺目光彩与迷人魅力。

《竹林七贤》
近年来,“竹林七贤”研究渐成热点,汇聚了数量可观、成果丰硕的研究队伍,截至2010年底,在海峡两岸,已先后举办过七次以竹林七贤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2]。竹林七贤研究的综合化、国际化趋势渐趋显著,以至于“竹林学”之谓水到渠成,应运而生[3]。
冥冥之中,我与七贤有缘。早在1998年,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还在读研究生的我便写过一篇不足七万字的《琴弦上的英魂——嵇康传》。
2009年,拙著《一种风流吾最爱:世说新语今读》问世,此书分“人物篇”和“典故·风俗篇”二册,差不多又把七贤等魏晋名士“巡礼”一遍。
或许是因缘际会,2009年11月至2010年9月,我应邀在央视《百家讲坛》先后录制《魏晋风流》和《竹林七贤》系列节目,耗时一年,共录制了25集。
2010年10月10日,后录制的《竹林七贤》系列13集先行播出,而根据讲座整理而成的《魏晋风流十讲》[4]则延宕了四年,今天才得以和读者见面。
众所周知,电视讲坛固然离学术堂奥相去甚远,但其传播普及之功亦不容无视。就我个人而言,常觉今生今世,若能在竹林七贤与魏晋风度的传播上略尽绵力,则心愿毕矣,至于来自周遭的抑扬毁誉,大可忽略不计。
记得10月21日那天,我在观看《广陵绝唱》一集时,不禁热泪长流,并抑制不住激动之情,率尔写下古风一首——《怀嵇康》:

《嵇康集校注》
叔夜龙凤质,平生最钟情。
金兰总相契,命驾千里行。
绝交巨源信,冷对士季声。
爱恨岂无意,生死何相轻。
东市临刑处,日光照美形。
一曲广陵散,千古播令名。
马昭一何蠢,钟会一何精。
屠刀锈腐后,青史耀眼明。
烈士泰山重,独夫鸿毛轻。
昔岂惭柳惠,今何愧孙登。
余生长恨晚,竹林久服膺。
青灯伴黄卷,朱墨和泪盈。
不才不自弃,只缘未了情。
痴心俗人笑,讷言夫子惊。
寂寞千年后,讲坛祭英灵。
所以不揣谫陋献丑如上,并非顾影自怜,而是想表明,我之闯入魏晋文学与文化研究领域,诚非积学日久所致,而全由性情契合使然。

《竹林七贤集辑校》
节目播出期间,同名小书亦同步出版。在书中,我把原本写好而并未录制的《七贤之谜》置于开篇,综合前辈及时贤的研究,将七贤之谜归纳为“人数之谜”、“传播之谜”、“地点之谜”与“聚散之谜”四端[5],并以七贤与魏晋易代之际的政争——曹马之争——作为绾合全书的纽带,试图于环环相扣的故事讲述中,凸显七贤之卓异人格及多舛命运。
然而,我更为关心的七贤以生命所凝聚而成的“竹林精神”,及其与“魏晋风度”之关系这一议题,在拙著中虽有提点[6],却尚未充分展开,这里试从知识分子精神史和心灵史进路切入,就此一问题做进一步讨论。讨论之前,且请对“魏晋风度”这一概念稍作梳理。

与“竹林七贤”一样,“魏晋风度”同是文化传播过程中渐次形成的文化概念和命题。就“魏晋风度”而言,其肇端固然当在一千六七百年以前的魏晋之际,而其真正凝结成为一大概念,则历时尚不足百年。
1927年7月23日,在国民党政府广州市教育局主办的“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上,时年46岁的鲁迅做了一场现在看来十分重要的演讲,题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7]。
在这篇将近一万字的演讲稿中,鲁迅谈到了三个方面:一是魏晋文章及其特点,概括下来就是:清峻、通脱、华丽、壮大;二是以“正始名士”何晏为祖师的服药之风;三是以“竹林名士”为代表的饮酒之风。
尽管除了题目,正文中并未对“魏晋风度”做过具体阐释,但鲁迅的意思当是,魏晋文章及名士们扇起的服药与饮酒两大风气,便是“魏晋风度”最重要的表现及展示。此后,“魏晋风度”便成为一大文化关键词,以之为题做文章者代有其人,络绎不绝。

《美学散步》
1940年,宗白华的《论〈世说新语〉与晋人的美》[8]问世。在这篇屡被称引的论文中,宗氏开篇就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宗氏以悖论的形式揭橥了魏晋时代的“艺术精神”,堪称孤明先发,振聋发聩。
此外,还有两个论断深具卓识:一是“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二是“中国美学竟是出发于‘人物品藻’之美学”。这两句话本身也可说是中国美学史上的重大“发现”。
1944年,哲学史家冯友兰发表《论风流》[9]一文,将“魏晋风度”张大为“魏晋风流”。在谈及名士之人格美时,冯氏称:“是名士,必风流。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假名士只求常得无事,只能痛饮酒,熟读《离骚》。他的风流,也只是假风流。嵇康阮籍等真名士的真风流若分析其构成的条件,不是若此简单。”

《冯友兰文集》
并进而提出,真名士必备之四个精神条件:曰玄心、曰洞见、曰妙赏、曰深情。进一步从人格美的角度深化了“魏晋风度”的精神内涵。
1948年,王瑶完成《中古文学史论》[10]一书,在《自序》中,作者称该书第二部分《中古文人生活》“主要是承继鲁迅先生《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加以研究阐发的”。书中的《文人与药》、《文人与酒》等篇什,后来成为研究“魏晋风度”的必读文献。
1981年,李泽厚《美的历程》出版,书中第五章题为《魏晋风度》,把这一议题的探讨和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
在《人的主题》一节中,李泽厚提出了“人的觉醒”这一命题,认为正是“人的觉醒”才使“人的主题”提上日程,从而形成了汉魏六朝这几百年的人性大解放和艺术大繁荣。这就又把“魏晋风度”的内涵在美学和哲学向度上推进了一层,使铃木虎雄首倡、鲁迅复加点染的“文学的自觉”说有了一个更可靠的理论前提。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一些学者纷纷就“魏晋风度”著书立说,为丰富这一研究做出了贡献[11]。
笔者也曾以风俗为切入角度,将“魏晋风度”分疏为以下十二个面向:(1)美容之风;(2)品鉴之风;(3)服药之风;(4)饮酒之风;(5)清谈之风;(6)任诞之风;(7)隐逸之风;(8)艺术之风;(9)嘲戏之风;(10)清议之风;(11)雅量之风;(12)豪奢之风[12]。除服药之风与豪奢之风外,其它十种风气均有正面阐释之价值。
窃以为,“所谓魏晋风度,是指汉末魏晋时期形成的一种时代精神和人格理想,具体说就是指受道家学说和玄学清谈思潮的影响,而产生的一种追求自然(与名教相对)、自我(与外物相对)、自由(与约束相对)的时代风气,以及由此在上层贵族阶层中形成的,一种超越性的人生价值观和审美性的人格气度。”[13]

《一种风流吾最爱:世说新语今读》
“魏晋风度”的探讨与诠释,实际上隐含着近代以来“人性解放”与“人格独立”等一系列大问题、大拷问。
其中就包括人对于现实政治的超越以及个体人格独立的问题。鲁迅做完演讲后即在给友人信中称:“在广州之谈魏晋事,盖实有慨而言。”[14]同样,我们研究“魏晋风度”,亦当存有反躬自问,重建知识分子风骨与精神之关怀。
事实证明,在精神层面,竹林七贤对魏晋风度和名士人格影响甚巨。不仅因为上述每一种风气,差不多都能找到他们的影子,还表现在,他们的立身处世,无不彰显着对自然、自我和自由的不懈追求。

《竹林七贤学术档案》

说到竹林七贤与魏晋风度的关系,不能不以《世说新语》为中心。我曾做过统计,《世说新语》中直接记载“竹林七贤”故事的条目共有近60条,还不包括刘孝标注释中的数十则材料。
这相对于全书的比例是非常惊人的。也就是说,《世说新语》差不多每20条记载中,就有一条是关于“竹林七贤”的!
这个数据足以说明“竹林七贤”对于《世说新语》全书以及“魏晋风度”的重要程度。下面就结合上述“三自追求”——追求自然、自我、自由——来谈谈竹林七贤之精神及其对魏晋风度之影响。
(一)求自然:“越名教而任自然”
竹林七贤的自然追求又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其一,容止顺自然。
所谓容止顺自然,即与我所谓之“美容之风”相关联。众所周知,魏晋之季扇起了一股对男性美之极端欣赏与追捧的风气,其事多见于《世说新语·容止》门。此一门类共39则,真是触目皆琳琅珠玉,朗然照人。
其中如“蒹葭倚玉”、“傅粉何郎”、“掷果潘安”、“看杀卫玠”等典故早已脍炙人口,给人一个鲜明的印象就是,魏晋男性美是偏于阴柔和雕饰的,甚至由于服药之风的影响,那些美男还略显病态,可说是阴柔美和病态美的结合。
然而,《容止》门中所展现的男性美,远比乍一看所得之印象更丰富。除了阴柔美和雕饰美,事实上更有阳刚美与自然美。如“床头捉刀”的曹操、“腰带十围”的庾子嵩、“嵚崎历落可笑人”的周伯仁,皆属此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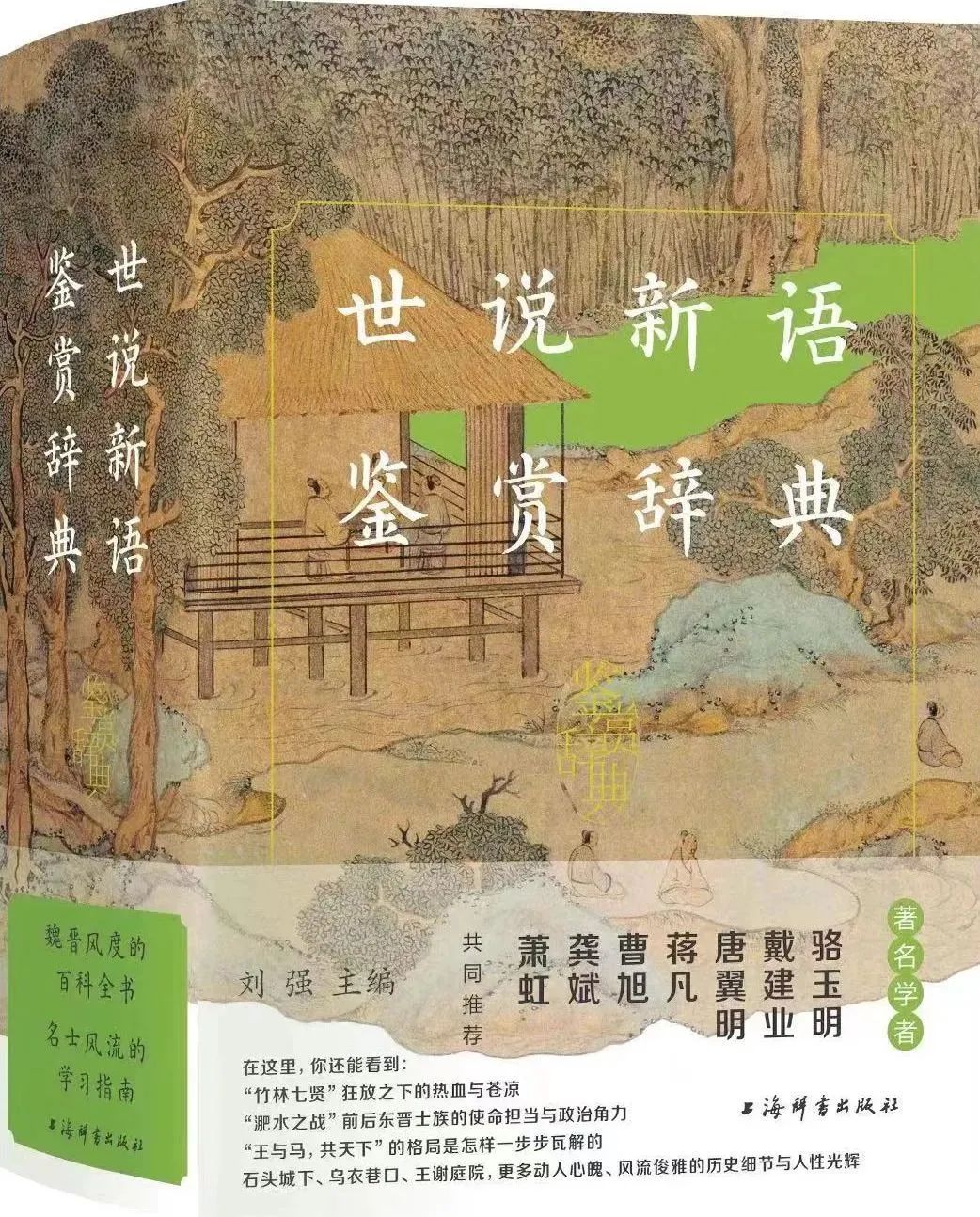
《世说新语鉴赏辞典》
而其中,最具风采的典型便是竹林七贤。《容止》第5则云:
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
高大,伟岸,健康,明亮,嵇康的美便是一种阳刚之美。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形容嵇康的语词全是自然化的,诗意的,其传达出的是一种“天然去雕饰”的自然审美观。
再看刘注引《康别传》:“康长七尺八寸,伟容色,土木形骸,不加饰厉,而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正尔在群形之中,便自知非常之器。”
这里“土木形骸,不加饰厉”和“龙章凤姿,天质自然”,凸显的也是一种不加修饰、顺其自然的自然美。同是一种男性美,嵇康之美便与“性自喜,动静粉帛不去手,行步顾影”(《容止》第2则注引《魏略》)的何晏等人判然有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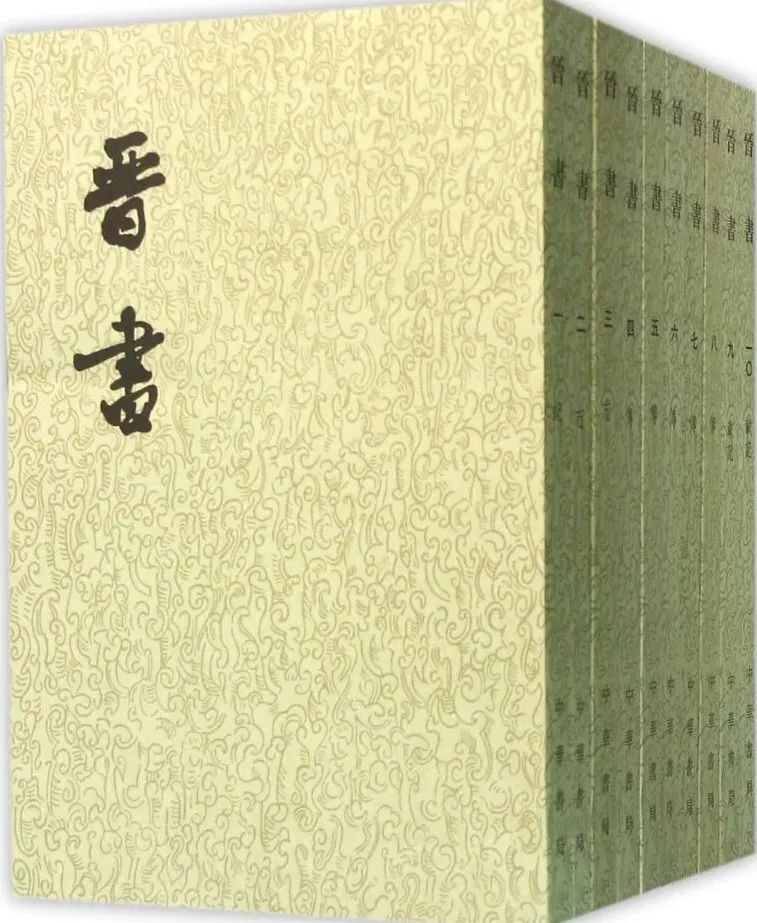
《晋书》
无独有偶。竹林七贤还有一位著名的丑男,就是刘伶。《容止》篇13则说:“刘伶身长六尺,貌甚丑悴,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土木形骸”,乃视形体外貌为土木之意。
又《晋书·阮籍传》称阮籍:“当其得意,忽忘形骸。”“忽忘形骸”正可与嵇康、刘伶的“土木形骸”等量齐观。可以说,摆落形体带来的世俗拘囿,不事修饰,萧然独得,顺其自然,构成了竹林七贤整体的人格风貌。
其二,思想尚自然。
所谓思想尚自然,则与玄学清谈之风相关联。正始时期,玄风大炽,何晏、王弼揭起“贵无论”的大旗,立论称:“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成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晋书·王衍传》)
又掀起“名教自然”之辩,主要的观点可以概括为“名教本于自然”。何、王一边是注疏经典(《论语》《道德经》《周易》)的经学家,一边又是领导清谈的清谈家,所谓“清谈祖师”。他们的玄学理路大致是“以道解儒”,这当然与调和儒道的现实政治需要有关。
当时,竹林名士们沐浴时风,同为魏晋玄学清谈之风的重镇。特别是嵇、阮二人的思想,与“贵无派”的正始名士何晏、王弼、夏侯玄等大不相同,其最鲜明的理论主张就是嵇康在《释私论》中提出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故竹林玄学被学界称为“自然派”。
如果说,正始名士继承了“老学”,致力于调和儒道即“名教与自然”之紧张关系的话,那么,竹林名士则发扬了“庄学”,“越名任心”,回归自然,他们都是庄子的隔代门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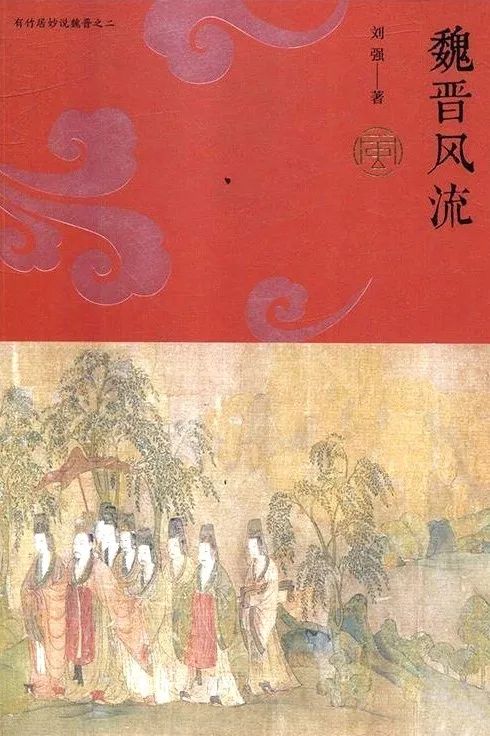
而且,他们真的做到了知行合一,思想上这样主张,实践上便这样贯彻,这就走向了反礼教的一面。也就是说,在儒家强调的“群己”关系之中,他们更加看重“己”——追求自我的实现和精神的张扬。容止顺自然与思想尚自然,一外一内,表里互济,共同营造了竹林七贤的人格基座。
三是居止近自然。
这是魏晋隐逸之风影响下的一种追求自然的生活方式,是思想上崇尚自然在行为上的落实和表现。《世说》中《栖逸》一门,最可见出此种消息。而这一门类,正是以竹林七贤为发端的。
当时的隐士喜欢在名山大川、茂林修竹之地隐居,如嵇康就隐居在风景秀丽的山阳一带。隐逸的风气也和名士们追求自由息息相关,关于这点后面还会谈到,这里且按下不表。
(二)求自我:“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此一种追求几乎是魏晋名士最本质的精神特质,在饮酒与任诞之风中表现最为显著。《世说新语·任诞》第1则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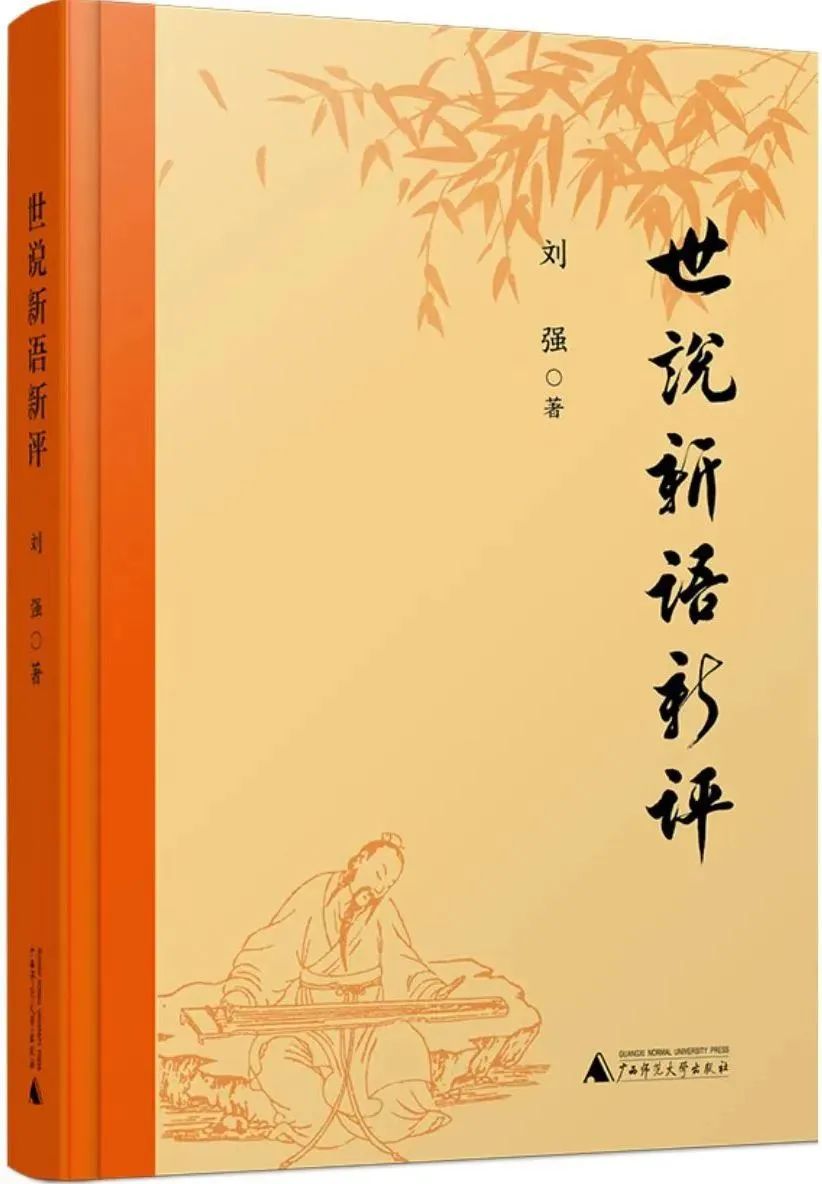
《世说新语新评》,刘强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2月版。
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世说新语》虽是丛残小语,然结构井然,每一篇之第一则无不体现作者之匠心与判断。这一则可以说是竹林七贤的“总纲”。说明在作者眼里,“任诞”之风的开风气者不是别人,正是竹林七贤,而“肆意酣畅”一语,又把饮酒之风提挈而出。
事实上,饮酒固然是任诞的一个表现,但不喝酒照样可以“任诞”。竹林七贤是如何求自我的呢?也可从三个方面来看:
一是方外求我。
“方外”,既可指“世外”,亦可指“礼外”。且看著名的“阮籍别嫂”:
阮籍嫂尝回家,籍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世说新语·任诞》7,下引均省略书名。)
阮籍的“礼岂为我辈设”,既是他的反礼教宣言,也是他的自我宣言。它与殷浩的“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品藻》35)的宣言一样,都奏出了魏晋名士张扬自我的最强音。

《阮籍集校注》
这里,“我”与“礼”构成了不可调和的两极,大有“礼内无我,礼外求我”之意。往深里说,当时司马氏鼓吹的“名教”已经不仅是“不自然”的问题,名教还绑架甚至消灭了“自我”!
阮籍的另外两个故事更具象征意义:
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坐,进酒肉。司隶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文王曰:“嗣宗毁顿如此,君不能共忧之,何谓?且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籍饮啖不辍,神色自若。(《任诞》2)
阮步兵丧母,裴令公往吊之。阮方醉,散发坐床,箕踞不哭。裴至,下席于地,哭,吊唁毕便去。或问裴:“凡吊,主人哭,客乃为礼。阮既不哭,君何为哭?”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制。我辈俗中人,故以仪轨自居。”时人叹为两得其中。(《任诞》11)
阮籍丧母是魏晋文化史上值得注意的一大事件,我曾写过《阮籍丧母考》一文,认为此一事件是阮籍由“至慎”一变而为“佯狂”的导火线。“居丧无礼”不仅是对当时礼教的反叛,也是阮籍丧母之痛带来的自我迷失的一种表现[15]。

《阮籍评传》
以前阮籍喝酒醉酒,是为了避祸,本质上还是清醒的,此时的阮籍却进入精神上的癫狂状态,因此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以自暴自弃的态度继续向名教发起挑战。彼时的他已不再用语言,而只用行动来确立自我。礼法之士如何曾辈对阮籍恨之入骨,而素有“清通”之誉的裴楷却看出了其中的奥妙——“方外之人”这一指认,正是裴楷对阮籍的自我追求的一种观感。
裴楷完全理解阮籍对礼法之士的轻蔑。在阮籍们看来,那些礼法之士不过是一些没有自我的裈中之虱、套中之人罢了,何足道哉!
这方面阮咸也是一个代表,他的“未能免俗”之典,以及在母亲丧礼上“骑驴追婢”、“累骑而还”的悖礼行为,其实也是“礼外求我”的一种表现。
二是酒中求我。
说到“酒中之我”,最佳代表不是阮籍,而是刘伶。刘伶在中国酒文化史上的地位自不待言,其在中国人之精神史和心灵史上的地位尚须重新认识。
在我看来,身材矮小、形貌丑陋的刘伶,却拥有一个无比强大、无比张扬的精神自我,而这个精神自我的最佳触媒不是别的,而是——酒。他的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无不凭借杯中酒来展示和抒发,而深具人类学价值和哲学深度。
史载刘伶“自得一时,常以宇宙为狭”(《容止》13注引梁祚《魏国统》),这种“天地之间唯我独大”的时空观和宇宙意识彰显的正是一个大大的“我”字!

《中古文学史论》
刘伶在酒中的那个自我真是令人“须仰视才见”。那是一个“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居无室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酒德颂》)的自我,是一个“常以细宇宙、齐万物为心”(《晋书》本传)的自我,是一个把生死看得很淡,扬言“死便埋我”的自我。
只有刘伶才能说出“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的豪言壮语,也只有刘伶才会上演下面的“人间喜剧”:
刘伶尝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任诞》6)
“入我裈中”的意象看似滑稽好笑,实则彰显了一个“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的大我和超我。这一刻的刘伶,不仅是位特立独行的“行为艺术家”,更是一个经天纬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大哲人!

《世说新语通识》
后来魏晋名士好酒成癖,说出多少绝妙的话来,如“酒引入着胜地”,“酒正使人人自远”,“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实时一杯酒”,“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等等,差不多都是承接刘伶而来。诚所谓“醉里乾坤大,杯中日月长”,刘伶通过酒,完成了自我人格的充分实现。
还有阮咸,也把喝酒这件俗事变成了狂欢甚至是图腾。他的“人猪共饮”的故事很多人以为是虚无和堕落,但我以为,其中弥漫着的是一种东方式的“酒神精神”。
如果说刘伶的“死便埋我”是庄子“齐生死”之思想的投影,那么,阮咸的与猪共饮则体现了“齐万物”的超越性。阮咸们似乎在表达,唯有在与自然万物的亲和中,人类才能更好地认清自我,找回自我。
或问:酒的麻醉作用常常使人“忘我”,又何来“酒中之我”呢?我的理解是,这里的“忘我”,忘的乃是鄙俗功利之“小我”、机关算尽之“伪我”,找到的则是解放超脱之“大我”、赤裸坦荡之“真我”。
东晋名士王忱说:“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任诞》52)这里的“形”亦可理解为肉体层面的“小我”、“伪我”,而“神”则指的是灵魂层面的“大我”、“真我”。
三是情中求我。
在魏晋,自然与名教的冲突,实质上也是“情”与“礼”的冲突。而人们在“发现了自己的深情”之后,便再也不愿意放弃这“人之所以为人”的最重要的禀赋。“礼外求我”并非空诸依傍,最终还要落实在“情中求我”。在更本质的意义上,“有情”方可谓“有我”。
这一点可以竹林七贤年龄最小的王戎为例:

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简服其言,更为之恸。(《伤逝》4)
这故事其实也可以理解为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名士对何晏、王弼“圣人无情有情之辩”的一种现实响应。王戎们不惮于以“中人”自居,委婉地表达圣人道境之难以企及,不如痛快淋漓地投入对情感的拥抱。
“情钟我辈”的“我辈”,正可与阮籍“礼岂为我辈设也”的“我辈”并观对照,其潜台词也可以理解为“情之所弃,绝非我辈”,这不正是“情中求我”的最佳诠释吗?
后来魏晋名士重情、主情、伤情的故事层出不穷,《世说新语·伤逝》门有精彩描画,实在与竹林七贤的身体力行、推波助澜大有关系。
(三)求自由:“不自由,毋宁死”
自由是否可能?人活在世上,怕永远无法摆脱此一追问。这同样也是竹林七贤面对的一个大问题,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他们给出了以下三种答案。
一是从隐逸中求自由。

明吴勉学刻本《后汉书》
这又与“隐逸之风”发生联系。古语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汉末以来,天下大乱,正是“邦无道”之时,加上道家学说日益盛行,佛教思想润物无声,以致避世隐逸蔚成风气,《后汉书》专设《逸民列传》就是明证。
降及魏晋,隐逸之风更是大行其道,不过由于政治环境之改变,具体表现上实与汉代不同。我曾总结过汉、魏、晋三个时期隐逸之风的不同取向:汉代人是孔子所谓“隐居以求其志”,魏晋易代之际则是“隐居以避其祸”,到了东晋,隐居流衍而为时尚,如郗超辈简直成了“隐士经纪人”[16],隐居之意涵遂发生滑转,变成了“隐居以求其乐”。
而在我看来,隐逸之风是中国人精神史和心灵史最值得关注的现象,士人们“避世避地避色避言”的目的,除了亲近自然,安放自我,同时也是为了追求自由。所以,以“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相标榜的隐逸之风,其实也是有志之士捍卫个体尊严和独立的一种姿态。
竹林七贤无疑是魏晋隐逸之风的重要代表,《世说·栖逸》门开篇就是阮籍“苏门啸侣”的故事,紧接着的两条又是嵇康的,这样的安排足以凸显竹林七贤对于隐逸之风的重要性。
而且,嵇康的两条故事颇具象征意义。一写“嵇康游于汲郡山中,遇道士孙登,遂与之游。康临去,登曰:‘君才则高矣,保身之道不足。’”二写“山公将去选曹,欲举嵇康;康与书告绝。”
这足以说明,魏晋易代之际,追求自由的隐居已经随着权力斗争的加剧而成了一种“奢侈”。仕和隐的选择几乎成了哈姆雷特之问:“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个问题。”因为在专制暴政者看来,弃权票就是反对票!
所以“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就变成了“邦有道尚可隐,邦无道必须仕。”嵇康坚持不与司马氏政权合作,贯彻隐居之志,最后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世说三昧:有竹居古典今读之三》
嵇康死后,隐居对于士人来说更无可能,后来向秀也不得不应郡计进京做官,还说了一句很伤人心的话——“巢由狷介之士,不足多慕”(《言语》18)。如果说隐居是一种以赛亚·伯林所谓“消极自由”的话,那么在极权暴政笼罩之下,这种消极自由已经成了“禁忌”,甚至是连罗斯福总统所说的“免于恐惧的自由”都无法实现了。
但是,隐逸本身所具有的那种超越性和自由度还是让后来的士人心向神往。到了东晋,政治环境相对宽松,名士们便纷纷把隐居当作生命的“秀场”,不断演绎着一个个“玄对山水”和“厉操东山”的佳话。因为说到底,东晋的隐士至少已经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总之,尽管竹林七贤并非一个严格意义上的隐士群体,但他们对中国的隐逸文化贡献至大,因为“竹林”二字本身就寄托着超尘出世的理想,不管“竹林”一词是中转自佛教,还是现实中的实存,其包含的意味都是与名缰利锁格格不入的自由追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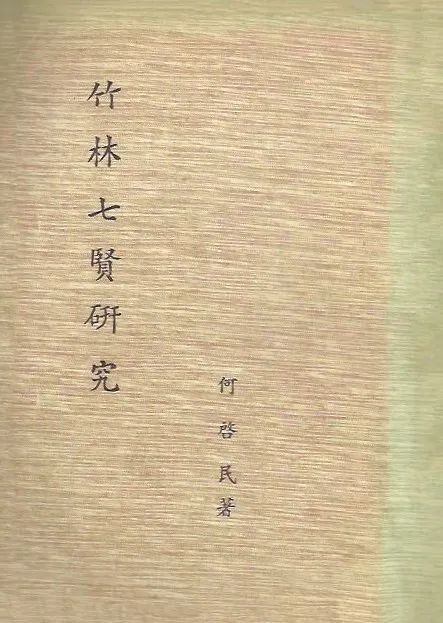
《竹林七贤研究》
二是从艺术中求自由。
魏晋虽是乱世,政争激烈,国无宁日,但思想和学术却相对宽松,所以这一时期,各种艺术样式都达到了空前的繁荣。汉代以前,很少有人因为艺术上的成就而名垂青史,而在魏晋,因为艺术而为后人敬仰膜拜的人层出不穷,史书的记载中,文体日益丰富,甚至书法的体式也被记录在案,这在前代是不可想象的。
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说:“艺术是发扬生命的,死神所在的地方就没有艺术。”我要再加上一句:艺术是人类放飞自由的最佳方式和最佳阵地,没有艺术的地方便无从感知自由。醉心艺术的人,常常是内心的自由需求极其强烈的人。
因为不管是哪一种艺术,都是人在自由地驱使“物”,而不是被“物”所驱使,只有在艺术的创造中,才能真正抵达庄子所说的“物物而不物于物”(《庄子·山木》)的自由境界。
竹林七贤中人多是当时杰出的艺术家。阮籍、嵇康除了是思想家,文学家,还是第一流的音乐家,他们都善弹古琴,都写过音乐论文。
除此之外,阮籍还擅长围棋和长啸;嵇康还是杰出的书法家和画家,他的草书被誉为草书妙品,唐代张彦远《书法会要》评嵇康为草书第二,而王羲之则屈居第八。嵇康的绘画造诣也很高,作品在唐代还有流传。阮咸不仅妙解音律,听力超群,而且善弹琵琶,据说是一种圆肚、长颈、四弦的琵琶的发明人,后来琵琶的别名就叫做“阮咸”,简称“阮”。这在中外音乐史上也是一个特例。
王戎应该也有才艺。因为王导看谢尚跳舞,看着看着,忽然对客人说:“使人思安丰(即王戎)。”(《任诞》32)这话很让人怀疑,王戎可能是个不错的舞蹈家。可以说,传统雅文化中所谓“琴棋书画”,差不多是从竹林七贤那里才真正熔铸为一个整体并发扬光大的。

《世说新语研究史论》,刘强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12月版。
他们或在音乐中体悟大道,或在诗歌中排遣幽情,或在书画中挥洒性灵,或在围棋中感受优雅,或在长啸中宣泄苦闷……艺术的天地,成了他们自由挥洒和诗意栖居的精神后花园。他们的艺术实践对整个魏晋南北朝的艺术之风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继“文学的自觉”之后,又直接催生了东晋的”艺术的自觉”。
三是从死亡中求自由。
这是一种极端的追求自由的方式,类似于西谚所言:“不自由,毋宁死!”在竹林七贤中,只有嵇康践履了这种追求自由的方式。由于出身背景、婚宦关系和个人气节等诸多原因的共同作用,仕和隐的选择问题,在“龙性难驯”的嵇康身上尤为尖锐地表现为生与死的选择和对抗。
《世说·雅量》一门对于中国精神史及人物美学的研究意义非常重大。“雅量”是魏晋人非常向往的一种理想人格,也是最具人文内涵的一种生命境界。雅量可以理解为人的胸怀博大,气量宽宏,临危不惧,处变不惊,不以外在环境的变故,改变内在人格的稳定性。

《魏晋风流十讲:世说新语中的奇风异俗》
雅量常常成为人们评价名士雅俗、优劣、高下的重要依据,像王子猷、王子敬在“火警”发露时的不同表现,祖约和阮孚对待自己癖好的不同态度,还有谢安和王坦之赴桓温“鸿门宴”时的不同气度,都是凸显名士“雅量”的著名案例。
我以为,雅量不仅关乎人的胆识、定力和气度,同时也关乎对自由的追求。因为“自由”也可以倒过来解,那就是“由自”。
质言之,一切外物都不足以撼动内在的自我,“我的一切我做主”,哪怕是在危险甚至死亡面前,也要将自己认可和追求的人格形象进行到底!
雅量人格往往可以通过外在的神色和表现显露出来,夏侯玄临刑、裴楷被收时神色不变,就是雅量的表现。而在魏晋名士“雅量人格”的舞台上,最值得注意也最令人“惊艳”的则是嵇康。
嵇康一生热爱自然,追求自我,崇尚自由。作为竹林七贤的灵魂人物,他最能体现士人或者知识分子应该具备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立身处世,为人为文,光明磊落,彪炳千古。
他的《山巨源绝交书》其实就是一篇“自由颂”,那“七不堪、二不可”的宣言就是“坚决不做公务员的九大理由”,这在官本位的今天,读之尤其令人神旺!西方有自由女神,如果中国要选一自由男神,我愿意投嵇康一票。
嵇康的伟大人格完型于他的“广陵绝唱”。《世说·雅量》2载:
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文王亦寻悔焉。

《世说学引论》
这是《世说新语》全书最有力量的段落,堪称惊天地,泣鬼神。嵇康之死堪称人类历史上足以与“苏格拉底之死”相媲美的最哀婉、最壮丽的死亡事件之一,是中国士人精神史和心灵史上最重要的华彩乐段,千载之下读之思之,犹令人荡气回肠。
嵇康之死不仅丰富了死亡的价值,更彰显了生命的尊严和自由的高贵。有鉴于此,我不敢苟同有些学者对嵇康之死类似“性格决定命运”的分析,换言之,嵇康之死如果只成为我们的性格分析材料,实在是对他的大不敬。
嵇康之死,使竹林七贤出现了极大的人格落差,更使他们成为中国文化史上最具阐释价值和哲学意蕴的文人群体。
关于此点,我想说的是,竹林七贤的每个人都有选择之权利,他们的选择及命运最终丰富了国人的人格图像和精神维度。我们不能因为崇敬嵇康,就对阮籍、山涛们大加挞伐,而应该具有“了解之同情”。

《竹林七贤诗赋英译》
进而言之,我们应该祈祷的,绝不是今后还会出现更多的嵇康,而是,让那个导致嵇康死亡的黑暗世道万劫不复,彻底消亡!

关于竹林七贤与魏晋风度之精神层面的探讨,上述所谓“三自追求”,只能算是一个宏观的、横向的观照,如果就竹林七贤对魏晋风度之影响做一纵向的梳理,还可发现一个历时发展的脉络。
而这一脉络差不多与汉末、魏、晋的名士人格之嬗变若合符节,即表现为从“风骨”向“风度”、再由“风度”向“风流”渐次滑落的动态过程。
“风骨”、“风度”与“风流”这三个概念全来自汉末以来的人物品藻和人伦识鉴。大概言之,“风骨”指人的风力、骨气,表现在人格上有刚烈、清峻的特点;“风度”则指人的风神、气韵、器量、识度的高妙;“风流”则很难就字面去诠解,略有广狭二义,广义包括前面的风骨和风度,狭义则似可理解为不执着于某种既定价值、率性任情、具有审美性和超越性的人格状态,类似于牟宗三先生所说的“清”、“逸”二气。就竹林七贤而言,这三种形态都有鲜明表现,难以量化区分。
大略言之,最具“风骨”的当推嵇康。嵇康实则继承了汉末清议名士陈蕃、李膺以及后来的士林领袖孔融的铮铮铁骨,他的死亡,宣告了清议的终结。故王夫之说:“孔融死而士气灰,嵇康死而清议绝”(《读通鉴论》卷十二)。

《读通鉴论》
如把“风度”与识度衔接,则七贤中阮籍、山涛辈可作代表,其它如刘伶、阮咸、向秀、王戎等人,则是由“风度”向“风流”转变滑落的过渡人物。
迨至两晋,尤其是玄风盛行的东晋,“风骨”如同清议一样渐趋式微,“风度”则被“风流”所取代,士人们不以物务自婴,“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晋书·刘惔传》),纵情于山水丘壑,流连于丝竹丹青,追求“神超形越”,便形成了所谓“江左风流”。
当是之时,尽管追求自然、自我、自由的大方向没有大变,但其中的生命张力和精神厚度却不可同日而语了。戴逵所谓:“然竹林之为放,有疾而颦者也;元康之为放,无德而折巾者也。”[17]洵非虚语。究其原因,实与汉末、三国、两晋之政治、思想、文化背景轮番“倒卷”[18]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以上,是我对竹林七贤与魏晋风度两者关系的一些粗浅理解,主要内容曾在不同场合讲述过,姑且置于此书的篇首,希望能引起读者的进一步思考。
注释:
[1] 此文是根据2011年3月29日在台湾成功大学的演讲整理而成。江建俊先生主编的《竹林风致之反思与视域拓延》,台湾里仁书局2011年7月版。又刊于《书屋》2011年第12期。[2] 河南省修武县政府已主办三次,分别是:2006年10月28-31日的“首届云台山竹林七贤学术研讨会”,2008年10月24-26日的“第二届中国修武云台山竹林七贤学术研讨会”,2010年11月13-14日的“中国云台山第三届竹林七贤文化学术研讨会”。成功大学中国文学系江建俊研究室也承办了三次“竹林文化的形成、流播与影响学术研讨会”,分别是2007年12月16日、2009年10月17日、2010年5月2日。此外,2010年11月6-7日,新乡学院樊荣教授亦发起承办了首届竹林七贤暨豫北历史文化学术论坛。
[3] 参见江建俊主编:《竹林学的形成与域外流播》,里仁书局2010年4月版。
[4] 按:此书系《竹林七贤》的姊妹篇,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初版,2018年再版时更名为《魏晋风流》。
[5] 参见刘强《竹林七贤》,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年10月版,页1-11。
[6] 如将“竹林精神”归纳为“独立、自由、放达、超越、重情、尚美”等几个面向,并与陈寅恪先生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相勾连,以彰显知识分子应有之品性。
[7] 此演讲后整理成文,收入杂文集《而已集》,1928年出版。参见《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页513。
[8] 原载《星期评论》,1940年第10期,后收入宗白华著《美学散步》一书,此书版本甚多,不赘。
[9] 冯友兰:《论风流》,《哲学评论》第四卷3期,1944。
[10] 此书《中古文学史论》完成于1948年,1951年8月由上海棠栋出版社出版,分为《中古文学思想》、《中古文人生活》和《中古文学风貌》三册。这里以其完成年代为准。
[11] 如刘康德《魏晋风度与东方人格》(沈阳:辽宁教育出版,1991),宁稼雨《魏晋风度——中古文人生活行为的文化意蕴》(北京:东方出版社,1992),马良怀《崩溃与重建中的困惑:魏晋风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刘宗坤《觉醒与沉沦:魏晋风度及其文化表现》(郑州:大象出版社,1997),尤雅姿《魏晋士人之思想与文化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7),郭平《魏晋风度与音乐》(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吴中杰导读《魏晋风度及其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范子烨《中古文人生活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等等。
[12] 参见拙著《世说三昧》,岳麓书社2016年月版。
[13] 参见刘强《一种风流吾最爱:世说新语今读·典故风俗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页220。
[14] 此为鲁迅1928年12月30日致陈蚌信中语。参见前揭《鲁迅全集》第11卷,页646。
[15] 此文曾在2010年第三届中国云台山竹林七贤文化研讨会上宣读。收入张新斌,徐学智主编《云台山与竹林七贤》论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9月版。
[16] 《世说新语‧栖逸》15则:“郗超每闻欲高尚隐退者,辄为办百万资,并为造立居宇。在剡,为戴公起宅,甚精整。”
[17] 戴逵:《放达为非道论》,《全晋文》卷一三七。
[18] 钱穆在谈到两汉、魏晋之际的学术政治大势时说:“西汉初年,由黄、老清静变而为申、韩刑法。再由申、韩刑法变而为经学儒术。一步踏实一步,亦是一步积极一步。现在是从儒术转而为法家,再由法家转而为道家,正是一番倒卷,思想逐步狭窄,逐步消沉,恰与世运升降成为正比。在此时期,似乎找不出光明来,长期的分崩祸乱,终于不可避免。”参见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修订第3版,页225。政治学术上如此“倒卷”,对士人精神与心灵产生相应之影响,必不难想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