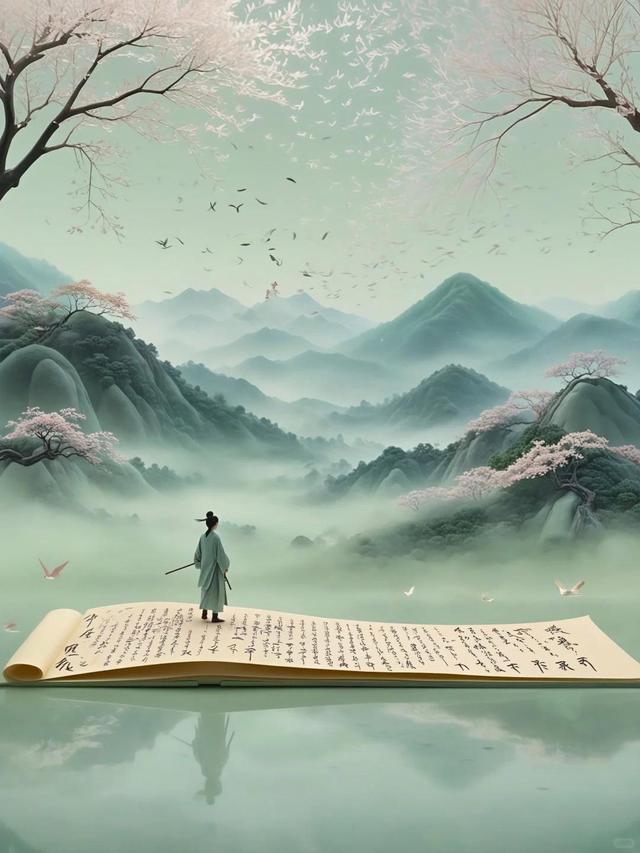读书,品诗,看电影
悟人生
我是威评书影史

01
《登高》
唐·杜甫
风急天高猿啸哀, 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 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 潦倒新停浊酒杯。
古人登高望远,在极目远眺,视野开阔中,个人的渺小和宇宙的无垠,容易触发内心的感受,于是喜欢抒发情怀。
登高之时,山风扑面,衣袂翻飞,仿佛整个人都要融入那无边的天地之中。脚下的山石坚实,头顶的苍穹浩渺,人在其间,不过是沧海一粟。这种渺小感非但不令人沮丧,反而让人心胸开阔,思绪万千。
杜甫登高望远,见秋色萧瑟,写下“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苍茫。他们的诗句,既是眼前景色的写照,也是内心情感的抒发。人在高处,视野开阔,心也随之澄明,许多平日纠缠的烦恼,此刻都显得微不足道。
登高不仅是一种身体的攀登,更是一种精神的超越。站在高处,俯瞰大地,山川河流尽收眼底,仿佛整个世界都在脚下延展。这种视角的转换,让人跳出琐碎的日常,思考更深远的问题——人生的意义、时间的流逝、自然的永恒。
于是,登高望远便成了一种心灵的仪式,让人在短暂的超脱中,重新审视自我与宇宙的关系。
如今的人们,虽未必如古人那般吟诗作赋,但登高时的那份心境,依然相通。或许是在城市的楼顶俯瞰万家灯火,或许是在郊外的山顶眺望云卷云舒,那一刻的宁静与豁达,便是对生命最好的慰藉。

02
一千多年前,杜甫登高望远,见秋色萧瑟,写下了一首《登高》。既是眼前景色的写照,也是内心情感的抒发。
人在高处,视野开阔,心也随之澄明,许多平日纠缠的烦恼,此刻都显得微不足道。
杜甫独倚高台,秋风裹挟着枯叶的沙响掠过耳畔。远处江涛拍岸的轰鸣与山猿哀啼交织,在群峰间荡出悠长的回响。他望着自己枯枝般颤抖的双手——这双曾写下"致君尧舜上"的笔,如今连酒盏都端不稳了。
浑浊的酒液在杯中摇晃,倒映出他霜雪般的鬓发。二十年前在长安曲江畔的豪饮仿佛隔世,那时新酿的绿蚁酒浮着细沫,与岑参、高适的佩剑相击声清脆如磬。而今严武病逝、李白坠江,故人星散如这漫天飘零的枫叶,只剩他拖着风痹的双腿,在夔州的山崖上独自咀嚼着岁月的苦味。
江面忽然掠过一道白影,是逆风而上的沙鸥。它单薄的翅膀切开翻滚的浪沫,恰似当年那个"会当凌绝顶"的少年。杜甫浑浊的眼底泛起微光,手指无意识地在空中勾画起来。远处渔舟的号子顺风飘至,他忽然挺直佝偻的脊背,任秋风灌满破旧的衣袍——酒可以停,笔不能停。
山脚下,牧童的竹笛声混着稻香升起。老诗人摸出怀中磨秃的狼毫,就着夕照在斑驳的栏杆上写下新的诗行。长江在他脚下奔涌不息,将那些沉郁顿挫的文字,送往千年后的月光里。

03
清朝时期有个叫杨伦的人,在《杜诗镜铨》中是这样评价《登高》这首诗的:
高浑一气,古今独步,当为杜集七言律诗第一。
确实,生活是一场修行,每个人都在负重前行。但其实,境随心变,若心态超然,那满目的秋景便是让人惊叹的美好;若愁容满面,秋天自然也就悲伤。全在于自己的感受和心境的变化!
有时候想想,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尺寸年华,就该乐其乐,尽余欢。
心华结撰,工巧天成,人生也大概是这样吧?

04
杜甫笔下"风急天高猿啸哀"的秋景,恰似人生百态的镜像。
这位诗圣在夔州白帝城外登高望远时,虽身患肺疾、耳半失聪,却将萧瑟秋风化作笔底波澜,把飘摇的人生境遇升华为震撼千古的艺术绝唱。
这种将苦难淬炼为诗意的能力,正是中国文人最动人的精神传承。
明代画家石涛曾言"搜尽奇峰打草稿",其实人生何尝不是如此?
每个人都在时光的宣纸上挥毫泼墨,有人把骤雨写成泪痕,有人却将雨滴点染成荷塘月色。
苏轼在黄州赤壁的江风明月里参悟"逝者如斯",王阳明于龙场驿站的瘴疠之地证得"心外无物",都是将生命困顿转化为精神飞跃的典范。
现代心理学中的"认知重构"理论,恰与这种东方智慧遥相呼应。当梵高把阿尔勒的麦田画出漩涡般的生命力,当贝多芬在失聪后谱出《第九交响曲》,他们都在证明:生命质量的砝码,永远握在心灵的天平上。
就像陶渊明采菊东篱时,南山不只是山,更是精神归处的象征。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比古人更需要这种"境随心转"的智慧。地铁里刷手机的低头族,若能抬头看见玻璃幕墙折射的云影;加班后疲惫的归途,若能驻足聆听梧桐叶落的韵律,生活便会展开新的维度。
毕竟,生命不是等待暴风雨过去,而是学会在雨中起舞的艺术。
05
可能这也是读古诗的意义吧?给心灵一个慰藉,给身心一个放松的方式。
感谢有杜甫!
杜甫的一生,是诗与苦难交织的旅程。尤其是安史之乱后,给他带来太多深刻的人生记忆,也使得他心灵得到了升华。
他携家带口漂泊西南,在成都草堂的短暂安宁里,仍不忘以笔墨记录民间疾苦。乾元二年秋,他写下"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呐喊,茅屋为秋风所破时,心里装着的却是整个破碎的山河。
战火蔓延至蜀地后,五十三岁的杜甫再度踏上漂泊之路。夔州的白帝城头,他望着滚滚长江东去,写下"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千古绝唱。老病缠身的诗人在这里完成了《秋兴八首》,将个人命运与家国兴衰熔铸成青铜般的诗句。
生命的最后三年,他像一叶孤舟沿湘江漂流。在潭州遇李龟年时,两个白发老人相对而泣,"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的平静叙述里,藏着盛唐陨落的全部哀伤。
大历五年冬,饥寒交迫的诗人倒在岳阳至衡州的小船上,临终前仍以颤抖的手写下《风疾舟中伏枕书怀》,墨迹未干便与世长辞。
这个用诗歌丈量过整个乱世的诗人,最终没能回到魂牵梦萦的长安。但他的诗句像种子撒遍九州,在后来每个风雨如晦的年代里,总会有人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中看见自己的影子,从"国破山河在"的痛切里找到共鸣。
杜工部用一千四百余首诗歌,为中华民族保存了最珍贵的苦难记忆与精神火种。
06
杜甫一首《登高》诗,道尽感慨,人生何尝不是在高低中徘徊?
现代人登高望远时,总在寻找某种超越性的视角。杜甫笔下"无边落木萧萧下"的苍茫,恰似中年回望时骤然惊觉的时光碎片——那些未竟的理想、错失的机缘、猝不及防的别离,都化作萧瑟秋风中的枯叶,在记忆的深渊里盘旋坠落。
但诗人紧接着写"不尽长江滚滚来",这又是何等惊人的生命辩证法:个体的凋零与天地的永恒,在此刻形成了奇妙的共振。
当代人的困境在于,既失去了古人"独坐敬亭山"的静观能力,又尚未建立适应数字时代的认知锚点。地铁里刷短视频的年轻人,办公楼里盯着KPI的中年人,都在进行着另一种意义上的"登高"——在信息洪流中踮起脚尖张望,却常常被算法推送的碎片压弯了脊梁。
当杜甫感叹"艰难苦恨繁霜鬓"时,他至少还能将生命体验淬炼成金石般的诗句;而这个时代的悲欢,更多时候消散在朋友圈的九宫格里,成为数据海洋中微不足道的浪花。
但或许真正的登高不在海拔,而在认知维度的提升。
就像苏轼在《赤壁赋》中悟出的"逝者如斯",当在人生中途停下奔波的脚步,学着用诗人的眼睛重新丈量世界时,那些看似沉重的"艰难苦恨",反而会成为滋养灵魂的养分。
长江永远向前奔涌,而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登高者,在无常中寻找恒常,在局限里触摸无限。
-作者-
威评书影史,自评自说自开怀,更多诗评、书评、影评,给您不一样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