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主要回答“南明为什么复国无望”的问题。
南明复国失败,与“抗清”能否成功没有半毛钱关系。“抗清”是“抗清”,“复明”是“复明”。按当时的状况,明朝复国几乎无望。即使抗清成功,明朝也注定成为历史。
王朝的本质上是公司制。明朝经过二百七十年,历史的“负资产”相当沉重,除了推倒重来,根本没有第二条出路。
参考汉末三国面临的局面。各路军阀嘴上说的是“光复汉室”,心里想的全是主意。根本没有人想真正回到汉朝,“光复汉室”和阿弥陀佛一样,是军阀集体的心照不宣和权宜之计。

南明也好,三国也罢。背负一个如此沉重的历史包袱。除非有一个类似“曹操”的人物出现,采取非正常的手段,勉强还能给王朝续命一两代。
历史给过南明这样的机会,可惜没有抓住。
孙可望便是南明版的“曹操”。正史中,孙可望是一个企图“称帝自立”,被李定国赶走的奸佞。这种观点是有待商榷的。
南明最大的问题是各路藩镇军阀拥兵自重,皇帝指挥不了军队,没有形成反清复明的统一战线。弘光、鲁王、隆武、永历不过是军阀手中的“吉祥物”。
在这种混乱局面里,必须由一位真正懂内政且精通军事的“军政全才”来总览全局,方能脱离困境。纵览南明群英,只有孙可望能担此大任。
在经营云南一事上,孙可望的能力得到过证实。1646年,云南经过沙定洲叛乱,境内满目疮痍,30万人横尸遍野。孙可望接管后,积极推行土地和货币改革。三年时间,云南恢复到了“耕者有其田、战者有其食”的状态。这在南明历史上堪称奇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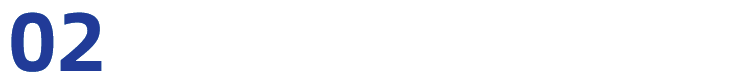
孙可望确实有野心,想效仿曹操玩一手“挟天子以令诸侯”。野心绝不是政治家的诟病,而是天然属性。只是孙可望没有料到,第一个带头反对的是结拜兄弟李定国。
如果把孙可望比作曹操的话,相当于曹操对内宣布要“挟天子令诸侯”,曹仁、夏侯惇、夏侯渊、曹洪、乐进和李典这伙人立马站出来反对,表示誓死拥护刘家的大汉天下。
理性分析。孙可望的膨胀,远没有到“称帝自立”的程度。“称帝自立”无异于曹操炉上烤彘(欲使吾居炉火上耶),成为众矢之的。且不说会招来清朝的针对,心怀异志的汉人军阀也不会轻饶了自己。凭孙可望的政治头脑,不会想不到这一步。
留着永历皇帝当吉祥物,作为一面旗杆。起码在道义层面上能够约束一下各路军阀。与清朝开战时,不至于后院起火,甚至能够适当配合牵制清军。
按理说,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政治计划,也是南明种种出路中“唯一一条活路”。
但孙可望错在“在一个错误的时机,去干了一件正确的事”。郑成功、张煌言、马进忠、沐天波这伙“塑料盟友”不支持也就罢了,李定国、刘文秀、白文选、冯双礼同样激烈反对。再加上,刚刚输了宝庆和常德之战,孙可望的“民意支持率”大幅下降。
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孙可望的政治理想破灭了。

这又引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李定国要反对孙可望。是为了反对而反对,还是出于“忠于大明”而反对。
种种迹象表明,李定国反对孙可望与忠于大明有关系,但不是主要关系。如果李定国真有这样的觉悟,一开始就不会加入大西推翻大明。
在这件事上,李定国带有浓烈的主观私心。从义弟刘文秀和永历皇帝的一段对话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孙可望走后,李定国做的第一件事,是把刘文秀从贵州召回昆明。名义上是让他协管内政,实则是对刘文秀实施监视控制。
刘文秀也是一位内政奇才。在他的治理下,贵州已经出现恢复之象。召回刘文秀,等于放弃了贵州这座军事桥头堡,云南失去了一道重要的军事缓冲区。
刘文秀一撤,清军迅速占领了贵州和湘西,南明在大西南地区势力缩水一半。
回到云南后,永历帝跟刘文秀聊起孙可望叛逃一事。刘文秀对永历说,自己带着大队人马,沿大路追赶。一时大意,让孙可望抄小路轻骑逃走。
永历帝听后,沉默半晌,叹息一声说,早知截不住孙可望,不如痛快放他走,经过这一番刺激,日后必对朝廷心怀愤恨。

永历的话,明显透露出对李定国处理这件事感到不满。如果孙可望真有称帝自立的野心,永历自然不会埋怨李定国。李定国把孙可望和南明的关系推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
刘文秀同样感到郁闷,从贵州回到昆明不久,忧愤而死。
孙可望对南明来说,是低配版的“萧何”。没有了孙可望,刘文秀也病死了,后勤交给谁谁管理,粮草从哪来,兵源从哪征。
事实果然得到验证。三年后,南明彻底下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