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的历史长河中,朱载坖作为第十二位帝王,其知名度相对较低。关于其姓名,曾存在一定争议,有人记作“朱载垕”,但经严谨考证,其确切称谓为“朱载坖” 。

在历史长河中,关于隆庆帝之名的记载为何长期存在混淆却无人明晰指正?这一现象背后,实则有着复杂的文献记载差异。在传统正史二十四史之《明史》中,将隆庆帝记作朱载垕。然而,与之相悖的是,《明实录》作为记录明代诸朝史实的重要文献,其中嘉靖与隆庆两朝的相关记载却均记作朱载坖,诸如“上命皇第三子为载坖”的表述。不仅如此,《皇明诏令》以及《朝鲜王朝实录·中宗恭僖大王实录》等文献,同样将隆庆帝之名记为“载坖”。值得一提的是,拥裕派大臣陈以勤曾就隆庆帝名字做出阐释:“乃生而命名,从元从土,若曰首出九域,君意也。”
朱载垕之名缘何出现?历史上是否确有其人?答案是肯定的。朱载垕乃齐东温惠王朱厚炳之庶长子。嘉靖四十一年,朱厚炳辞世后,朱载垕承袭爵位,登上齐东王的宝座。
在古代封建王朝的礼制规范下,皇子与藩王断无重名之可能,尤其是对于未来承继大统的皇帝而言,避讳制度极为严苛,其名讳绝不容他人僭越。明朝朱氏皇族在命名时,严格遵循以“金木水火土”为偏旁部首的规则,加之其后裔繁衍昌盛,致使可用之名日渐稀缺,甚至不得不创造诸多新字。在此背景下,自万历朝往后,关于隆庆皇帝之名,讹误流传,历经三四百年之久。
随着史学研究的持续深入,诸多学者以详实证据加以佐证,促使朱载坖之名逐渐为学界及大众所认可。朱载坖虽看似平凡,却身世显赫,乃明世宗朱厚熜之子,明神宗朱翊钧之父。朱厚熜在位长达45年,朱翊钧在位48年,而朱载坖在位6年。祖孙三代统治时长总计近百年,于明代历史进程中占据重要时段。

朱载坖系朱厚熜的三子,朱厚熜共育有八子。其长兄出生后不久便不幸夭折,彼时,次兄被立为太子,然十余岁时亦溘然离世。至此,皇位继承的关键位置,引得朱载坖与其弟朱载圳皆心生觊觎。盖因八位皇子历经岁月,最终仅存此二人。但命运弄人,排行第四的朱载圳未能争过朱载坖,于嘉靖四十四年病逝,年仅二十八岁,且身后并无子嗣留存。
明朝时期,朱载坖生母康妃杜氏于早年在宫廷中未获恩宠。朱载坖获封藩王之际,严嵩等一众朝臣竞相攀附太子,身为皇三子的朱载坖遂遭冷落。彼时,他置身太子争夺之局外,淡然处之。而其兄、弟先后离世,使得皇位机缘悄然降临于他。嘉靖四十五年,朱厚熜龙御归天,徐阶与张居正二人协同草拟遗诏,辅佐朱载坖顺利登基,旋即改元隆庆。
朱厚熜,这位对道教尊崇有加的帝王,在其统治时期醉心于修仙之道。彼时,其身边有一道士名为陶仲文,颇得朱厚熜青睐。陶仲文曾提出 “二龙不相见” 这一独特观点,即皇帝贵为真龙,而皇子乃潜龙,若两者相见,真龙之气会对潜龙形成妨害,进而致使皇子殒命。朱厚熜的长子与次子相继离世,此事在其心中投下浓重阴霾。鉴于此,此后他不仅刻意避免与其他皇子会面,甚至连册立太子一事也搁置未行。

尽管朱厚熜采取了相应举措,却依旧未能摆脱命运的阴霾,其余数位皇子仍相继过早夭折。此后,朱厚熜为规避类似厄运,有意识地减少与子女的接触。在此情形下,皇三子朱载坖与父亲的关系渐行渐远。相较于朱厚熜,朱载坖缺乏其父亲那般的政治谋略,既无征战沙场之能,亦无洞察民生、治理国家之智,这使得朱厚熜对其深感不满。
自彼时起,父子间竟长达二十年未曾谋面,朱载坖长期处于阴霾笼罩之下。朱载坖之母康妃杜氏辞世之际,朱载坖恰得子嗣,此情形引发朱厚熜不满。因依礼制,丧期生子乃为大忌,朱厚熜原本对杜氏的嫌恶,由此进一步波及朱载坖。
以明世宗朱厚熜朝为例,诸多举措显露出其对皇四子朱载圳及其母卢氏的偏爱。如未允皇三子朱载坖依制守孝三年,亦未追封朱载坖生母杜氏为贵妃,且明令文武百官在杜氏丧期不得身着丧服。在此情形下,朱载坖深知争宠无望,对于子嗣之事亦不敢再向朱厚熜奏报。此外,朱载坖之子朱翊钧的命名被长期搁置,满月剃胎发一事也未向朱厚熜禀明。彼时,朱载坖与朱载圳皆未被立为太子,时任礼部尚书徐阶,基于规制,曾三次奏请朱厚熜册立朱载坖为太子,然而,朱厚熜均予回绝。
在朝廷政治格局的悄然演变中,势力逐渐分化为两大阵营。其一以严嵩为核心,其二则以徐阶为代表。严嵩一方倾向支持朱载圳,而徐阶阵营偏向拥护朱载坖。彼时,朝堂之上流传一则关乎皇位继承的流言,传言严嵩图谋加害朱载坖,欲助力朱载圳登上皇位。经调查,此流言源于前左春坊左中允郭希颜。最终,朱厚熜下诏,将郭希颜处以斩刑。
郭希颜意图借传播流言,使朱厚熜陷入困境,以期促使其早日确立太子之位。当其奏请立朱载坖为太子,并命朱载圳前往藩地时,朱厚熜积压数十年的怒火,一并倾泻于郭希颜身上,决然判定其死罪。然而,为缓和舆论影响,朱厚熜最终采纳郭希颜所奏,诏令朱载圳就藩。所择藩地为湖北德安府,此地恰是数十年前朱厚熜启程之所。
自严嵩遭籍没、徐阶升任内阁首辅之后,明世宗朱厚熜仍未册立朱载坖为太子。此举清晰表明,朱厚熜对朱载坖不仅毫无喜爱之情,甚至怀有憎厌之意。据载,朱厚熜曾于宦官面前表露此类态度,相关言论旋即传至湖北。闻此消息,朱载圳旋即奏请前往武当山,为朱厚熜举行道教祭天祈福仪式。此举动意明显,旨在迎合朱厚熜对道教的崇信,而朱厚熜亦允准了朱载圳的奏请。
徐阶面临着严峻的困境,他一直寄予厚望的朱载坖,在皇位继承问题上似乎前景渺茫。然而,时移势易,不久之后,朱载圳竟身染重病。徐阶致信朱载圳,郑重建议其安心养病,待身体康复后再行祭祀祈祷之事。但事与愿违,朱载圳终究未能战胜病魔,不幸病逝。至此,朱载坖成为朱厚熜唯一在世的皇子,皇位归属遂成定局。此后,朱厚熜于西苑病情急剧恶化,移驾乾清宫后不久,便溘然长逝,朱载坖甚至未能与父皇见上最后一面。

嘉靖四十五年末,徐阶奏请入宫拟就遗诏,并提议由朱载坖主理丧事。草拟遗诏之际,徐阶特邀张居正襄助,而高拱对此全然不知。彼时,朱载坖甫即皇位。在皇子时期,朱载坖便目睹朝廷内部权力倾轧、勾心斗角之态。故而即位之初,其首要考量并非急于建树政绩,而是致力于维持政权平衡。鉴于文官集团长期内斗,势力此消彼长之态势朱载坖自幼熟知,打压任何一方皆可能引发无端损害,遂其秉持宽容理政之方针。
明世宗朱厚熜龙御上宾后,为明穆宗朱载坖留下诸多干练能臣,诸如徐阶、李春芳、高拱以及张居正等。此辈久历朝堂,浸淫政务多年,于国家大政要事洞悉入微。若此等贤才齐心辅弼,朱载坖治理国政或可事半功倍。朱载坖鉴于其父朱厚熜一生痴迷求仙问道,却终究未能证道成真,反因服食仙丹而崩逝,故而其即位之后,明确表明对道教持坚决抵制之态度。
道观神坛遂成为重点整治目标。朱载坖敕令将其尽数拆除,并褫夺邵元节、陶仲文等道士的官爵。与此同时,于关外颁布大赦令,海瑞亦自狱中获释。因进谏而身陷囹圄的官员,大多并无严重罪责,故而多获平反昭雪,并得以重新起用。
然而,这般兴盛之态未能长久维系。初履新职时的蓬勃干劲逐渐消退,朱载坖在朝堂之上愈发沉默寡言,决策时亦缺乏明晰主见。进而,他竟下令朝臣无需上朝,可居家休养。正值而立之年的他,却醉心于后宫游乐,对朝政事务全然怠忽,大有重蹈晚年朱厚熜覆辙之势。此情形引发朝廷上下诸多议论,诸如皇上久未亲临朝堂、未曾主持祖宗祭祀仪式,且对堆积如山的奏折置之不理等。甚至有朝臣为此专门上奏谏言,而朱载坖却以廷杖之刑应对。
最终,各项政务皆交付内阁处置,此举措获得朱载坖的默许,实则意味着其对政务的有意疏理。彼时,内阁大学士共计九人,分别为徐阶、李春芳、高拱、郭朴、陈以勤、张居正、殷士儋、赵贞吉与高仪。在这一众大学士中,徐阶身为首辅,威望显著高于他人。紧随其后的,则是李春芳、高拱以及张居正。尽管这三人同处内阁,然而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融洽。
隆庆初年,朝堂之上权力斗争暗流涌动,徐阶与高拱展开激烈角逐。徐阶凭借言官之力,营造强大声势,迫使高拱及其党羽郭朴不得不离开权力中枢。早在草拟朱厚熜遗诏之时,徐阶便未让高拱参与,此举致使高拱对其恨意颇深,一直耿耿于怀。此后,高拱暗中培植自身势力,坚信时机成熟时,定能将徐阶扳倒。与此同时,皇帝朱载坖对朝政的态度发生转变,由起初对朝野诸事的宽容处置,逐渐变得消极无为,对朝中动向不闻不顾。然而,他并未意识到,自己这般行事,已然在朝堂之中埋下了派系纷争的隐患。

于内阁之中,徐阶蓄意对高拱加以排挤,致使高拱为求自保,毅然主动奏请辞官。至此,内阁内部的这场权力纷争暂告一段落。然而,高拱虽离开内阁,却并未就此罢休。他旋即联合宦官与给事中,对徐阶展开弹劾攻势。弹劾之举再三上演,徐阶敏锐察觉到自身处境堪忧,极有可能重蹈严嵩覆辙。权衡之下,他深知与其被动承受他人不断构陷罪名,莫若主动引退。于是,在隆庆二年,徐阶以年老为由,请求归乡,内阁首辅之位遂交由李春芳接任。
明隆庆五年,高拱荣膺内阁首辅之职。上任伊始,便对前任首辅徐阶穷追不舍,必欲除之而后快。为此,高拱特意差遣海瑞前往苏州,查办徐阶相关事宜。幸得海瑞念及徐阶昔日救命之恩,并未对其斩尽杀绝。期间,徐阶曾致信高拱,言辞恳切,恳请高抬贵手。然而,高拱对此置若罔闻。最终,徐阶被抄家,虽性命无虞,却无奈举家从上海迁至浙江湖州,并于湖州度过余生。
徐阶身为资深朝臣,得以安享晚年,其根本缘由在于明穆宗朱载坖无意对其施以诛杀。徐阶在漫长岁月中,始终不渝地辅佐明世宗朱厚熜,为朝廷鞠躬尽瘁,功绩与辛劳均不可忽视。故而,即便高拱屡屡弹劾,朱载坖亦未对徐阶痛下杀手。然而,徐阶的政治生涯终结,亦与张居正的作用息息相关。作为徐阶的门生,张居正与高拱携手,促使徐阶辞官退隐。徐阶秉持保守理念,行事向来审慎。他凭借此特质成功扳倒严嵩,却最终在政治斗争中,为昔日阵营之人所累,不得不退出政治舞台。
张居正得以跻身内阁,源于徐阶出于制衡高拱之目的而对其加以援引。然而,张居正的政治理念却与高拱更为契合。二者同属改革派阵营,故而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于内阁之中维持着相对平稳的共事局面。徐阶,其为官履历长达45年,自嘉靖二年始,迄隆庆二年终,尽管与高拱年龄差距不甚显著,但其主流思想相对保守,与高拱的理念格格不入,此乃致使他遭受排挤的因素之一。至于明穆宗朱载坖,其在这一政治格局中,既未展现出明确的偏向与干预意图,亦未采取强硬的主导举措,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居中调解的角色。
在隆庆朝的政治格局中,徐阶与高拱二人皆意图促使对方卸任归乡,朝廷为维系双方势力均衡,同时顾及各自颜面,采取了相应策略。彼时,另一重大历史事件为俺答汗率军南下侵扰明朝边境。俺答汗所属势力,实乃土木堡之变中瓦剌部的余脉。其屡次进犯明朝边境,核心诉求是促使明朝全面开放贸易市场。明朝自中后期起,推行严厉的抑商政策,严禁民间私自开展对外贸易活动,一旦发现,涉事者将被严惩下狱。诸如海禁举措以及对马市的严格管控,均为明朝实施禁商政策的有力体现。
为稳固大明社稷,避免土木堡之变的历史悲剧重演,明穆宗朱载坖着力强化边防军事训练,对边防将领予以重用。隆庆四年间,明朝军事态势向好,战事多捷,不仅鲜有败绩,还收复诸多失地。是年六月,明军在对鄂尔多斯等部落的攻势中,斩获蒙古军首级160余颗。八月,蒙古进犯锦州,亦遭明军痛击,被斩40余人。至九月,俺答之孙把汉那吉归降明朝。此时,王崇古建言接纳把汉那吉,并以此为契机,凭借人质优势,迫使俺答归服明朝。此议得到高拱与张居正的支持。

朱载坖认为此举于明朝之大一统颇具裨益,遂饬令高拱与张居正全力推进。经双方审慎谈判,终达成共识。俺答承诺不再侵扰明朝边境,并将充任其谋主的白莲教徒赵全、李自馨等数人交出。与此同时,明朝亦遣返把汉那吉,并应允通贡开市之议。此次议和,在历史上被冠名为“隆庆和议”。
此后,明朝与蒙古迎来了长达数十年的和平稳定阶段,这在一定程度上大幅削减了明朝的军事财政支出。明穆宗朱载坖不仅开启了与蒙古的互市贸易,还推行解除海禁之策。自明朝建国伊始,海上贸易市场便逐步遭到封禁,而此举致使民间贸易活动悄然兴起。由于此类情形难以全然掌控,官方亦只能采取适度宽松的态度。盖因管控过严,倭寇作乱现象便会愈发猖獗,甚至会趁夜实施劫掠,给沿海民众带来诸多困扰。为有效整治沿海地区的混乱局势,朱载坖采纳高拱的提议,开放海禁,推动江海联动贸易,这一举措对明朝的经济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朱载坖实施的开关举措,犹如冲破坚冰,终结了明朝延续两百余年的海禁政策。据相关统计,隆庆年间,明朝白银存储量占据世界总量半数以上。开关不仅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收益,还使得彼时明朝沿海地区海盗活动显著减少。在土地赋税改革方面,朱载坖推行清丈土地与一条鞭法。清丈土地旨在重新丈量税负不均衡的土地;一条鞭法,海瑞将均徭均费等银两,不再区分银差与力差,统一以征银方式施行,此方法在嘉靖初年虽已在局部地区有所尝试,但尚未全面推广。而在朱载坖时期,海瑞的实践让起源于江苏、上海等地的一条鞭法更为完善,进一步推动了明朝赋税制度的变革与发展。
一条鞭法秉持简化原则,整合各类差徭、土贡等项目,废止力役形式,统一以征银代之,并由官府统筹雇人承担劳役,相应役银均按田亩进行摊派。除江南部分地区仍负担供应宫廷膳食所需漕粮外,全国范围内田赋普遍改征折色银两。通过这一系列举措,不仅极大地简化了征税流程,促使赋役朝着货币化方向发展,亦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经济的进步。
在局势渐趋向好之际,明穆宗朱载坖却身染沉疴。朱载坖在位仅六年,朝堂之上能臣济济。鉴于此,其个人并未在历史长河中留下显著声名,不为大众熟知亦属情理之中。在位期间,朱载坖的主要理政方式为充分放权,对臣下的举措多予以应允,使能臣得以施展抱负。这些臣子本就期望凭借政绩获取君主认可,皆有积极作为之心,故而朱载坖顺势采取相对无为的理政态度。
从另一视角审视,或可认为朱载坖在决策与思维层面缺乏自主性与鲜明特质,甚至被视作性格懦弱的君主。然而,此观点并非关键所在。朱载坖如此性格的形成,与其自幼所处的成长环境紧密相关。早期,其行事常处于惴惴不安之态;但登基之后,身为一国之君,天下大事皆决于其手。彼时,国家财政充盈,民众生活富足、社会安定,边疆亦无战事纷扰。基于此有利局势,朱载坖遂开启了以个人享受为主的执政状态。
在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历史进程中,明穆宗朱载坖在位期间呈现出特定的行为模式。据相关历史记载,诸如《国榷》所云:“上初在裕邸,姬御甚稀,自即位以来,稍好内,掖廷充斥矣。”这表明朱载坖在身为皇子居于裕邸时,生活尚显清心寡欲,姬妾数量稀少。然而,登基称帝之后,情况却发生显著转变。当政期间,朱载坖似乎全然抛却理政之重责,将心思过度倾注于后宫声色。或许是受其父遗留药物之影响,亦或是自我约束能力的匮乏,他逐渐沉溺于酒色之欢,不仅怠于上朝,更使得宫廷之内夜夜歌舞升平。此种行为的巨大转变,充分反映出其在面对权力与诱惑时,未能有效坚守自律,从而陷入纵欲的泥沼之中。
在往昔,所处环境中女性数量相对稀少,然此情形并不足以表征其品性端方。及至后来,随着财富的积累与地位的提升,其所处社交圈层中女性数量显著增多,他的行为便开始背离道德规范。由此可见,“男人有钱就变坏”这一观点,并非毫无依据。《明实录》作为重要的历史文献,亦对其沉溺女色、荒淫纵欲的行径有所记载,其相关描述之程度,甚至可用“夸张”一词来概括。据载,即便在身体已然卧于床榻之时,他仍执意行宠幸美女之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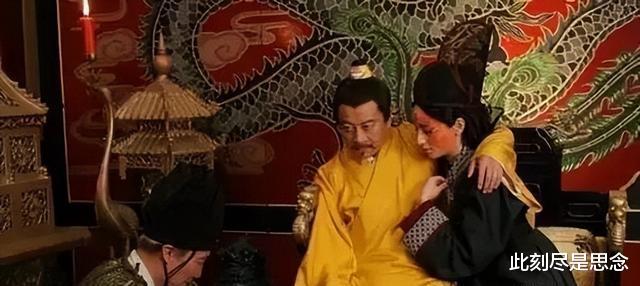
据史载,朱载坖35岁时崩逝。此前,其抱恙静疗两月,病情非但未愈,反而加剧。其表征为头晕目眩、手部震颤,坐起之时症状尤为显著。从这些症状综合推断,朱载坖的离世极有可能源于心血管类疾病。长期沉溺声色且服药不当,或引发脑中风,致使其最终溘然长逝。
朱载坖,乃朱厚熜之子、朱翊钧之父。虽其在位时长仅六载,然相较于其父朱厚熜与子朱翊钧,其统治展现出别样风貌。朱载坖在位期间,政治氛围相对宽松,于政务处理与个人生活方面,似未背负过多沉重压力,行事较为顺遂自如。若朱载坖能始终秉持稳健之治国方略,大明王朝之历史轨迹或许会发生积极转变。
张居正改革紧随其后,实则是对隆庆年间一系列政策的延续与拓展。朱载坖的离世,为历史徒添诸多憾事。此后,明朝国运自万历时期再度走向衰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