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上,凡改革必然存在争议,张居正改革也不例外。
450年来,关于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是良法,还是恶法?争论至今。

什么是“一条鞭法”。明史中,是这样概括。
一条鞭法者,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故谓之一条鞭。
这段话透露出两个基本要点:
一是徭役、杂赋统一并入田赋。徭役和杂赋打包摊入田赋后,百姓只需承担“田赋”一个税种,至于官府需要徭役时,不再惊扰百姓,由官府花钱雇人干活。
二是朝廷不再征收粮食、丝绢一类实物,统一该收银两。
一条鞭法不是张居正的原创,而是嘉靖时期内阁大学士桂萼发明的。桂萼提出“编审徭役,通计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完全是后来张居正“一条鞭法”的骨架模型。
不同的是,在此基础上,张居正加了一条“计亩征银,折办于官”——银子取代实物。
1578年,张居正下令全国推广“一条鞭法”时,就遭到很多人反对。反对的理由是,明朝是“以农立国,收银不收物,不利农事”。
反对者的理由不无道理。“一条鞭法”推广后,虽然前期取得了拉平税赋、减少成本的效果,但副作用的威力同样巨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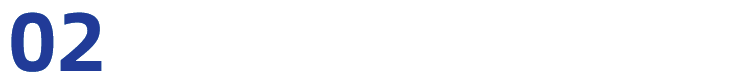
以自耕农为例。
过去,一户自耕农所交的赋役是固定的。比如,一年交2石粮食,如果年景好,收获了3石,那么这一年会有1石余粮可供自由支配。如果年景不好、粮食减产,只收获了1石粮食,那么这一年就亏了1石粮食。
是盈是亏,官府不用操心,风险由自耕农自己担着。只要把定额的粮食交上去就完事了。至于家里没有余粮,会不会挨饿,那是自己的事儿。
当一条鞭法来了后,自耕农该交的税一分没少,还是2石粮食的定额。只不过官府不再要粮食,改收2两银子(粮食和白银兑换比例“壹两一石”)。
问题是,土地是老百姓收入的唯一来源,庄稼地里只能种出粮食,长不出银子。想从土里扒出银子,只能拿粮食找有银子的富商巨贾大地主去兑换。
如果手握银子的富商巨贾能够尊重市场,严格按照“壹两一石”兑换给百姓,百姓倒也不亏。
可是。“壹两一石”的兑换比例只是一种约定成俗的市场习惯,不在朝廷强制规范之内,白银兑换属于民间“黑市”交换。
如果富商巨贾存心找茬,故意用粮食品质来压低兑换比例,非要“壹两一石五”的话,老百姓是兑还是不兑。
不兑的话,完不成任务。兑的话,血亏。

这样一折腾,老百姓要完成过去2石的任务,需要付出3石粮食,平白无故亏了1石。
官府倒是省心了,过去收实物,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去运输、看管、维护,如今只需要拿着麻袋,挨家挨户要银子就行了。
相当于,由朝廷承担的支出,经过富商巨贾这一道,转嫁到了自耕农身上。很快,自耕农和普通小地主阶层经不起“一条鞭法”催生出的“黑产”揩油。
一时间,大明王朝人人“谈地色变”,百姓纷纷视“土地”是有害的东西。既然朝廷是“按地收赋”,如果手里没有土地的话,是不是就不用承担“田赋”了。

于是,明朝进入了一段“佃户”狂潮。自耕农和小地主阶层纷纷放弃土地,跑去富商巨贾家里当“佃户、织工”,走向了一条职业打工的道路。
视田如荼毒,去之唯恐不速。于是,而世业之田皆归于无籍之豪民。(湘乡县志·卷三下·赋役志)

自耕农放弃土地,去给大户人家打工,任由土地荒废。首当其冲的是,朝廷征收的田赋逐年减少。
皇帝一看,这样不行。没人种地交田赋,我怎么养兵打仗。
于是。40年后(1578年1618年),万历四十六年,加征“辽饷”登上了历史舞台。
打这开始,明朝社会危机再也按不住了,彻底进入无可救药的晚期。
白银的威力还远止于此。没有“一条鞭法”以前,所有王朝只有一个主要矛盾——土地兼并。
过去,“土地”是唯一的硬通货,豪强地主想巧取豪夺、盘剥百姓、揩油皇帝,唯一的手段就是“土地兼并”。
土地是不“长腿”的,它跑不了。兼并的越多,事搞得越大。当吃相太过难时,惹怒了天下,皇帝派人一查,一目了然。皇帝只要把不法地主解决掉,把多占的土地分下去,百姓怨气立刻消解。
徐阶就是最好的例子。巴不得整个松江的土地都是他家的,那又如何?海瑞让他交出多占的土地,还不是乖乖照办。
“一条鞭法”实施后,把银子炒成了硬通货,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银子真的会“长腿”,找个深山老林挖个地窖一藏,皇帝上哪找去。
“一条鞭法”的结果是可以预见的。最后的结果是,穷死了百姓和皇帝,吃肥了大地主群体。

PS:站在封建皇帝、官僚地主、富商巨贾立场来看,“大明首辅”四个字毫无争议。“一条鞭法”让皇帝成了最大的短期受益者。长久来看,大地主大富商才是真正的受益者。
站在自耕农立场来说,是“续命”,还是“索命”,还真不宜评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