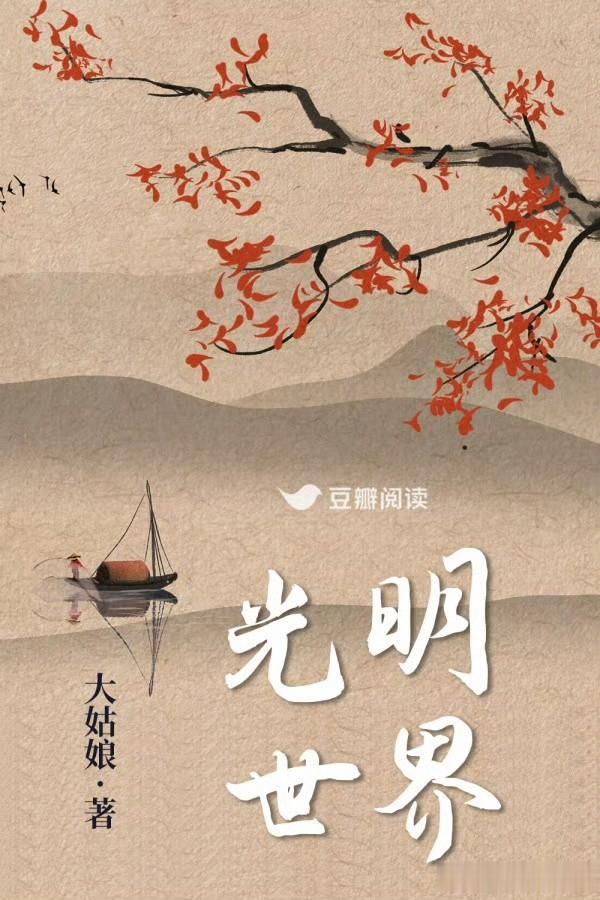十七岁那年,老夫人给了院里的大丫鬟两个选择。
要么给各房爷们做妾,要么给外院的管事做妻。
我们四个人,三个都选了妾,只有秋霜选管事。
她问我为什么,我低下头默默地想:
因为我不想我的孩子再做丫鬟了。
1
决定后半生的那天是个大晴天,日头高高挂着,照得人眼花。
陶妈妈和煦地对我们说:「这是一辈子的大事,老夫人仁厚,让你们自己决定,今晚都好好想一想,明日来告诉我结果。」
毕竟还是小姑娘,我们四个都红了脸。
春露作为年纪最大的姐姐,等陶妈妈离开才开口道:「现在不是矜持的时候,我们四个一起长大,情谊比亲姐妹还厚,互相通个气吧!别往后不小心做了仇人。」
她眼睛雪亮地盯着每一个人,只因她早就有了去处。
我们四个都是老夫人院里这一茬的大丫鬟,老夫人是林府最大的长辈,我们的去处自不会差。按从前几位姐姐的例子,合该是配个前院的管事,再回后院做个管事妈妈。
但那得二十岁往后。
也是叫我们赶着了。老夫人有三个儿子,两个亲生的,一个庶子,谁家的家业都是长子担着,老侯爷在边疆驻守,大爷是世子,就是府里的顶梁柱。
偏大爷二十七岁了,还没有儿子。
大夫人是个善妒家世又好的,前头又生过一个女儿,老夫人便一直忍着,忍了六年,大夫人再没怀过孕,做母亲的终于坐不住,要往大爷房里塞人。
可只给大爷塞,就是在打大夫人的脸,等于指着她骂不能生,所以老夫人便决定每房都指一个,首先想到的,就是我们四个。
她是个心软的老人家,做妾跟配管事两条路都让我们选,左右院里多的是丫鬟,若我们不愿,总能凑够三个愿意做姨娘的。
而春露,她是早就被大爷看中的那一个,她怕多一个人跟她抢。
夏荷最先笑笑道:「我看三爷挺好,老夫人疼小儿子,我也能得着好。」
秋霜撇撇嘴:「我不想做妾,生个孩子都不能叫我娘,没意思,我要选个管事。」
我则讷讷道:「我瞧着二夫人和气,我想进二爷的院子。」
二爷是府里唯一的庶子,春露不放心地确认:「冬雪妹妹,你当真吗?」
我点点头,自是当真的,娘早就教过我,做姨娘的,夫人什么样,比夫君什么样更重要。
2
可到头来事情还是出了差错。
春露欢欢喜喜绣她那床鸳鸯被的时候,被人冲进来塞住嘴绑了出去。
大大的厅堂里,她惨白着脸跪在那儿,大夫人甩出几个肚兜对老夫人说:「还请母亲做主,这个丫头虽是您院里的,却是个臭的。她跟马厩的董癞子私通,这些肚兜就是证据,万不能配给大爷。」
老夫人的面色沉下来,小辈这么骂长辈的丫鬟,这是在向老夫人叫嚣,叫嚣她不满意老夫人给大爷纳妾的安排。
可不等老夫人开口,她又笑眯眯道:「但您院里的,除了她都是好的。媳妇儿瞧着夏荷就很好,不如母亲换个人,把夏荷指给大爷,也好让大爷早日开枝散叶。」
原来不是不让大爷纳妾,只是不让他纳那个合心意的妾。
我一个丫鬟能看懂的事,老夫人自然更能看懂,她沉痛地看着春露,可只一瞬就收敛道:「老大房里的事终究是你做主。既如此,就换成夏荷吧!来人啊!把春丫头拉出去,跟马厩那个一起赶出府。」
从头到尾,春露嘴里的布都没取下来过,她惶恐地进来,绝望地出去,主人们连一句辩解的机会都不给她。
因为在老夫人心里,她冤不冤枉不重要,儿子房里的安宁才更重要。
这一场别人的祸事里,冷汗淋漓的却是我这个旁观者,我捏紧了帕子,再一次在心里起誓,我再也不要生下一个跟我们一样的小丫鬟。
3
夏荷哭了一整晚,她跟春露一个屋,感情最是要好。
她掏出大半金银塞进春露的行李,哑着声对我说:「我顶了她的缺,她一定不想见我。冬雪,你把包裹拿给她吧!跟她说出去了也要好好过。」
可冷风如刀的傍晚,大夫人的嬷嬷就那么守着,把包裹里我们塞的钱都搜刮了个干净。
我只能拽着春露的手,用袖子遮掩着递过去一角银子,最后说一句:「春露姐,多保重。」
她拼命甩脱那些人抱了我,在我耳边轻而又轻地说:「帮帮我,帮我去找大爷,让他来救我。」
她说的时候,董癞子就在旁边,咧着一嘴黄牙,觊觎地看着她,大夫人把春露姐的卖身契给了他,他从此就是春露姐的男人。
我知道我不该管。可我们七岁来院里,一起度过十年光阴,那些互相庇护的往事冲散了我的理智。我守了三日,终于守到大爷。
就在我们院子外,就在他曾跟春露耳语过的廊桥下,他拦住夏荷,捏了一下她的手,笑着说:「好丫头,这副耳坠子给你,等进了院子,爷再好好疼你。」
一句话没说,我转了身。
是我痴了,只是个小玩意儿,谁会在意它叫春露还是夏荷。
4
秋霜是最早走的,她被指给柳管事。
我跟夏荷抬姨娘,只是穿身粉的摆桌酒,爷们是不可能出现的,但她却有完整的婚礼。
柳管事三代都在侯府,他爹也是得用的管事,早在外面置了屋子,我跟夏荷拿出毕生功力,给她绣了件龙凤呈祥的婚服,吹吹打打的唢呐声里,她进了那顶我注定上不了的花轿。
最后一刻,她拉着我的手落泪道:「自从你说你要当姨娘,我本打算这辈子再不跟你交心了,可不问这句我又不甘心。明明你从前跟我一样不屑争抢,怎么事到临头犯糊涂,做妾能得什么好?你看看春露姐。」
擦干她的泪,我笑了笑:「乖,新娘子要高高兴兴的,以后再同你讲。」
可我知道,我一辈子都不会告诉她是为了孩子,那是在往她心上扎钉子。
她素来傲气,老夫人院子里也平和,春露姐是最惨烈的一遭了,但我七岁就见过。
那年老夫人要人,进她院子的本不该是我,是她陪嫁丫鬟的小女儿,可大少爷看上小姑娘的姐姐做通房,她姐姐惧怕未来大夫人的名声不从,就那么全家被整治得发卖了出去。
从小陪着老夫人长大的丫鬟啊,跪下来求了又求,不及大少爷装病一场。
这些本不该小孩子知道的事,娘却把我搂在怀里,细细地讲给我听,她说:「小雪啊!哪怕现在你听不懂,也要记着,主子们的情分就那么一点,你要低着头做事,千万别扎进他们眼里,不然料理我们,一句话的事。」
后来她去世了,她教的道理我却牢牢记着,我不争不抢恨不得别人看不见我。
可我不愿再生一个跟我一样战战兢兢的小奴才了。
5
伺候二爷那天,是二夫人先见了我。
圆圆的脸蛋,很和气地对我说:「咱院子小,难为你是老夫人院里出来的还肯来,放宽心,以后就是一家人。」
我的心激动地要跳出来,忍不住抬头看她。
你看,她也是姨娘生的庶女,可她如今是官宦人家的正头娘子,等往后分了家,她还会成为老夫人那样的老太君。
她可以,我的女儿就可以。
我恭敬地伏在地上磕头:「谢谢夫人,往后奴婢一定一切都听您的。」
她扶起我:「都是一家人,就别自称奴婢了,往后我就叫你小雪。」
跟我娘称呼我一样,我突然有点莫名的心安。
见完夫人,就是长长的等待。
二爷一直到天黑透才进了我的屋子,憨厚的脸庞依旧憨厚,却从袖子里掏出一只钗道:「阿沅说你不能上花轿是一辈子的委屈,叫我送件东西哄哄你,我也不懂这些,你看看喜不喜欢?」
接过钗,我真心实意地欢喜道:「谢谢爷,妾喜欢,很喜欢。」
怎么能不喜欢呢?
会叫主君送东西给妾的主母,这么敬重主母的主君,我费尽心思挑的人,真的没有挑错。
6
做妾的日子各不相同。
我在二爷院子里依旧悄无声息地生活,他每月来两次,每次来都带着温和,却也只来两次。
白日里,除了给夫人请安,我都安静地在房间里绣花,偶尔也会假装路过花园,看小姐咯咯咯地撒欢。
夫人生了一儿一女,有慧小姐才两岁多,正是可爱的年纪。
但夏荷的妾却做得很高调。
大夫人仿佛要打那些说她善妒人的脸,金银珠宝,各色补品,不要钱一样往夏荷房里送。
大爷瞧着她的贤良劲,也放开了手脚折腾,一月有一半要宿在夏荷房里,这跟从前大不一样的景象,热闹得府里人人都在传。
她光景好,但能说话的人还是少,便有时来我这里坐坐,每次来,都带好东西,我推拒也要留下。
就是说的话越来越让人担心。
她问我:「冬雪,你后悔选了二爷吗?咱们都是同样的丫鬟,如今我的日子却比你好这么多。」
说这话时,她脸上带着隐秘的骄傲,好似自己做成功了什么了不得的大事。
可我还记得春露姐凄惨的样子,不安地劝她:「你收敛些,大夫人毕竟是夫人。」
她摸着肚子把头微微昂起:「那又怎样?我肚子里说不定就是大爷头一个儿子,做了长子,后头的福气谁也说不准。」
原来她怀孕了,若大夫人真的再不能生,的确是天大的福气。
可福气也要有命去享。
我又一次多管闲事道:「夏荷姐,你听我一声劝!我们做了妾,生的孩子就由不得自己,别生不该有的心思。想想春露姐,我不想再失去一个姐妹。」
提起春露姐,她的脸颤了颤,嘴上虽然仍硬道:「她总要顾忌着孩子将来恨她,她不敢的。」
可回去后,传到我耳朵里的风声却是她对大夫人更恭谨了。
大夫人也给她做足了面子,逢人就夸她好,说只要她生下儿子,就把卖身契还她,再去官府把她抬成贵妾。
贵妾跟丫鬟抬的姨娘不一样,那是好人家的闺女才有的待遇,即便做了妾,也能被当成半个人,主母都发卖不了。
我算着日子替她高兴,没想到临她生产,还有更高兴的。
7
大夫人叫了我去,春露也跪在里面,她难得和颜悦色地对我们说:「这胎对大爷很重要,听说春露在外面也学了些接生手段,你们是夏荷的好姐妹,便由你们陪着她在屋里生产吧。」
我低头应是,等到无人处,惊喜地打量着春露姐,搜遍全身,只恨自己只带了银耳环这点值钱东西,忙摘了塞给她。
她却不收道:「你也听大夫人说了,我做了稳婆,日子不愁过。董癞子对我不差,我如今收心跟他好好过,你看,连府里都肯请我,你就别操心了。」
我沉浸在姐妹团聚的那份情里,没看见夏荷瞧见春露姐的慌张,也没注意到春露姐那一瞬的恨意。
等产后那碗补药喂进夏荷的嘴里,等她口吐鲜血,止都止不住,我才知道发生了多荒唐的事。
春露姐指着夏荷,癫狂地骂道:「娼妇!叫你跟我抢大爷,叫你偷我的肚兜去大夫人那儿冤枉我!今日该生孩子的本来是我,你才该跟董癞子过!」
她撸起袖子,满臂都是伤痕,又哭又笑着:「我给他的酒里也下了药,你们去地下做对鬼夫妻吧!才配得上你们一起合谋算计我。」
那些疯言疯语里,我拼拼凑凑着知道,董癞子天天打她,她本已认命,可有一天那个混蛋喝醉酒说胡话,她才知道那些肚兜是夏荷,她最信任的妹妹偷出去的。
夏荷吐着血,也哭了,我便知道都是真的。
8
我跟春露姐一样恨,可我还是舍不得她死,我拼了命地叫,四处找人,可那些人就像抱着孩子消失了。
已经出气多进气少的人叫住我,连话都是断断续续的:「别……别找了,你还不懂吗?是夫人……夫人要我死,她怕孩子将来恨她,她得找人替她背这个锅。」
她复杂地看着春露姐,像辩解又像忏悔:「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既然……既然要做妾,自然求最好的去处,夫人来找我,说她绝不会让春露姐进院子,我不干,她就找别人干。
「大爷没有儿子,若我生了,将来他可能就是整个侯府的当家人,我心动啊,我怎么能不心动?
「可夫人明明答应我,她会给春露姐找个好管事,从董癞子出现开始,我就知道我会遭报应!好冬雪,姐姐求你最后一回,我活不成了,你把春露送出去吧!再晚,她、她也活不成了。」
七八月的暖阳天,我浑身冰凉地拽着春露姐往外走,我知道,我叫了十年的另一个姐姐,在我身后的屋子里等着咽气,可我一点办法也没有。
踏出门槛那步,传来她最后一声喊叫,她在喊:「春露姐,我还清了。我的儿,娘看不见你长大了,你要好好的,好好的啊!」
身边疯疯癫癫的人愣住了,抓住我的手用力得真疼,可我只能推着她往外走,往活路走。
没有人会比我们这些丫鬟更熟府里的小路。
趁着没人,我拖她到小门,摘下银耳环扔给她,用力把她推出去:「春露姐,忘了吧,恨也好,疼也好,我跟她都希望你活下去。」
我不敢看她的眼,只敢胡乱地往回走,走着走着,就像熬干了最后一滴心头血,扑通一声,栽倒在院子里。
9
再醒来,一切尘埃落定。
秋霜满眼是泪地坐在我床边:「若知道这是最后一面,我心里就是再别扭也会去,好好的四个姐妹,怎么就只剩了我们俩。」
大夫人为了把春露名正言顺地叫进府,说是姐妹陪着生夏荷更安心,也是叫了秋霜的,可秋霜自我们都选做妾起,就自动疏远了我们,这次也找了理由推脱。
我低下头,问道:「府里现在怎么说?」
「还能怎么说,当时院里接生的人全都作证,听见是夏荷先诬陷春露,才惹得春露报复。大夫人说大爷的孩子不能有这么不堪的生母,老夫人便做主,那个孩子从族谱上起就是大夫人生的,从此府里没有过夏荷,也没有过春露。谁再提,就直接打死。」
说完,她的泪掉得更凶了,往门口觑一眼没人,才小声咬牙道:「两个没出息的窝里横,临死都不知道该拖谁走,偏叫那个始作俑者还好好坐在高堂上。」
她从来都是这么聪慧敢说的性子,我却惊得去捂她的嘴:「无凭无据的事,你别胡说!」
大夫人早就做足了对夏荷好的姿态,再加上夏荷栽赃春露那一出,即便是那个孩子长大后听见什么风声去查,也没有人会怀疑大夫人才是布局的那个人。
夏荷从前说得对,大夫人怕孩子恨她,可这份怕没有叫她放过夏荷,反而把事做得更缜密,从一开始让夏荷去偷春露姐的肚兜,她就算好了要用这个把柄要夏荷的命。
否则那碗药怎么会等孩子生完了才有机会出现?否则当时院里的人怎么时机那么好,听完春露姐的控诉,等我找人求救却都不见了?
越想越怕,我盯着秋霜的眼嘱咐道:「记住了,刚刚那句话你没说过,从此有人试探地问你夏荷,你就往死里骂,骂她祸害了春露,小霜,是夏荷先做错了,你如今有了儿子,你想连累他吗?」
大夫人不能凭着怀疑就杀人,人死多了也是把柄、是蹊跷,只要外人以为我们也恨夏荷,那就能平安。
秋霜苦涩地笑了笑:「这有什么难?我本来就恨她,恨她脑子发昏,恨她背信弃义,恨她害苦了春露姐,可人真奇怪,她真死了,我的心又这么疼。」
到底我们都不是春露姐,没真的受过那些磋磨,总还留着一点无用的慈悲。
10
秋霜整理好眼泪,假装骂骂咧咧地走了。
她声响弄得很大,好叫别人知道我当时被吓傻了,也恨透了夏荷的恶毒。
可我知道还没有完,春露姐逃走了,大夫人肯定得来审我。
二夫人却叹息着进来道:「本来你有孕是件高兴的事,可现在府里乱糟糟的,也不能替你庆祝,好在老夫人体恤,不准那些人再来问你,免得你想起血腥场面再影响了胎儿。」
原来大夫刚刚来给我诊过脉,我竟也有孕了。
我被这消息砸晕在当场,好一会儿,才郑重地给夫人行礼道:「谢谢您,您真是个好人。」
我太了解老夫人,一定是二夫人当着人前提出要给我养胎,老夫人才顺势准的,她最怕别人说她刻薄庶子,面上功夫一向做得很好。
二夫人不似大夫人那般敲锣打鼓,她只是默默免了我的晨昏定省,还给我加了菜的份例,不惹眼,却很适合我养胎。
我的孩子,我比任何人都当心,也比任何人都避着大夫人院里的人,怀到六七个月,有经验的稳婆却说我该多走动,这样好生养,我才往花园多去了几趟。
去多了,难免碰上在那里玩的孩子。
大夫人抱着那个叫呈远的孩子,慈眉善目地逗弄着,事事妥帖,连手累了换给别人抱都舍不得。
我避在角落,默默地想,好歹夏荷有一件事心想事成了,她的儿子会很好很好。
11
我本以为这是能在花园碰见最大的事了。
可临生产前,我越发睡不着,晚上偶尔也忍不住一个人去逛逛,这一逛,就逛到有慧小姐偷偷在爬树摘桃子。
白日里我就听见她要上去,二夫人不许,她竟晚上一个人溜出来。
那么高的树,才三岁多的小娃娃摇摇晃晃地站在上面,我怕惊着她不敢喊,可梭巡遍园子,也看不见一个下人。
根本不容我思考,她那么直直地掉下来,我就那么下意识垫上去。
等我倒在地上剧烈地疼痛,小孩子终于知道怕,哇哇哭起来,才引来守夜的人救命。
染红的水一盆一盆端出去,二夫人把参片塞进我嘴里,握紧了我的手给我打气:「大夫说要不是你接的那一下,慧姐的腿就跛了,好小雪,只要你活下来,不论你要什么,我都答应你。」
血肉剥离身体的感觉叫我以为我快死了,想起花园里那个胖嘟嘟的孩子,我突然生了贪心,我没说这都是我该做的,而是回握住那只手说:
「夫人,我不为自己求,能碰见你跟爷已经是我的福气,我只求您一件事,无论今天我能不能活,求您,把这个孩子记在您名下吧!」
人心都是不足,本来只要是主子,庶的我也满足,可现在有了机会,我又想让肚子里这个前程更好。
看见夫人点头的一瞬,我的身体好似又有了力气,用力那么一挣,有婴儿呱呱坠地。
12
随有慧小姐的排行,二爷给孩子取名有仪。
大夫说我伤了根本,恐怕不会再有下一个,我有些失落,不能再给她生个弟弟庇护她。
可因祸得福,夫人待她更加上心,呈山少爷和有慧小姐也爱逗弄她。
她养在夫人屋里,我克制着不去看她,跟我这个亲生母亲接触越少,她的将来才能越好。
三个月大,夫人带着她一起来看我,不赞同地对我说:「自己亲生的女儿都不敢亲近,你是不放心我这个主母吗?
「你如今当了娘也该懂,那晚你救了有慧,就是救了我,我也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跟夫君都是庶出,我们懂姨娘的苦,你不必做成这样。」
我自然知道,当初我选二爷,就是图他们这份懂,所以定会善待庶子女,可我也知道,他们是真的恩爱夫妻,本不该有我。
夫人待我诚,我鼓起勇气问道:「看了三爷院里的情况,您真的没怕过,也没怨过我吗?」
从前大夫人不让大爷纳妾,二爷是自己不愿,三爷年纪小刚成亲,跟三夫人正是如胶似漆,三个院里都没外人。
老夫人塞人那一出,本以为大爷会最荒唐,可到最后,却是三爷尝到了甜头,一房一房往院子里纳人,三夫人没有大夫人的泼辣和家世,只能把苦水往肚子里吞。
她笑了:「做女人哪有不怕的?可再怕我也知道,能安我心的不是你,是我丈夫,他若想要,有没有你都一样。
更何况,这府里还有老夫人,我们这种人家,一房妾室都没有,该被戳脊梁骨的就是我,还是那句话,就算不塞你,也会塞别人。
我反而庆幸是你这样知进退又心善的,不然我的慧姐可怎么办。」
解了这个心结,我的愧疚少了一点,可我仍问道:「夫人,请您恕我僭越,你做姑娘时,羡慕过您的嫡姐吗?羡慕她有个出高门的母亲,不用听那些不中听的话。」
二夫人看着我,良久才叹了口气。
她懂了,我怕的从来不是她这个主母,而是我自己这个丫鬟出身的身份,会让我的有仪为我伤心。
羁绊越少,她为我伤的心就越少。
13
二爷不用再给我孩子傍身,来我房里便只需要聊天,我跟他们夫妻渐渐处成了亲人。
有仪小的时候真可爱,她以为我是夫人的妹妹,每次避不开相见的时候,都甜甜地叫我「姨姨」。
一岁,她把口水吐得到处都是,我给她做口巾。
三岁,她跟有慧小姐一样调皮,我悄悄缀在后面,连一眼都不敢错过。
四岁,她跟有慧小姐拌嘴在院子里哭,我不敢现身哄她,只能摘了多多的花瓣,让小丫鬟全撒在她头上,她由哭转笑,就像笑在了我心上。
六岁识字,七岁见女先生,一桩桩一件件,我都满心欢喜地帮她记着,我的有仪,跟有慧小姐长得一样好呢!
可八岁,她闯进我的小屋,红着眼问我:「雪姨娘,她们说你才是我亲娘,这是真的吗?」
有小丫鬟跟在她身后追进来,哭得凄惨道:「小姐,我胡说的,你别问了,让夫人知道,我就要被打死了。」
跟在小姐身边的同龄小丫鬟性子总会天真一点,她听父母嚼了两句舌根,就忍不住都倒给了有仪。
我慌得手脚都在抖,强装镇定地摇头:「三小姐您别拿我开玩笑了,您养在夫人院里,如何会是我生的?」
可我的桌上还放着绣桃花的帕子,那是她最爱的花样。
她气鼓鼓地瞪着我,再不说话,抓上那条帕子就跑了,我想追,却腿软得一步都挪不动。
还是夫人派人给我送的信,说有慧小姐正在劝她,只是那个小丫鬟,她怎么也不同意处罚或送走。
我揪心地等着,怕她闹,怕有心人传,怕我出身的印子打在她身上。
还好还好,最后是风平浪静地过去。
可我不敢再频繁地躲在暗处看她,日子一下,变得真难熬。
生辰那天,夫人为我置了桌酒席,她跟二爷要出府应酬不能来,伺候我的小丫鬟陪我喝了几杯,就醉酒被我打发回去睡了。
有仪就是这时候进来的,手上拿着一个卷轴,小脸依旧气鼓鼓的,走到我旁边,打开那个卷轴说:「先生最近在教我们写寿字,母亲说做人要勤俭。既写了,就送给你吧!」
她装作不在意,眼神却不自觉地流露出期待,期待我高兴。
其实根本不用这幅字,从她进屋那刻起,我就知道一切都是值得的,夫人把她教得真好,好到连我这样的亲娘她也认。
我忍不住抱紧她,她小声在我耳边抽泣道:「阿姐说你都是为了我好,只要在外人眼里我是跟着母亲长大的,哪怕知道我的身世,我的将来也比在你身边长大好。所以,我不能叫你娘吗?」
她的话让我的心都跳了一下,我担忧地拉开她上下打量:「怎么了,夫人对你不好吗?这不可能,她那么好的人。」
她低下头:「母亲当然好,她是世上最好的人,可我知道我跟阿姐不一样,她看我们的眼神不同就是不同。
「就像现在,就是你看我的这个眼神,你认不认,我都知道你是我娘。
「娘,我懂事的,我不当着人,你让我偷偷叫行不行?」
14
没有母亲可以执拗过孩子,从此每年生辰,都是我最盼望的日子。
但有仪十岁这年,秋霜罕见地来寻我。
这些年我们心里都希望对方好,面上却很少走动。
她几乎是跪下来求我:「小雪,你帮帮我,浩儿读书那么好,我不忍心他做一辈子下人。」
当初我不想钉在她心上的钉子,迟了十几年,还是自己钉了上去。
她的儿子柳浩七岁去族学上工,五年下来,竟把少爷们都背不下的书全背会了。
「我们本来没有痴心妄想他做读书人,可他每回见着书的眼神都亮得让我心酸,族学有位好心的先生悄悄告诉他,若他学下去,若他能去应考,将来中举的希望比府里所有少爷都大。
「他爹那里能走的门路都走过了,可到哪儿得到的都是一句『这府里,从不准人赎身』。」
秋霜抬头看我,像看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小雪,你在内宅,求你了!你帮我这一回!」
侯府最大的政敌就是几十年前从府里赎身出去的,从此,下人们除非被
文章转载自知乎,书名《悠悠杂感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