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下午,再也没有人聊天,甚至没有人到阳光明媚的院子里去站一下。整个房间内的空气,如同凝固了一样。杨伯涛不自觉地摁了一下胸口,如此反反复复的情绪变动,让他的心脏感觉到隐隐作痛。在此之前,他从来都没有想到过自己的健康问题,他觉得自己的岁数,自己的体格,都还不到思考健康的时候。可这两天,他老是想起早逝的父亲,怎么三十九岁的时候,说走了就走了呢,是得了什么不治之症吗?
杨伯涛想着心事,又不自觉地掏出那两盒香烟来,是侯吉珲购买的唯一一盒老炮台香烟,原本想回来让大伙一人一根过过瘾的,可没有想到,组长王伟杰再次强调了教导团的生活规矩,让他和侯吉珲再也不敢“装大”了。不过,杨伯涛狠了狠心,还是拆开了那盒香烟,又不自觉地想起了昨晚王伟杰捡拾烟屁股的场景,便抽出一根来,无声地让着趴在桌子前写字的王伟杰,王伟杰如同看到一条毒蛇一般,摇了摇手,又恶狠狠地瞪了杨伯涛一眼,那意思好象是在质问杨伯涛:“上午说的话,你当耳旁风了?”惹得杨伯涛倒像做了错事一般,又把那根烟塞了进去,无声地看着王元直的“纸上演兵”。

对于这个同事王元直,杨伯涛有一种说不清的感情,这个第18军的“插队户”,对于战术的研究,绝对是一流的,深得老长官方天、罗广文、胡琏等人的赏识,能以“半道”入主第18军而任嫡系第11师师长一职,足以说明了一切。而今天,对于战争已经极度厌倦,甚至不愿意再唤醒一下战场记忆的杨伯涛而言,感觉到王元直的研究,已经没有一点实际意义可言了,再好的战术,再好的装备,也已经挽救不了国民党覆亡的命运。纸上谈兵,又有何益处呢?
可令杨伯涛感觉到惶恐的是,他不知道自己能干些什么了,他猛然觉得,自己成了一只扔在冰面上的已经点燃了引信的炮仗,满腔的怒火,却只能在冰面上乱窜,等待着最后崩溃的时刻。然而,坐在王元直对面的吴绍周,似乎和杨伯涛的心情不大一样,他无声地看着王元直的图上作业,猛然说了一句:“重刚,我看了半天,我这个打法,全是美国人排兵布阵的方法,不能说不正确,但战场上的形势瞬息万变,他们这种打法,缺乏灵活性。况且,他们的步兵、炮兵、空军投入战场的比例、强度和我们都不一样,老是学他们那一套,未必实用啊。而共军,不,解放军针对我们的打法,也在不断地摸索对抗的办法吗。”
或许吴绍周的开口,让房间内又恢复了些生气,林伟俦和李学正也凑了过来,看着王元直的图纸,李学正看了半天,说道:“我怎么看,王师长画的都是塔山攻击战,当时,要是有这么多战车的话,或许……”
林伟俦用胳膊轻轻撞了李学正一下,王伟杰早已听到了李学正说的话,冷冷地说了一句:“李学正,这里没有王师长,只有战犯王元直。也没有塔山攻击战,那是针对解放军的屠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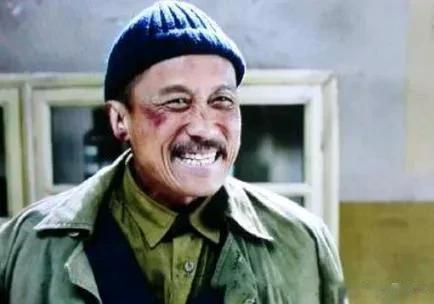
由于王伟杰的拦截,房间内再一次冷了下来,就在这个时候,一名年轻的解放军干部走了进来,众人急忙站立了。王伟杰兴奋而大声地报告道:“报告牛干事,我们第3小组共有9人,全部在此学习。邹玉亭的材料已经整理完备,请你过目。”报告完毕,从桌子上拿出邹玉亭交代的材料,恭恭敬敬地递给了那位牛干事。
牛干事略略看了一下,便笑了起来,说道:“天啊,这字体,也太好看了,老邹,你写的吗?”
邹玉亭摇了摇头,指了指侯吉珲,牛干事看了侯吉珲一眼,又笑了起来,说道:“我说呢,原来是侯吉珲,对吧?是个大学毕业的干部,好,等这两天安顿好了,我们请你给我们上上书法课,这字体,真是太好了,比报纸上的印刷体还好看。”
侯吉珲尴尬地笑了笑,说道:“过奖了,过奖了。有用的着的地方,侯某一定尽力。”
王伟杰刚要纠正侯吉珲的话,牛干事已经摇了摇手,说道:“老邹,不要有太多的想法,你的立功表现,天津市政府已经转给我们了。只是希望你配合我们,揪出大叛徒、大特务项迺光、袁晓轩来。好了,你的材料写得很好,我交给王区队长研究后,再和你谈。对了,你们中间,谁叫王元直啊?”
就站在他身边的王元直,立正站好了,说道:“报告牛干事,我叫王元直。”

牛干事笑了,说道:“不必那么严肃吗?王元直,你在商丘那边的表现,他们也已经出了证明,还向我们介绍说,你是个战车部队的专家。希望你整理出有关战车部队的资料来,给我们这些土八路干部上上课,开开眼界吗。我们的首长一再强调,土八路,不能就这样一直土下去,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仅要有强大的陆军,同样要建设强大的海军、空军、装甲部队等等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