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5年初,随着硝烟逐渐散去,一场决定未来世界格局的博弈在雅尔塔悄然上演。
没有枪炮、没有硝烟,只有三位大国领袖围坐桌前,彼此间用一言一语勾勒战后世界秩序,而在这场角力中,一个名叫“中国”的国家,成为争议的焦点。
此时的中国并不强大,刚从战火中艰难爬起,也不被看好,甚至被质疑是否配拥有全球事务的决策权。
就在众人质疑之际,美国总统罗斯福却力排众议,仅用一句话便让英国首相丘吉尔改口。

那一句话究竟是什么?而中国又为何能在战后成为世界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
密谈变数1945年2月,克里米亚半岛正在举行雅尔塔会议,在利瓦迪亚宫内,美、苏、英三国首脑围坐在壁炉前,世界的新秩序正在他们的谈判中缓缓浮现。
会议开始得并不热烈,讨论主题是如何处理德国的战后分区、组织未来的战争审判,以及成立一个能够调和各国矛盾、维持和平的世界性组织。

罗斯福将这个组织命名为“联合国”,一个不仅限于欧洲、不被殖民传统支配的全新国际架构。
在讨论到联合国的核心机构安全理事会时,罗斯福提出,他设想中的安理会需要拥有强有力的执行机构,必须由几个拥有强大军事与政治影响力的大国担任“常任理事”。
这原本没什么异议,美苏英三国自然在名单之列,让场面忽然紧张的是,罗斯福在接下来的发言中淡然说道。

“我认为,中国也应是理事会的永久成员,中国是抗击日本轴心国的东方支柱,他们不应该被排除在未来的世界秩序之外。”
这句话让丘吉尔变得警觉,在他看来,战后世界该由那些真正有实力、有影响、有殖民体系的国家来掌控,当时的中国无论从哪个层面来看,都不足以进入“核心圈”。
会议陷入了沉默,罗斯福知道,要打破僵局,他不能靠陈词滥调,而要用足够份量的筹码让对方心动。

事实上,这次“变数”的提出,并非罗斯福一时冲动,而是他酝酿已久的战略布局。
在他看来,战后的苏联必然成为美国最大的对手,而要在全球范围内构建一条围绕苏联的战略包围圈,亚洲也必须拥有一枚可以钳制苏联的“棋子”,中国恰好拥有这样的潜力。
“若不将中国列为永久成员国,你们考虑过后果吗,亚洲会怎么看我们,未来几十年我们想要稳定远东局势,还得靠谁?”

这一天的会议,以暂缓讨论草草收场,但变数已经悄然写入未来剧本,罗斯福已经将第一颗棋子落在了棋盘,他接下来的动作将决定这局博弈,最终是三国独裁还是五国共治。
各国盘算在雅尔塔会议的几日对峙中,表面上维持着大国间的“盟友姿态”,但实际上,彼此间暗流涌动,尤其是英国,对中国加入常任理事国这件事,心中波涛汹涌。

英国的疑虑并非空穴来风,作为昔日全球最庞大殖民帝国的掌舵者,一直习惯于俯视世界,用带着优越感的目光审视其他国家。
中国作为刚刚经历了八年抗战,尚未从战火废墟中重建的东方国家,突然要进入联合国的核心决策圈,无疑触碰了英国内心最敏感的神经。
原本他们已经默认“胜者联盟”将由美、苏、英三方主导,三边格局下,不管怎么博弈,每国都能保留一定的话语权。

可一旦中国也被拉入这个核心圈子,局势瞬间变成“四方共治”,再加上法国若也趁势而入,五边博弈的复杂程度将远超预期,英国在其中的影响力也必然被进一步稀释。
中国在英国人眼中并不是一个“可靠的同行者”,英国政坛乃至民间普遍认为,中国彼时的实力尚不足以与美苏英并列,议会中甚至有人冷嘲热讽。
“中国在战争中更多是在为生存而战,而不是为世界而战。”

英国还怀疑中国的“稳定性”,刚刚从日军铁蹄下挣扎而出,国内政权不稳,经济凋敝,把这样一个内忧外患的国家推上国际事务的最高决策台,是否会引发一系列的外交风险。
除了上述的战略考量,英国还有一层不便直说却挥之不去的忧虑,中国若一跃成为常任理事国,很可能直接影响到英国在远东的既得利益。
当时,香港仍是英国在亚洲的重要殖民据点,中国一旦成为常任理事国,将会在亚洲话语权中拥有“名正言顺”的地位,经济走向、外交联盟,甚至军事格局都可能绕不过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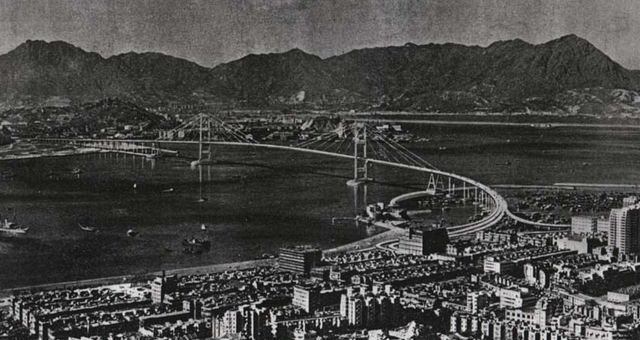
基于种种考量,英国的态度并不难理解,不过,时代的车轮已经驶向了新的轨道,不论英国是否愿意,一个来自东方的声音正在逐渐响亮。
丘吉尔当然明白,反对到底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项,若要接受中国入常,那得先拿到一些补偿,一些能“挽回面子”的代价,他也很快从罗斯福那里听到了。
罗斯福支持中国进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提议,这一“亲中”姿态背后,其实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算计与布局。

其一,美国看重的,从来不仅仅是中国这张牌,而是这张牌背后的“战略位置”。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尚未散尽之际,美国急于在战后的世界秩序中牢牢把持话语权,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地理上的特殊位置,显得尤为重要。
西接中亚、北临苏联、东临太平洋、南界东南亚,是天然的“地缘枢纽”,如果能让中国成为盟友,那么美国等于在亚洲部署了一道可以在未来制衡红色阵营的东方屏障。
其二,除了地理上的考量,美国也在利益层面看到了中国的“潜在价值”。

尽管那时的中国正处于一片废墟中,但庞大的人口基数与尚未开发的广阔市场,早已引起了美国企业家的浓厚兴趣,越来越多的商业巨头开始将目光投向东方。
如果能在制度上赋予中国更高的国际地位,美国便可名正言顺地介入中国事务,进行政治、经济乃至文化上的引导与渗透。
从政治保护到贸易倾斜,从军援计划到文化输出,这些都将成为美国扩展全球影响力的有效手段。

其三,尽管当时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存在诸多问题,但其意识形态和外交倾向明显更偏向西方,这样的中国,不仅“可控”而且“可塑”。
通过大量援助与密切合作,美国甚至认为自己有可能将这个古老国家重塑为一个亚洲版的“民主样板间”。
此外,美国还在为未来的“舆论战”储备道德资本,在构建联合国这套全新国际架构时,美国并不满足于单纯的实力博弈,更希望这是一场道义上的胜利。

美国必须为自己的主导权注入更多正义成分,中国的加入就成了最好的象征动作,既向世界展示了美国的“平等理念”,也为未来的外交斗争抢占了舆论高地。
在罗斯福的战略设想中,这一套连环布局一旦成形,中国不仅会成为对苏联的天然屏障,也将成为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多面工具”。
从这个角度看,美国当时的“亲中”,其实并不“浪漫”,更非出于善意,而是一次深思熟虑后的权衡博弈,是一枚暗藏刀锋的“橄榄枝”。
 一语点醒
一语点醒雅尔塔的风依旧冷峻,围绕中国是否应列入常任理事国的讨论,已持续了好几轮,面对丘吉尔的反对与斯大林的冷眼,罗斯福虽然保持温和语气,耐心也逐渐逼近极限。
“富兰克林,中国若进了这个圈子,我们原有的平衡就会被打破,他们的军队、工业、政局……一切都不够格。”
“温斯顿,我理解你的顾虑,但如果我提出,法国也加入常任理事国呢?”
“法国?”

丘吉尔喃喃重复,嘴角露出一丝意味难明的笑,那一刻,罗斯福知道,他的“诱饵”起效了,但这并非即兴之举,而是罗斯福早就准备好的替代方案。
当他意识到单凭中国一国之力难以攻破英苏的坚壳时,他便悄悄换了一张筹码——“利益再分一次”。
法国对英国而言,不只是昔日的盟友,更是可以用来平衡苏联扩张的“欧洲后盾”,在丘吉尔的眼中,法国拥有不可替代的地缘与历史价值,入局足以增强“西方阵营”的份量。

果不其然,丘吉尔很快作出了让步,对罗斯福来说,这便是胜利的信号,随后,他迅速捕捉战机,在会议记录中补充。
“我们将推动中国与法国同时担任常任理事国,这样不仅能体现联合国的全球性,也能确保东西方之间的平衡。”
这一策略可谓一石三鸟,既满足了美国扩大多边参与的设想,又顺利将中国推进局中,还借法国的“人情入局”,换取了英国的退让。

更妙的是,苏联虽然仍持保留意见,但面对两个西方盟友的共识,也不得不开始权衡自身立场的风险。
斯大林在这一阶段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谨慎,显然察觉到局势在悄然转向,如果他继续对抗西方的联合意志,那极有可能被孤立于联合国的创始核心之外。
“如果法国和中国都进来……那我们需要一些保障,至少,确保我们的边界不会因此变得脆弱。”
罗斯福没有继续施压,而是顺势而为,答应将在其他方面给予苏联“合理照顾”,比如在蒙古问题上的话语权,以及在东欧事务中的一定自由度。

就这样,三方最终达成共识,美、苏、英、中、法五国,共同构成新成立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成员。
外界并不知道,这个看似“顺利”的五国共治局面,其实是罗斯福利用一次“语言策略”完成的精密权谋。
他并没有在外交战场上大动干戈,而是在某个关口,用一句“让法国也加入”的提议,巧妙地拨动了对手心中最在意的那根弦,不仅点醒了丘吉尔,也最终改变了联合国的命运。

而这个世界,从那一刻起,便再也不只属于三个声音了。
【免责声明】:文章描述过程、图片都来源于网络,为提高可读性,细节可能存在润色,文中部分观点仅为个人看法,请理性阅读!如涉及版权或者人物侵权问题,请及时联系我们,我们将第一时间删除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