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十一年四月,四川夔关监督佛保向雍正帝呈递《归州巴东盐引请改拨川省行销疏》。此奏疏里,佛保着重指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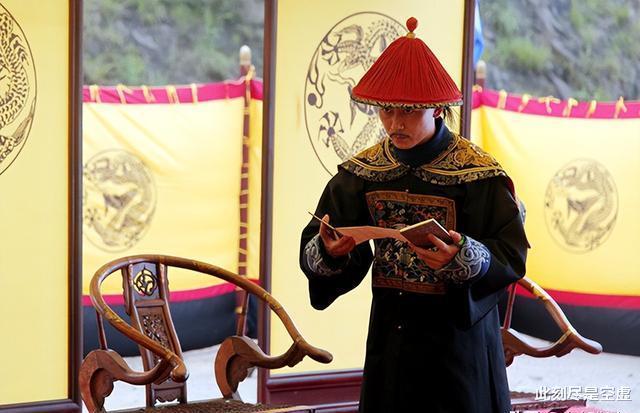
夔州府辖下云阳、大宁二县,素为食盐产地。其地距湖北仅一二百里之遥,且未存在越境售卖情形,故而导致盐货大量囤积。彼时,盐价极为低廉,每斤仅售四至五厘。为解此困境,不妨将归、巴两州县原应销售淮盐的额度,改作拨归川省进行报销与征课。如此举措,既能有效缓解夔州府属之盐积状况,又可确保归、巴两州县民众食盐供应无虞,免于淡食之忧。
此段内容传达出,云阳与大宁两县具备食盐产出能力,且当地盐价处于较低水平。然而,与之相距并不遥远的归州与巴东地区,民众却因种种因素,无力购置食盐。基于此困境,遂期望朝廷能够准许川盐向该两州县进行运销,从而有效化解当地百姓食盐获取困难这一问题。
佛保依据实际情形所呈递的建言,从合理性角度而言,具备充分的依据与可行性。然而,雍正帝却对此建言未予重视,未将其纳入决策考量范畴,采取了搁置的态度。
经御史详查,彼时云阳二县食盐价格为每斤五文,然而归、巴两州县的食盐价格竟飙升至每斤五十二文,二者相较,价差逾十倍之巨。不禁使人思索,缘何地域毗邻,食盐价格却呈现出如此显著的差异?

【根子出在盐销区上】
在历史长河中,食盐销售于各朝各代皆由国家垄断经营。至清代,其因袭明代旧制,施行专商引岸制度。该制度本质上是对全国食盐销售区域进行了明确的划分界定。
在清代,盐产区共计十一个。其具体涵盖长芦、山东、两淮、浙江、广东、福建、河东、陕甘、四川、云南以及奉天。各产区在当时的盐业生产与流通体系中,均占据一定地位,对国家经济与社会民生等方面产生着相应影响,共同构成清代盐业发展的重要格局。
此十一个盐产区所产食盐,各自对应特定的食盐销售区域。其中,长芦盐产区之盐,于直隶与河南地区销售;山东盐产区所产之盐,其销售范围涵盖山东、河南、江苏及安徽等地;而两淮盐产区的食盐,则在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以及河南等地区流通。
此类划分仅具概略性。就具体省份而言,通常存在数个各异的盐销区域。在此情形下,一省范围内会同时出现几种产自不同产区的食盐并行销售之局面。不仅如此,在某些府辖下的州县,亦可见来自不同盐销区的食盐流通。
盐销区一经划定,便确立起稳定的产销关联。在此框架下,盐商仅能于指定盐场采购食盐,并严格限定在特定区域内进行销售。任何逾越既定界限的行径,无论是盐商所为,抑或是涉事购盐民众,均会遭受严厉惩处。

从地域维度对盐销区进行划分,就理论层面而言,具备一定合理性。然而,在实际施行阶段,却滋生出诸多偏离正轨的状况。由此,衍生出诸如放弃临近产地而选择远距离供应,舍弃价格低廉的盐源转而采用高价盐源等现象。
以清代江苏镇江府而言,从地理区域划分视角,其隶属于两淮地区。然而,镇江府民众食盐的实际来源,却是浙江。在清代,食盐并非稀缺物资。据相关记载,乾隆时期,食盐年产量高达23亿斤,按人口平均计算,人均近8斤,呈现出明显的产能过剩态势。
食盐价格的主导因素,主要涵盖运输费用与人力成本这两个关键方面。以地理位置毗邻的扬州与镇江为例,扬州食盐价格为每斤十文,而与之仅一江之隔的镇江,食盐价格却高达每斤十八文。尽管两者之间存在价格差,但该差距尚处于民众可承受范畴之内,故而民众对此并未产生强烈异议。
归州与巴东两州县,面临的形势颇为严峻。依据相关规定,当地民众被强制要求采买两淮地区的食盐。需明确,两淮之地距湖北路途迢递,淮盐自仪征起运,入长江后溯流而上,运输过程成本高昂。

此情形致使两州县食盐价格持续处于高位。以乾隆初年物价水准为参照,彼时猪肉每斤仅二十余文,一石大米亦仅一两白银,而食盐却高达每斤五十二文,其价格差异可见一斑。
即便置于当下发达的经济环境,若一斤盐的价格竟等同于两斤猪肉,亦令人难以认同。更何况在清代,彼时社会经济尚处欠发达状态,如此盐价与肉价的比例,更是超乎常理,令人难以接受。
据文献记载,清代食盐价格居高位的地区为湖北、湖南、江西与贵州四省。于乾隆时期,此四地食盐价格区间大致处于四十文至五十余文。由此,当时“百姓淡食”的状况屡见不鲜。
从另一视角审视,部分产盐省份因食盐销售区域规模有限,致使食盐滞销。以川盐为例,依据市场运行规律,若将四川所产之盐销往湖北地区,其价格势必处于较低水平。
然而,彼时朝廷秉持僵化守旧之行事风格,于诸多政策举措上墨守既定成规,鲜少作出灵活变通。如此状况,致使资源分配严重失衡,呈现出极端分化之态势,部分地区资源极度匮乏,如同遭遇旱灾般陷入困厄;而部分地区却资源冗余,恰似遭遇涝灾般不堪重负。此局面无疑造成了国家资源的无端虚耗,着实令人惋惜。

【朝廷为何不重新划定盐销区?】
盐销区划分欠妥这一状况,自封建统治阶层的最高统治者皇帝,至各级臣僚,皆有所洞悉。然而,若欲对盐销区进行重新规划,则面临诸多棘手难题,实施过程举步维艰。
乾隆皇帝在位期间,曾发布一道内容详实的上谕。在此上谕之中,着重对重新划定食盐销售区域这一举措的不可行性展开论述。其不可行的缘由,主要涵盖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务必确保两淮地区盐课按照既定额度准时足额上缴。
在清代的国家财政体系中,财赋构成主要涵盖地丁、盐课、关税与杂税等类别。于诸项财赋之中,盐课占据相当比重,在乾隆中期,其数额已攀升至七百多万两白银。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两淮地区所承担的盐课,在全国盐课总量中独占鳌头,约达半数之多。
并非两淮地区食盐产量之高与行销范围之广成为其在盐政领域显著特征。实则,朝廷于赋税规划之时,在众多区域中,将两淮盐课的征收标准设定至最高水平。
据相关数据表明,在清朝中期,盐课银的征收标准在不同盐区呈现出显著差异。于两淮盐区,每引课银取值范围处于八钱至一两一钱之间;长芦盐区则为四钱至五钱;两浙盐区为一钱至四钱;四川盐区为二钱至三钱四分。

经对比分析可知,两淮地区的盐课定额在各盐销区中居于首位,其额度为其他盐销区的两倍乃至数倍之多。如相关文献所述:“淮盐课税相较于川盐,竟重逾十余倍。由此可见,淮盐每销售一分,所产生的课税,几乎足以等同于川盐销售二十分所上缴之税额。”
其二,盐销区域的重新划定,极有可能引发私盐猖獗的严峻局面。从历史经验来看,盐政管理中盐销区的调整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盐作为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其销售区域的变更,会打破原有相对稳定的市场格局与监管体系。一旦原有的盐销渠道和管控模式被改变,一些不法之徒便会瞅准其中漏洞,趁机大肆贩卖私盐,致使私盐在市场上大量涌现,扰乱正常的食盐市场秩序,进而对国家的税收及民众的食盐供应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乾隆于上谕之中,伊始便确认了食盐销售区域划分存在欠妥之处。此状况可表述为:若强制百姓摒弃价格低廉之盐、舍却距离较近之购盐途径,而选择价格高昂、路途遥远之地购盐,于情于理,皆有失公允。
然而,乾隆帝对此心存忧虑。在其认知中,对现行盐销区域进行变革,极有可能致使“民众受利益驱使,罔顾法纪,肆意逐利”,进而导致私盐猖獗泛滥。不仅如此,还会滋生引界争端,使官府在缉私工作上面临诸多棘手难题。鉴于此复杂形势,乾隆帝权衡利弊后,并未改变决策,而是选择维持既有格局。

从本质而言,清代盐征之所以弊端丛生,根源在于朝廷全然从自身利益出发,旨在维系盐课的固定收入数额,而对百姓所承受的困苦漠然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