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我来介绍潇水的写作,应该是一件非常违和的事情,因为近十几年以来,我一直在头秃地搞明朝的谷子,而潇水是一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人民作家。

《潇水讲三国》
但是潇水找到我,指定我宣传他、或辱蔑他,但不得不发声。我决定写,并不是因为我受到压力,一般我是不屈从于压力的。
作为一个在论文生产压力中恨不能提溜着自己头发逃离地球的学院派,我其实一直都鄙夷不能为建设和谐社会和美丽中国添砖加瓦的写作。
学院最近经常开展政治学习;回顾历史上的重大文艺路线,我也经常反思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文艺的普及与提高问题。我是从这个政治高度上去认识潇水的写作的。
潇水原本是一名先秦史写手。他的《青铜时代》曾被罗胖在“罗辑思维”上推介过。遗憾的是,由于全民风靡白话历史的热情已经过去,《青铜时代》未能获得《明朝那些事儿》那般的关注。
网络社区的明矾们屏息等待第六卷问世的前夜,我正在亚利桑那读博,与明谷子的第一个回合的缠斗快要结束了。当时有个还不赖的刊物约我给《明朝的那些事儿》写篇英文书评,正好我也需要从谷子中透口气,就写了一篇。
明月像他的传主一样崛起于畎亩之中,躬耕于天涯社区间,我十分羡慕、赞叹,或者应该说,我天生就是一个延座会精神的服膺者,喜欢一切能把复杂事情讲简单的文字,而非反之。
但由于我脑子里还是有些学院派的遗毒,加上约稿期刊也提出“要有建设性批评”,我好像也写了点“对历史演进机理还欠深度思考”之类的话,像一名浅薄的小学语文老师批作文。
我对明月是有点看法,但膏药没帖在疮上:明月后期的写作,不少地方像明代文献的今译,抻量着加上点搞笑逗趣;后期文字缺了裁剪和提炼。我见到就想,咦,这不是我在鼓捣的那点料吗?这段可能我也会写。

《明朝那些事儿》
后来我对明月感到很抱歉。抱歉的原因是因为把谷子抻到足够长之后,我发现长篇真的是很难驾驭,不是丢了芝麻就是丢了西瓜,要想要均匀地保持前后逻辑一致、行文腠理一致、语言风格一致,实在是个力气活儿。曹雪芹没有死,他只是写疲儿了化蝶为高鹗了。
再后来就读到潇水的五卷本《青铜时代》。他的各卷本命名法就挺稀罕的,分别为“蕨类战争”“蜥蜴战争”“鳄鱼战争”“恐龙战争”和“终结战争”,对应着先秦的五段时期。
从蕨类到恐龙的古生物学演进,寓意着上古民族从文明初化走向成熟的过程;战争的古生物载体,连接升级,直至最后战争终结,寓意着诸国武力争竞的升级,从春秋到战国到秦统一,最终以强秦独霸天下而收场。
读毕,我感到,潇水同志,是一位深刻领略了巴赫金精神的写手,他一直写到第五卷,仍保持着高水平的狂欢化品质。就凭这点,我对潇水就有着与对兰州拉面抻面师傅一样高的敬意。但书名《青铜时代》与王小波的名著重了,在命名法上很吃亏;在快读时代,这是一个灾难。《青铜时代》没打出更大的响动来,跟这个重名很有关系。
有个书评栏目注意到我评过草根写史,要我给潇水也来一篇。我写了,写得十分拧巴,一方面想到稿子毕竟作为史学书评——虽然探讨的是通俗写史——得有专业术语,另一方面考虑到所评文字具有娱乐性,在严肃紧张团结之外,我的也该有点小活泼,所以在炮制的过程中,水多了搁面、面多了搁水,好容易才撮成面团擀成皮,把《青铜》的馅儿包成了包子。

《青铜时代》
其中比较不近似人话的有以“取历史研究应具揭橥历史意义和历史运动趋向的学科价值的一面而言……”开头的一段,明显面疙瘩都还没活开;勉强包住馅儿可能还有点漏汤的比如这段:
在这个如尼尔·波兹曼所定义的“娱乐至死”的时代,“恶搞”文化是几乎为所有网文所共用的。它的产生原因很复杂,一种说法是本是出于对精英文化、经典话语权和宏大叙事的结构和挑战。
在白话历史写作上,则呈现为将原历史文本打碎、破坏,使原来的语境与寓意消解,揉入现代人的思维和话语,形成一种超现实的、常常引入喷饭的奇特效果。这种做法,与历史学科的求真性本是背道而驰的。
其后,我可着头做帽子,抛出了一个“如何写出一段狂欢的白话历史网文而不失历史作品的真实性?”的貌似深奥问题,但马上进入了对《左传》和潇文的大量转引,有点骗稿费之嫌。如今我不怕带着这个嫌疑再次转引,以证潇文之狂欢化特征:
潇水写过“楚囚” 钟仪的故事,而读书人都知道,它的出处在《左传•成公九年》。其原文本如此:

清光绪壬辰年宝善堂刻红印本《春秋左传》
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问之曰:“南冠而絷者,谁也?”有司对曰:“郑人所献楚囚也。”使税之。召而吊之。再拜稽首。问其族。对曰:“泠人也。”公曰:“能乐乎?”对曰:“先人之职官也,敢有二事?”使与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对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问之,对曰:“其为大子也,师、保奉之,以朝于婴齐而夕于侧也。不知其他。”公语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称先职,不背本也;乐操土风,不忘旧也;称大子,抑无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旧,信也;无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虽大,必济。君盍归之,使合晋、楚之成?”公从之,重为之礼,使归求成。
潇水将这段故事打碎重写,变成了以下这样:
晋景公视察战车库,瞥见胡子邋遢的钟仪,吓了一跳:“呔!是人是鬼?”对方没有动静。晋景公仗着胆子走近这个发霉了的东西细看,却是活人,卧在一堆白森森的老鼠骨头中间,衣服已经被老鼠或者他自己吃光了,惟(唯)独帽子还端坐在头上。我们知道,帽子对于春秋时代的古人,就像阿拉伯妇女的面纱,是身份的标志,不能摘的。当时不加冠的只有平民、小孩、夷人、罪犯和女同志。由于罪犯不冠,所以免冠表示谢罪,跟现代社会的脱帽致意差不多吧。
“你是什么人?”
“我是一名来自楚国的囚犯,名叫钟仪兮!”一口纯正的楚国话从这个人、鬼、兽的结合体传来。一年蹲监狱,寂寞将何言?他不但没变成哑巴或“白毛男”,居然兮兮地乡音未改。一年多来,他一直用尽浑身的黑暗想家,光着身子也要坚持戴故国的南冠(楚民族帽子),不忘本,不懈怠,为保住自己的民族帽子,跟老鼠们不知英勇搏斗了多少次,估计一年都没敢睡大觉。
晋景公让他演奏了一段儿楚国音乐,他唱起故国乡音,凄婉哀绝,闻者泣下数行。晋景公觉得这个“楚囚”钟仪的一举一动都慎守着故国礼仪,很有股子信仰,值得敬佩。于是就礼遇钟仪,把他当成一个守节不移的爱国模范来宣传推广,以教育本国的白眼狼卿大夫们(他们越来越有势力,不听君主的话了)。
而与此同时,战场上传来坏消息:楚共王奋起爹爹楚庄王遗威,北上解救晋人对郑国之围,攻服陈国,远袭山东莒国威胁齐人。并且晋国西线又遭受了秦军、白狄的联合骚扰。晋景公想一举击溃楚人,重新夺回被楚庄王时代抢走的中原霸权,已变得希望不大。于是,浑身不爽的晋景公只好先跟楚国妥协,把钟仪释放回去,以和平大使身份向楚国人民讲晋主席的好处。楚国响应了晋国的示好行为,双方谈判议和,并在在取得人质后晋国释放了扣押的亲楚派郑国国君。

《一读就上瘾的夏商周史》
潇水在这段改写中,强调了南冠不可摘的重要性——这对春秋时代的人是不言而喻的,故左传中没有对此进行阐发;添加了“不冠之人”的类别;在钟仪的对白中加入“兮”字以强化其楚国人身份并生成搞笑效果;加入了与老鼠斗争的想象情节;删掉了范文子其人其言;交代了晋国的困境形势和晋景公释放钟仪的动机。
他的改写,更动了原文结构,但符合历史的真实。我们不妨试想:换一个对晋楚争斗格局认知稍差的写手,在处理左传这个故事的时候,肯定会出于对经典的敬畏而不敢放开手进行增删,这段文字恐怕就会被写成像一段古文今译的样子。
古文今译而欲带有网文的狂欢搞笑性以吸引点击率,只能往里面生加佐料,这类网文见得多了,读者味蕾都会蜕化,掺入物压根儿不能被食道消化,只会让人觉得牙碜。
我因为这则书评认识了潇水。他是个喜欢听响动的人,自然欢迎我的“谬誉”;我觉得,他是真心欢迎一切打到经络上的赞美与侮辱,可能后者更甚。
我似乎确实有一些制造后者的生产力,但在鲁国的文史圈中完全施展不上;出过一册旧诗文小集后,我交了一批友人,他们都似对我蛮客气,我隐藏着我的生产力,对他们也蛮客气。

《家法:一位食货后学的政经法论稿》,刘晓艺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24年9月版。
过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我好像被当作一个维基在用:
“刘老师,《尚书今古文注疏》《逸周书校补注译》《大戴礼记解诂》《国语集解》《礼记训纂》《吕氏春秋注》《诸子集成》的英译为何?”
“刘老师,舜的继母的名字壬女的出处为何?”
我不时收到这样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我查查,能答,因为这些书名存在于我过去修课获得的知识结构里,查查是为了确认不错。
第二个问题答不了。我对于我在鲁国经常被当维基用这件事感到有点懊恼,因为一个知识点,如果我记得,我一定是能阐释的,但你并不需要我的阐释;如果我不能阐释,则我能搜到,你也应该能搜到。
我搜不到,其实问答就可以终止了,但因为潇水了解,所以我听到了有趣的诠释。他的上古史储备十分丰富,而且是与《论语》《孟子》《诗经》《尚书》对读得来的。所以,他不光是这类问题的维基,其阐释也有道道儿。
我一向以为,纯知识值不了几个钱,有价值的是阐释,在那之上是文采。两者都有叫受上苍祝福的笔。能阐释,就让人高看。他的口头表达与笔头一样强。
问舜继母问题的是位文化官员,他佐貳于一位更重要的官员,他们在致力于把舜打造成鲁国的文化IP。他们对舜在何处栖居过有深入的研究,相应地点设计了蓝图,蓝图里有舜酒店、舜餐饮、舜娱乐城的系列推出。当然,我现在还没见到它们盖起来。

《先秦凶猛》
潇水本名张守春,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留学于新泽西州立大学,正职是人力资源管理。我猜想,在他十三不靠的专业、写作和本职之间,一定有些什么会通,因为上古史中有大段的空白,在没有材料的地方,写作者要动用他对社会组织、人际和心理的认识,拼接起来。
潇水从事人力资源,这大概有利于他练成一种看人事死角的视线。但他于真正的、尘世的人事持有一种嵇康式的抽离,“纵逸来久,情意傲散,简与礼相背,懒与慢相成”,如果不是为了钱,他连上班打卡都懒得打。人读书多了会有一个自我从头顶冒出来,在上面漂浮着、闲闲看着自己的肉身与社会。
潇水好像练成了此功,我还没有。但是他与出版社常年吵架,就像嵇康见谁都懒得说话但跟山涛实磕,因为编辑动他的文字。《青铜》两次要再版,印量5万起,都因为他坚持不能大动文字而丢了合同。在这类事上我也反感编辑的主观能动性,这年头很少有作者的风格不被他们削没的。作者的风格是个面团的话,他们一定要把这个团儿削成面叶子才罢休。

《秦殇:谁杀死了秦帝国》
我们共同认为写小说比写史要难。因为史有框架,史的最终结果业已发生,阶段性结果也都还算清楚,就算对其中的细节不完全把握,照着摹不会摹飞了;小说就不同,每一个人物的每一句语言、每一个动作都构成场域,都必须与另外人物的每一句语言、每一个动作进行互动,而互动必须是合理的。在这个层面上我们的认知大体一致。分歧在于具体的部头。
我仅承认《红楼梦》《金瓶梅》《醒世姻缘传》三部长篇小说的伟大,而他并不熟后两部。看在我与明谷子纠缠的份儿上去翻了翻《醒世姻缘传》,像鲁迅一样读不下去,但承认其伟大。我说过对其他部头的看法,他很赞赏。
我的观点是:《水浒传》《儒林外史》,都取巧地使用了人物情境的转递,规避了宏大场域的互动;而《西游记》《镜花缘》,则取巧地通过地理情境的转递,规避了宏大场域的互动。它们没有死磕过虚拟写作的真正硬骨头,被归为二流,宜哉。
“你怎么看《三国演义》?”他问。他会关注这个问题,也宜哉。
潇水与“得到”签了约写三国,缘起还是因为罗振宇认可他的白话写史。此前他已经写过一部《真三国不演义》,80万字,是基于《三国志》的对《三国演义》的纠偏之作,取消了《三国演义》里所有的杜撰,加上了独属《三国志》的情节和人物。
Again,临付梓前,他与编辑吵架,把合作吵黄了。他自己掏钱找出版社印了一些,送了我一套;我因为进入了新一轮的明谷子,没有时间细看。无论志还是演义我本来都不咋爱看。但略翻翻就知道,写出此书需要有对二著的极大熟悉。
我当然不认为志或演义中的任何一种高于我所认同的三种,但也承认历史叙事之难。刘知几谓“善叙事”是良史必备的能力与素质。他说的是一种裁剪功夫。史家必须将在多维中发生的历史事件和多维中存在的历史因果硬挤到一条线之内。

《卢奇安对话集》
古希腊学者卢奇安﹙Lucians)谓历史叙事应有“真实之美”“秩序之美”与“文字表述之美”。对付三国这样复杂的时代、事件和人物群落,如果叙事还没让读者晕掉,则作者已经是伟大的,因为他实现了“秩序之美”。
我扯得有点远,一不小心暴露出祭獭鱼本色,好在提问方是谅解的。
“全国那么多人做三国,易中天啊谁的,他们得有多瞎,非得找你做呢?而且我实在是不明白选题意义何在,”似被“选题”二字激活什么黑暗元素,我的音调高了起来,并且冒出了行业黑话,“一个选题只有两种情况下值得做:1、前人没有研究过;2、前人研究过但是出于各种原因没有研究到位。”
潇水的回答倒是很流利,比我听过的多数开题答辩过硬,其逻辑流是这样的:

《潇水演义真三国》
用一句最老生常谈的话,《三国演义》不但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它是世界了解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媒介。《三国演义》这部名著就是这样,它弘扬了历史,又通过虚构改变了历史认知。它影响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三国时代是中国五千年文明的一个分水岭,这前后的历史和文化,都由《三国演义》棱镜般折射而出。棱镜的折射,有光和角度的曲折,不可一一看实,然亦不可将其看虚。要把握这个时段,绝非仅仅掌握东汉末年和三国那有限的近百年即可的。
在此之前的先秦时代和秦汉时代,即中华文化的上古和中古,传给我们后世的,是经和史。所谓经书,就是春秋战国时代相继成书的《论语》《孟子》《诗经》《尚书》,它们是中国文明的思想源泉,是贵族精神与平民哲学的智慧互动结晶,至今仍支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善恶原则。
《三国演义》所塑造的核心人物,分别就是这些善恶价值观的符号性代表。其书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呈现这批符号。换句话说,《三国演义》有着与经书同样的载道的作用,而且更为贴近人民的阅读需求。
读了刘备、曹操、关羽、诸葛亮这些人物的故事,人民就懂得了仁、义、贤、智这些核心经学要素。《三国演义》通过虚构,突出刻画了刘备、关羽、诸葛亮、赵云等人,生动具化了经学中原本抽象的概念,从而塑造了国人的思想观念。所以,讲透三国演义,是件有意义的事情。一个在现代社会里长大的普通中国人,通过阅读《三国演义》,可以快速地了解本国文化的前生今世,对于理解“我和我的祖国”,是大有益处的。
我当时没有想到的是,潇水也需要给“得到”交选题报告,自然用心准备了一番。他流利的答辩很学院、很正规,里面有驳不倒的逻辑,尤其是还涉及到国族的崇高叙事。

《真三国·不演义》
学院派的弱点是一见到自洽的崇高叙事就感动,可以连报酬都不谈。舜那哥们儿给过我信息费吗?没有嘛;他找舜的继母干啥,给我提供过上下文吗?使我感到过叙事自洽了吗?也没有。我还不是照样把潇水提供的信息第一时间转给了他?
那仅仅是在乡邦史层面上!潇水加码,转述了王国维语录:“一国人的性格志趣,是和他们接触的历史的深度有关。”这当然就点了我死穴。我表示无条件支持。他预约我写篇推荐语。
没过多久他把书和节目都做出来了,的确是快手。他希望我如约出推荐语,要惊悚一点的。于是我提笔写了一个开头,带着我所隶属的二级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独有的气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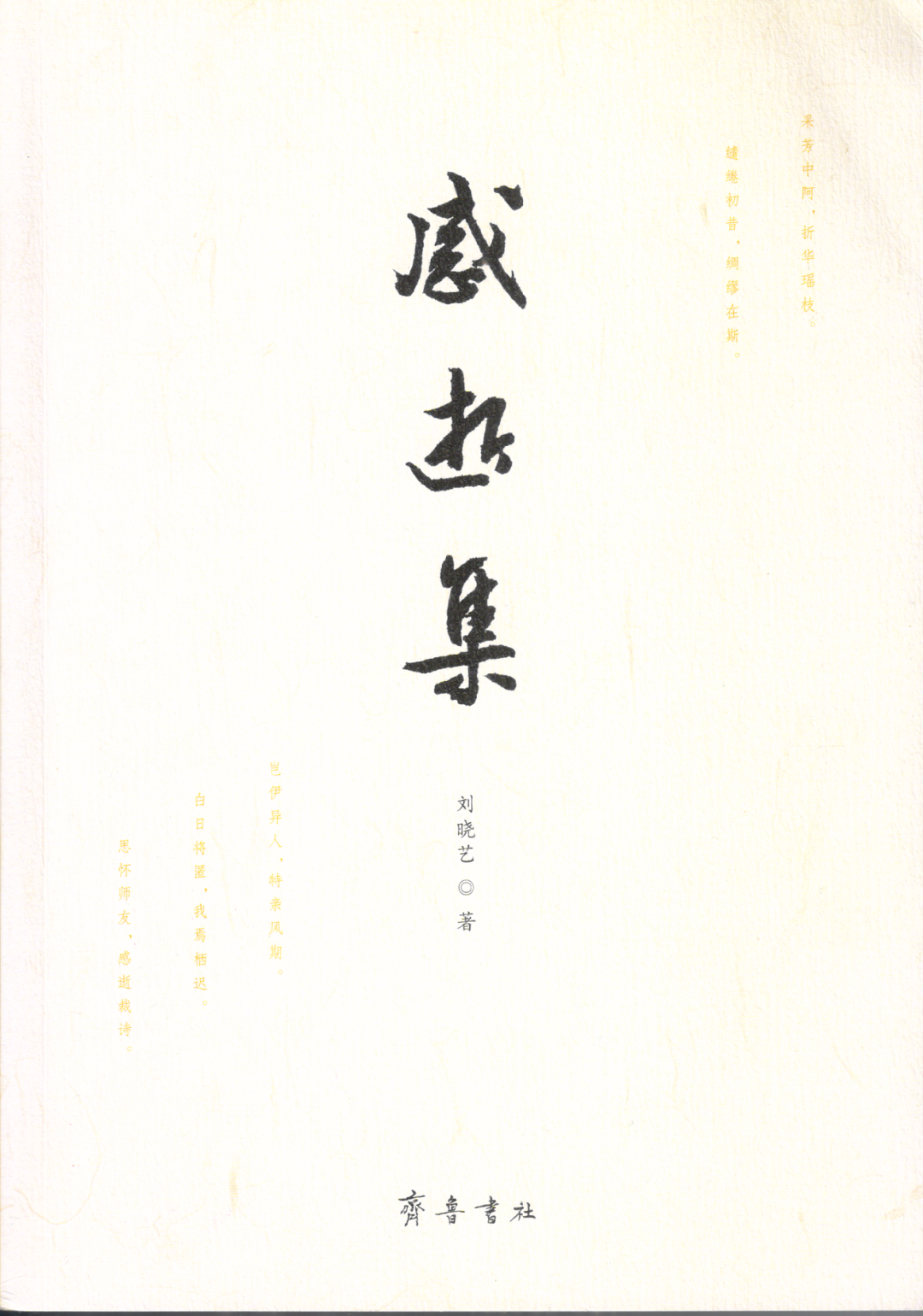
《感逝集》,刘晓艺著,齐鲁书社2024年10月版。
读三国,不读三国,这是个问题。尤其是,《潇水讲透三国演义》出版了,作为读者的你,难免要陷入这个哈姆雷特之问。
他很不满意。NG了。于是我援笔又写了一个:
不论后现代史家如何反对线性历史,在历史书写的问题上,若没有时间线……爱德华·吉本称之为“时间的秩序,那不可能出错的真实性的试金石”……的话,文本绝对会是一场灾难。潇水携其先秦史积淀,复来凿说《三国演义》,这就形成了某种垂直打击的优势……这正是其他的《三国演义》评说者所不具备的。
就是在这个节点上,潇水批评教育了我:
一个不能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人,写得越多,就越祸害树,你知道吗?像你这样一个不上不下、出版过一批无毒无害的谷子但群众也并不喜闻乐见的作者,可谓“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你需要在延座会理论的正确导向下,逐渐摆脱机械论文观、机械著述观,虽然一时还达不到“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境界,最起码应该有“不再糟蹋树”的觉悟吧。
惊悚的效果达到了。我十分惊悚。我惭愧地说,最近这段日子,我数了数年终的核定工作量,还差两篇CSSCI——其实也写差不多了,而且有C刊编辑表示感冒。我可不可以等写完这两篇之后,再告别对树的浩劫生涯、回归作树的朋友呢?

《昔在集》,刘晓艺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7月版。
潇水说,以我的明谷子对生态造成的破坏,现在再不起而行之就晚了。如果我肯宣传他、或辱蔑他,让他为更多人所知、所阅读,本质上就是一种tree-friendly的行动,因为他的读者都不买他的正版书。群众看了他的书,不就没空看那些假大空了;而他的书又不费树,这是不是双倍的环保?这是不是双重地减少碳排放?这是不是可以双重地赎回我以前写谷子对树造成的浩劫?
我想了想,也是这个理儿,于是就把两篇C刊搁置了。在两家编辑和我之间,也说不清谁鸽了谁;比较清楚的是,缺了两篇C刊,后来我的年度奖金在院里遥遥领低,至今也没地儿索赔去……此为后话。
再后来呢,我就确实写了一篇推荐语。以上就是我为潇水写推荐语的来龙去脉。不抄了,过录为单篇,免得像骗稿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