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03年十二月,东晋权臣桓玄在清洗了东晋宗室实权派与北府老将之后,终于篡晋自立,建立了所谓“楚朝”,史称桓楚。然而桓楚建立了才两个月,北府少壮派将领刘裕便在京口召集同乡故旧发动兵变,起事反桓,然后一鼓作气,攻入建康,赶走了桓玄,恢复了晋朝的江山。
404年三月初三,京口起事后仅仅第五天,胜利者刘裕领军进驻石头城要塞,宣布恢复晋朝并成立“留台”也就是留守京师临时政府。然后代表留台,做出以下决议:
第一,烧毁桓温列祖列宗的神主,重新为晋朝诸先帝制作灵位,纳于太庙。
第二,遣刘毅、何无忌、刘道规等诸将准备船只,即日出发追击西逃的桓楚皇帝桓玄。
第三,以尚书王嘏负责主持迎奉晋安帝司马德宗回京复位诸事宜。当然,如今司马德宗还在忠于桓玄的江州刺史郭昶之的手里,这件事情还得先军事开路,再从长计议。
第四,诛杀来不及逃离京城的所有桓家子弟,完全清楚桓家在下游的势力。
第五,派大舅哥臧熹入宫,收图书、器物、金宝,封闭府库,严加看管,禁止任何人包括建义军将功勋们染指私吞,以待安帝回归。

安排完这些大事之后,接下来就该讨论新政府的人事问题了。按道理,再造大晋的最大功臣是刘裕,其次是刘毅何无忌等举义京口诸君,大家在没有任何武装和门第可以倚仗的情况下,凭着一腔热血与缜密的筹划,居然在五天之内就驱逐了强大的桓楚皇帝。这就让建康百官与门阀士族们“时失民望,莫不愧而惮焉”(失去了执政的民意基础,一个个都相当惭愧恐惧)。特别是当前朝廷最高官员司徒王谧,在桓玄刚得势时就倒向了这个叛逆,甚至曾亲夺安帝的玺绶献给桓玄,而群臣也都曾去到姑孰向桓玄劝进,如果要论罪的话,这岂不都是附逆的大罪?所以王谧等朝廷高官商量了一下,要联名推荐刘裕为扬州刺史。东晋的都城建康位于扬州,经济与人口基础三吴之地也在扬州(注1),一般来说,谁成为扬州刺史谁就相当于东晋帝国的实际的掌权人了(注2),王谧等人此举,其实就是要献出权位来给自己买命。
然而刘裕拒绝了,他倒不是不想放过朝廷百官,而是想要和这群门阀士族们更好地合作。桓玄虽然被赶走了,但那是因为桓家在下游缺乏根基,如今他回到上游,仍是建康最大的威胁,桓氏家族在荆州经营多年,根基深不可测,可以说,真正的恶战现在才刚刚开始。
所以,刘裕决定暂时放弃与建康高门争夺权位,并充分释放团结与和解的信号,以此来争取士族的合作与资源,这样才能彻底打败桓玄,为国家带来真正的统一与安定。
于是,刘裕坚决辞谢了扬州刺史之职,并推戴王谧为侍中、领司徒、扬州刺史、录尚书事,让王谧做了这个临时政府的首脑。然后,王谧便以主政之名,任命刘裕为使持节、都督扬、徐、兖、豫、青、冀、幽、并八州诸军事、领军将军(注3)、徐州刺史。也就是说,刘裕从四品建武将军,升为二品持节都督,全面主管下游诸州军事,并兼领徐州政务与禁军之一军。另外其他举义诸将,刘毅为青州刺史,何无忌为琅邪内史,孟昶为丹杨尹,刘道规为义昌太守。以此为象征,东晋的门阀政治进入终场,南朝的军人时代到来了。正如川胜义雄所言:“在四世纪(刘牢之时代),军队说到底不过是贵族政权的佣兵,然而五世纪(刘裕时代)时已发展到由军人来掌握政权了。”(注4)

而王谧作为“尽心伏事”桓玄的楚朝元勋,本来应被视为大晋逆臣而予以严惩,如今却在刘裕的推戴下摇身一变成了大晋宰相。如此,王谧便与刘裕深度绑定,成了刘裕集团的士族代言人,当初他营救刘裕的三万“投资”,如今收到了千百倍的政治回报(注5)。
和王谧相比,刘裕的另一个老相识,豫州刺史刁逵就惨了。几天前诸葛长民在历阳举事失败,被刁逵抓住押送建康。谁知囚车才刚走出历阳,就传出桓玄已经败亡的消息。押送诸葛长民的卫兵立刻明白这苍茫天下谁主沉浮了,于是打破枷锁放出诸葛长民,还攻历阳。刁逵一看情况不妙,赶紧弃城逃跑,可也跑不了,被部下抓获。这回轮到刁刺史被囚车押解建康了。到了石头城,刘裕想起刁逵多年作恶又附逆桓玄,实在罪无可赦,于是下令除刁逵年幼的弟弟刁聘之外,其余刁氏男性成员全部处死。刘裕与王谧商量之后,以魏咏之为四品建威将军、豫州刺史,镇历阳,诸葛长民为三品辅国将军、宣城内史。

另外,鉴于晋帝司马德宗还在桓玄手里短时间内肯定回不来,刘裕和王谧商量还是要找一个司马宗室来做朝廷象征。当时刚好有一位反桓志士武陵王司马遵,本来被贬为彭泽侯要押送到江州去,但适逢水灾冲毁了船而滞留京师。刘裕等人便宣称受晋安帝密诏,命武陵王遵为大将军,承制总百官行事。接着又宣布除了桓玄一族,大赦天下。
当然,无论王谧还是司马遵,都只是临时政府的门面招牌;真正踏踏实实在做实事的,还是刘裕的主簿刘穆之。经过近一百年腐朽的门阀政治,如今这个国家已经是“晋政宽弛,纲纪不立,豪族陵纵,小民穷蹙”,门阀官员们不仅上班吊儿郎当(注6),犯了罪也得不到应有惩罚(注7),仍旧作威作福,霸占资源,欺凌百姓,更搞得朝廷税收都成问题。桓玄一度想要搞改革,但这公子哥是王莽作风,出来的政策不仅“科条繁密,众莫之从”,且执行下来仍是东晋“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那一套。对此,刘穆之的策略是“斟酌时宜,随方矫正”,既灵活又严格,而刘裕本人也以身作则,坚决执行改革方案,以军人之绝佳意志力,其方建大功的威严、领导政府打好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门阀们本来在刘裕等寒族军人面前是高人一等的,但偏偏他们此前加入了桓玄朝廷,在法理上都是附逆之臣,所以一下子失去了政治高度,只能乖乖听刘裕的话。当然,还有一些死硬分子不肯就范,结果刚好撞在了刘裕的枪口上。比如光禄勋卞承之、左卫将军褚粲、游击将军司马秀等人擅自把百姓变成私家奴仆,被御史中丞纠察上报朝廷。这几位都是宗室、外戚和宠臣,自以为没人治得了自己,态度十分强硬,不仅谢笺上言辞怨愤,还天天去有关部门闹事骂街,刘裕大怒,宣布将三人免官。太原王氏对刘裕等军人主政亦非常不满,对其改革更是深恶痛绝,遂密谋发动叛乱,结果消息泄露,尚书左仆射王愉父子全家十余人皆被斩。加上前面王国宝、王恭的两次惨败被族诛,自魏晋以来“八叶继轨,轩冕莫与为比焉”的太原王氏,在南方几乎被灭族(注8)。朝廷百官看到刘裕动了真格的,不由“肃然奉职,不盈旬日,风俗顿改”。

流亡在南燕的北府将刘敬宣、高雅之以及司马休之等人也没有闲着,他们打算在南燕起兵推翻鲜卑慕容的统治,归附东晋。但同来的刘轨已被慕容氏任命为司空,坐享高官厚禄,而且年纪也大了不想折腾了,结果密谋泄露,刘轨高雅之都被鲜卑人所杀。刘敬宣和司马休之则逃到淮泗一带,听说刘裕等人已举兵击败桓玄克复建康,于是回归东晋,受到刘裕热烈欢迎,刘敬宣重新被任命为辅国将军、晋陵太守,袭封父爵武冈县男。司马休之是宗室,自然地位要更高一些,任荆州刺史、监荆益梁宁秦雍六州军事、领护南蛮校尉。当时荆州还在桓玄手里,之所以提前给司马休之这个职位,因为北府诸将已经在准备西征上游了。
注1:史书上没有记载东晋人口的统计数字,但按《宋书》记载公元464年刘宋的人口统计数字,扬州编户人口总数为1605694(不包括庄园依附民),占刘宋编户总人口的27.4%。刘宋北伐之后领土比东晋多了淮北地区,故东晋时扬州人口占比应该更大。
注2:如东晋的王导、谢安、司马道子、司马元显,还有桓楚的桓谦都是以扬州刺史为宰相。刘宋永初年间,针对扬州刺史刘义真的朝堂班次问题,中书令傅亮亦认为:“扬州自应著刺史服耳。然谓坐起班次,应在朝堂诸官上,不应依官次坐下。”(《宋书·蔡廓传》)
注3:领军将军本是建康禁卫军六军将军之首,《宋书·百官志》称其“掌内军”,即统禁省之兵,但自刘裕担任此职后,领军将军便增加了权力,可预问政治,实际成了宰相。后来宋少帝即位,谢晦便以领军将军之职“辅政”;宋明帝死时,刘勔亦以领军将军“受顾命”。所谓“辅政”,“受顾命”,即都是宰相。《宋书·沈演之传》载宋文帝曾对沈演之说:“侍中、领、卫,望实优显,此盖宰相便坐,卿其勉之。”当时刘毅亦升任护军将军(《晋书·王谧传》云“护军将军刘毅尝问谧曰”),其实也是宰相,与刘裕的地位相差不多,时人称之为“亚相”。
注4:川胜义雄:《魏晋南北朝》,九州出版社,2022年,第208页。
注5:甚至也遗泽了他的子孙。王谧死后,其子王球常常自恃身份而以清高自期,他当过中书令、尚书仆射等要职,却屡屡称病不上班,录尚书事江夏王刘义恭要“以法纠之”,宋文帝却称他“时望所归”,“遂见优容”。就算是王球的侄子王履跟随权臣刘湛犯下谋逆死罪,事发后吓得光脚大哭,王球也就一句“阿父在,汝亦何忧”,结果还真让宋文帝赦免了王履。宋文帝日理万机,当时群臣奉诏进见,等个十几天都是常事,只有王球遇上这种情况立刻离去,从来不肯停下来等待召见。
注6:这些高门士族本来也就没有行政能力,甚至以不干实事、照例署名为“清贵”,而那些需要“恪勤匪懈”的工作,则相当“鄙俗”,是留给下贱人干的(杜佑《通典·职官三》)。东晋的一个官员熊远亦在奏章中描写过当时的士族风气:“当官者以理事为俗吏,奉法为苛刻,尽礼为谄谀,从容为高妙,放荡为达士,骄蹇为简雅。”(《晋书·熊远传》)事实上,正因为实际行政能力不行,高门子弟们才高倡玄学风尚,从而避免将自己与寒族官员放在一个考核标准上。在这个标准下,寒族的无能是无能,他们的无能就变成了高贵风雅。比如,晋明帝的女婿、丹阳尹刘惔死后诔文曰:“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却居然被当时士人赞称“为政清整”,并“以为名言”(《晋书·刘惔传》)。
注7:东晋门阀当国,实行“镇之以静”方针,对官僚尽意宽纵优容,把“宁使网漏吞舟,不必察察为政”奉为指南(《世说新语·规箴》载顾和评王导)。监察制度,也往往是宪纲具在而形同虚文。参阅阎步克:《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41页。即便是门阀中对法家颇为留意的桓温,对犯罪官员的杖罚之法制也订得较轻,行杖往往只是做样子,被描述为“上捎云根,下拂地足”,“正从朱衣上过”。意思是装腔作势不真打,高高举起、轻轻落下,只从衣服上擦过而已。但就这样,桓温还表示“我犹患其重” (《世说新语·政事》)。而《晋律》中亦有八议(八种特殊人物的法律特权)以上,皆免官收赎,“勿髡钳、笞”;免官者,“比三岁刑”的条款。另据《宋书·王韶之传》载东晋官吏休假制度云:“伏寻旧制,群臣家有情事,听并急六十日。太元中改制,年赐假百日。又居在千里外,听并请来年限,合为二百日。”如此宽松的官员休假制度,在史书上也是罕见。
注8:只有王愉之孙王慧龙逃到北魏,得到崔浩赏识,从而与北方大族广泛联姻,并因此在孝文帝时发展为顶级豪门,名列“五姓七望”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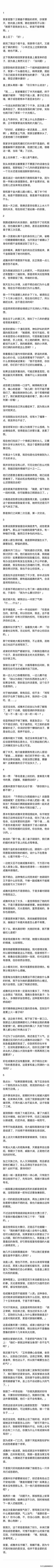

刘裕是位军事和政治全面的出色君主![点赞][点赞][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