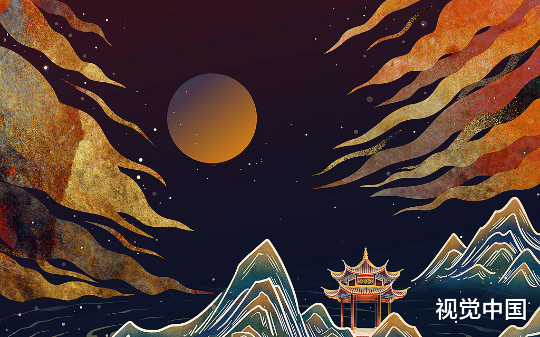春日宴上,素未谋面的太子殿下对我深情灼灼,胡言乱语,“封妜,这一世,我不会再放开你了。”
自此,太子的礼物流水般送到我屋里。
在我躲他的第五次,他将我堵在死胡同里,眼尾见红,“妜儿,你相信前世今生吗?”
我恼羞成怒,当场拒绝了他的爱慕之情,并且狠狠踩了他一脚。
原以为他会就此罢手。
可马球赛场,他明明不擅御术,却倾尽全力赢得博彩送给我,只因那彩头是我久久求而不得的焦尾琴。
端阳狩猎,我险些毙命,他将我从利箭前救下,眼底满是担忧与后怕。
直到我为躲他去滇南外祖家,看到我与表兄挚友相谈甚欢,他立马红了眼,将我围困在方寸之地,满眼偏执,“封妜,别忘了,你的命是我救下的,不许想沈常若,你只能想我。”
“这辈子,你的夫君只能是我。”
1
皇后举办春日宴,给京城各个贵胄女眷都发了拜贴。
以往这种事,都是身为太傅嫡长女的阿姊出面应付,可这次,阿姊却硬要拉上我一同前去。
“这次春日宴是在骊山举办,听闻那里的温泉极养人,你大病初愈,正好去去病气。”
阿姊见我无动于衷,立即上前夺了我手中的笔,“阿姊,我还没写完呢。”
“你每日都待在屋里,不是看书就是写字,再这般下去,都快成书呆子了。”
说完,就推着我进了里屋,为我挑选衣裙首饰。
我是个极不爱出门的人,阿姊常说,就因为我这个不爱动的性子,外头都鲜少人知道太子太傅家还有一个嫡幺女。
可我并不在乎,如今家里衣食不愁,就算我一辈子不出门,家里也委屈不了我。
不情不愿地随阿姊去了骊山,不曾想刚落脚就遇见了当今太子魏斟,那位传闻中风光霁月的男子。
常听阿姊说,太子魏斟才学斐然,性格温和,又长得十分俊朗,是陛下最器重之人,出于好奇,在行礼时忍不住多瞟了两眼,殊不知刚巧与魏斟四目相对。
他正深情款款地看着我,眼神炙热,眉眼带笑地走上前,凑在我耳畔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
“封妜,这一世,我不会再放开你了。”
我怔在原地,一脸懵。
我鲜少出府邸,更从未见过魏斟,他为何认识我,他眼底万种风情,热烈疯狂,又因何而来。
彼时满座哗然,旁边的阿姊更是疑惑,用手肘抻愣在原地的我,“妜儿何时认识太子殿下的。”
我朝阿姊无辜地摇摇头,表示我的不知情。
还未待我反应过来怎么回应时,那个奇怪的太子却先出了声。
"早听老师府上还有位绰约多姿的幺女郎,今日终于见到了真容。竟比想象中还要美上几分。"
我脸皮薄,被他如此直白的话羞红了脸,木木地垂着眼帘,不知如何作答。
这时,姗姗来迟的皇后终于来为我救了场。
“斟儿,今日怎么如此孟浪唐突,妜儿年纪尚幼,难得出一次府,你可别吓坏了人家。”
我暗暗舒了一口气,朝上座的皇后做了一礼。
皇后与父亲师从同门,太子出世后,皇后便请了父亲给魏斟教导功课,故而,皇后与母亲也成了手帕交,刚出生,便将我与阿姊认作了干女儿。
但因我不爱出门,不常与皇后见面,平日里都是阿姊与她走得近。
“母后教训的是,是儿子孟浪了。”
随后魏斟朝我拱手作揖,“妜儿妹妹多有得罪,一时失言,还望妹妹莫怪。”
他端地很是谦逊诚恳,只是那句“妜儿妹妹”却叫得令我十分惶恐。
让人觉得,他有意与我拉进关系。
之后,阿姊在皇后旁边咬了几句耳朵,便笑盈盈地拉着我去了温汤池,临走时,我能察觉到魏斟的视线在我身上不断游离,不知为何,心口汹涌得厉害,以至于不小心踩到了自己的裙裾。
身子正踉跄,魏斟眼疾手快,稳稳扶住了我,朝我抿唇一笑,“山路崎岖,妜妹妹可要仔细脚下。”
尽管魏斟举止得体,我还是一下子炸红了脸,垂着眼帘与他道谢,“多谢殿下提醒。”随后慌慌离去。
2
“妜儿当真没见过魏斟?”走远了,阿姊又问了我一遍。
我摇头,“我出府的次数屈指可数,如何能认识他。”
阿姊点头,毕竟我每回出去,阿姊都与我一起,形影未离,若真见过,她定当是知道的。
她沉思片刻,又说道,“魏斟此人长得虽标志,性格也好,但毕竟是太子,心思深沉,这么多年,我也捉摸不透他,你心思单纯,日后还是离他远点好。”
我乖乖应下,觉得阿姊言之有理。
温汤泡得身子昏昏沉沉,阿姊耐不住,早一步起身去了厢房歇息。
我刚穿整好衣裙,玉面屏风外突然出现沉稳的脚步声,我立马吓了一惊,扬声道,“谁在外面?”
话刚落,就听见魏斟清咳了一声,“抱歉了妜妹妹,我本想来泡个温汤解解乏的,不知道你在这处。”
我出了屏风,就见魏斟身子微躬,对着我淡淡而笑,再加上言语诚恳得体,我心中即使不满,也不好发作。
想着刚刚阿姊对我的叮嘱,我只摇摇头,道了一句无妨,就急着往外走。
“妜妹妹这是要去哪?我送你。”魏斟突然快步赶上我。
我立马拒绝,“不用,阿姊说在西厢房等我,我自己去就可以了。”
“你知道西厢房在哪里吗?”
我瞬间愣住,从小我就是个不记路的性子,又是头一遭来这里,确实是不认识的。
魏斟轻笑,“怎么还是跟从前一样呆呆的。”
从前?我皱眉,“殿下以前见过我?”
他不答,只静静地看着我,眼底是我看不懂的情绪,似悲似喜。
过了一会,才说道,“我送你去找封姚吧。”
最后,我没有拒绝。
一路上,我静静紧跟在魏斟身后,悄悄打量他。
身影颀长挺拔,既有浑然天成的高贵淡雅之气,又时不时流露出身居高位的孤独感,不知不说,魏斟确实当得起世人美名。
西厢房很近,不一会就到了。
许是刚泡完温汤,再加上走了一段路,如今身子有了些汗意,刚想着待会要吃些冰鉴葡萄,魏斟就突然来了一句。
“刚泡完温汤,可不许贪凉吃冰鉴果子,容易生病,待会我叫内侍送些你爱喝的红参玫瑰茶过来。”
我顿时诧异,不自觉地后退几步。
他是有读心术吗?怎么对我的喜好这么了解?
魏斟见我此举,并不惊讶,反而笑得更开心了,“快进去吧,若是封姚看见你这副样子,可又要冤枉我欺负你了。”
说完,就转身离去了,留我在原地久久不能回神。
彼时,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魏斟有鬼,远离魏斟。
3
可自春日宴后,太子魏斟频频往封府送礼物,昨天是富景酒楼的糕点,今日又是他用新得的和田玉打造的玉簪子。
外头都传,太子魏斟在春日宴上对太傅幺女一见倾心,不日便要立储妃了。
“这魏斟是在打什么算盘?”
阿姊看着刚送来的玉簪子,陷入沉思,“父亲本是他的老师,自是一心向他,如今朝堂亦无党羽之争,更不需他用联姻来谋利……”
“难不成这厮真对你一见倾心了?”
我茫然地摇摇头,“阿姊与他接触更多,尚不知他的目的,我就更不知道了。”
说完继续看我的书册。
“事关于你,你还能这般心如止水!”阿姊颇有恨铁不成钢之意,一把扯掉我手上的书册。
我叹了一息,“现今天下太平,朝堂安稳,就算他是当今太子,可我只见过他一面,他若真想求娶我,如父亲的地位,只要我不愿嫁,他便奈何不了我。”
阿姊自小就是个坦率豁达的性子,又最为疼我,就算去岁她已嫁做了探花妻,却仍怕我这个沉默寡淡的妹妹闷在屋里无聊,隔三差五就回娘家来陪我说话。
“阿姊放心,我不出门就是了。”
我投以阿姊一个安心的笑,可内心却还是有点发怵。
魏斟好似对我很是了解,如今又频频示好,总觉得事情不会如此简单。
傍晚,阿姊回家后,我只身去了藏书楼,今日父亲新得了一批书册,我抽空过来看看有没有我感兴趣的,顺便理一理书架。
“扫整书架这种活,怎么还需你来做?”
魏斟突然出现在另一排书架前,拿着一本书正好整以暇地看着我笑。
我吓了一跳,手上的竹简砸了脚,“嘶…”
“我有这么可怕吗?吓成这样?”魏斟急急上前,扶我坐下。
“你无声无息地突然出现,是个人都会害怕!”心中怒气上涌,因为脚上的疼痛一时没忍住发泄了出来。
“好好好,是我不对。”他反而笑了起来,柔着声音给我道歉。
“太傅说他新得了一些书,叫我过来取这几天的课业,到时候要考,没想到吓着你了。”
他这一番话,竟让我无从反驳。
这时夕阳透过窗子撒进来,正照在魏斟的身上,他朝着我浅浅笑,眉眼温和缱绻,有一说一,他真的是有一张容易令人沦陷的皮相。
恍惚片刻,他打破了沉默,将手上的书册递给我,“这本书你应该会喜欢。”
我接过一看,顿时惊讶,他怎么知道我喜欢看这类杂书?
手心不自觉沁出一层薄汗,“殿下为何对我这般了解?我们以前见过吗?”
魏斟没有立即回答我,而是静静地看着我,似乎在透过我的眼眸回忆些什么。
半晌,才微笑着答道,“显而易见,我对你心生爱慕,提前打听了你的喜好想讨你欢心。”
“那日春日宴上,我与殿下本是第一次相见,可当日殿下的表现却十分反常。似乎对我很是熟悉。”
我瞪着他,他却依旧波然不惊地解释,“那次,并不是我第一次见你。”
他这个理由看似很合理,可我却并不相信,但又究不出错处。
最后,我朝他后退几步,恭敬地做了一礼,“多谢殿下抬爱,但臣女惭无倾城色。不敢攀贵德,抱歉了!”
说完,我也顾不上什么礼数章程,慌张离去。
4
后面几日,魏斟以课业之由去过藏书阁两回,被我躲过了碰面的机会。
皇后生辰宴发来拜贴,我以旧病复发为由,未能与阿姊一同出席。皇后知我自幼身子病弱,并未怀疑。
整一个月,魏斟的礼流水一般送到了我的屋子里,我却从未出过门。
待到四月廿五那日,阿姊突然染上了风寒,听母亲说,烧了三日,很是严重。
我得知后,着急赶往阿姊府中看望。
走到半路,突然想起阿姊最爱吃富景酒楼的马蹄糕,可刚进酒楼,就见魏斟随步而来,看我的眸子里似乎有些怒意。
我也不知道为何,折身就跑,可身后的魏斟却紧跟不舍,东走西窜下,魏斟将我抵进了死胡同。
“为何躲我?”魏斟粗喘着气,把我围困在他的臂弯里,身后是冰冷的石墙,退无可退。
“殿下请自重!”我被乱了气息,再加上他的唐突之举,脸上愠意明显。
魏斟见我怒目圆睁,脸色稍缓,却并未放开我,颇有一种不给他一个解释就不善罢甘休的气势。
我见况,心中更火了,一下子将这些时日来的憋闷恼意全部倾泄出来。
“敢问殿下这是何意?是想强取豪夺,恃强凌弱不成?”
“你说你爱慕我,所以大张旗鼓地送礼,惹得满城风雨,就算我已明确拒绝,可你依旧步步紧逼。丝毫不顾及我是否会损闺名。”
“且不说你对我在并不相识下的爱慕之情从何而来,就论你这个只有一面之缘就对我过分了解一事,我如何能不躲不惧?”
越说越委屈,说到后面,我的声音已经有些颤抖。
魏斟见我眼底的雾气,突然手足无措起来,赶忙松开对我的制梏,后退了两步,“抱歉,是我唐突了。”
我撇头,不接受他的道歉。
良久,我再抬头看他时,他眼尾泛红,“妜儿,你相信前世今生吗?”
我感觉听了一个笑话,嗤笑道,“殿下是想说,我与你在前世见过,所以你才这么了解我是吗?”
他点头,十分诚恳。
我刚息下的怒火又窜了上来,重重踩了他一脚,“耍我玩啊!”说完,愤愤离去。
5
五月初五,端阳佳节。
距离上次与魏斟不欢而散又过了多日,许是当日之言起了作用,魏斟再也没往府上送礼。
可皇宫设宴,作为皇后的干女儿,理应入宫参宴,往年我都是不出门,皇后也体谅,可如今我已十七岁了,皇后认为我不能这么闭塞在家,要多见见世面,沾些烟火气。
饶是我再怎么不愿,还是被阿姊和母亲推上了入宫的马车。
“这次的晚宴还是设在骊山行宫,听王嬷嬷说,陛下请了西域的胡姬表演,还能一同去后山骑马狩猎,泛舟游湖。”
“上次泡了温汤身子确实爽利许多,这回正好可以再去泡泡,对你也有好处。”
阿姊一路上喋喋不休,试图让我提起兴趣。
我如小鸡啄米,顾着点头,可心底还是有些不安,这种场合,必定会遇到魏斟。
罢了罢了,想多了庸人自扰,既来之,则安之。
到了行宫,我跟在阿姊与母亲身后,努力拉低自己的存在感,可越怕什么来什么,由于之前甚少出门,京城贵胄女眷都对我这个新鲜之人好奇,纷纷过来问候奉承。
好在阿姊懂我的为难,与皇后说了几句话便带我去了温汤池,“知道你适应不来这种席面,你且在这处泡泡温汤,我让王檐若留下来服侍你。”
我叫住阿姊,“阿姊不留下来陪我吗?”
每回这种场面,我都要阿姊在旁边才会踏实。
“封家无男丁,父亲居于高位,我身为封家嫡长女,自要同母亲一起撑起封家门面,你在这处等我,待我去交酌完,就来接你去骑马打马球。”
说完,又朝她最亲信的侍女王檐若仔细交待几句,便转身离开了,
我静静地看着阿姊的背影,端庄绰约,落落大方,突然眼睛有些湿润,原来我能由着自己的性子生活,一直以来都是阿姊替我担起了封家的责任。
心里顿时暖暖的。
泡完温汤出来后,王檐若替我去取些冰鉴果子,我悠然自得地坐在院子里晾头发看话集子。
可王檐若回来时,手上的镶玉漆盘里盛着的一壶尚冒着热气的红参玫瑰茶,以及几样十分精致的糕点。
我皱眉问,“不是说要冰鉴果子吗?怎的是这些?”
王檐若为难道,“方才去小厨房,那掌炊的内侍说,太子殿下刚下的令,说是为了姑娘的身子考虑,不可给姑娘凉食冰饮。”
我一听,瞬间就火了。
又是魏斟!又是魏斟!
我自小在万千宠爱中长大,父亲纵我,母亲宠我,阿姊疼我,从小,只要我不愿意,不喜欢的,没有人会逼迫和强制。
魏斟是第一个!
我揣着一肚子火起身,王檐若放下漆盘,“姑娘这是要去哪?”
“去找魏斟算账!”
王檐若不敢多言,急急跟在我身后。
一时气昏了头,却忘记了自己根本不识路,也不知去哪里找魏斟,一通乱走后冷静下来时,才发现自己竟走到了山林中。
“檐若,你知道我们走到哪了?”
“奴婢不知。”
我懊恼道,“你方才应该叫住我的。”
“方才见姑娘怒气冲冲,以为姑娘知道太子殿下在哪,便不敢多嘴。”
果然冲动误事,这四处茂林深篁,辨不出方向,我与王檐若只能折身靠着显微的足迹和印象慢慢走。
突然,一支箭矢疾风而来,我被吓得愣在原地,风驰电掣间,一个残影近身,腰身瞬间被一只有力的手臂抱住,耳旁一阵刺痛,汩汩暖流沿着右颊流下。
待我反应过来时,面前是魏斟冲冠眦裂的脸,“好好的乱跑什么,知不知道,刚刚那一箭差点能毙了你的命!”
我懵了一会,再缓过神来时,竟然好不争气地大哭起来。
这一哭,魏斟立马息了怒色,泪眼朦胧间,我好像看到了他眼底的泪痕,他一把将我拥入怀,紧紧地抱着我轻声哄着,“不哭不哭,没事了,没事了。”
后来我才知道,我误闯了狩猎的林子,因植被茂密,我被当成了山鹿,若没有魏斟及时赶到救我,那一箭就正中心口。
好在最后只是被箭矢擦伤了右颊和耳朵。
魏斟将我带回了他的殿中,立马传了太医过来,伤口不大,只需要按时上半个月的药便能痊愈。
魏斟仔细地为我的脸上药,温柔又细致,我静静地看着他,脑海里又想起他怒我时的担忧和泪痕。
那一刻,我真切地感受出他当时的害怕和心疼。
“这是太医院里最好的金疮药,回去后可要按时涂,你们姑娘家脸皮娇嫩,可别留了疤。”
“嗯!”
“封姚说让你在小筑等她忙完带你去打马球,好端端地怎么突然进了后山林?”
“我……”我一下被噎了声。
若是这时说是因为被他气昏了头,去找他算账才迷了路会不会有些荒唐,我可不能在他面前丢了面子。
他魏斟见我不想说,也没再强求,只叮嘱我不识路不要随便乱跑,这山间蛇虫猛兽多之类的话。
几番折腾下,惊动了行宫上下,就连陛下皇后也来了看望,母亲和阿姊更是满眼心疼,在魏斟说了细末后,她们才稍稍放了心。
阿姊本想陪我回府,以往这种时候,我肯定是答应的。
可阿姊平日里要顾两个家,每日奔波,今天难得有她喜欢的打马球,我不想让她扫兴。
所以我拒绝了阿姊的提议,“我想留下看阿姊打马球。”
这一刻,阿姊笑得很开心。
6
一番慰问后,行宫开始复了热闹,阿姊带我去看她打马球。
这场比赛,阿姊半个月前就报了名,她自幼喜欢马球,骑马也很厉害,与男子作比一点也不逊色。
那日阿姊说,这马球比赛的彩头是焦尾古琴,这是一把遗失许久的名琴。
我向来爱琴,父亲为此为我搜集了天下名琴,唯独没有焦尾,一直以来,我都很想用焦尾来弹一首离骚。
阿姊得知后,立刻上贴报名参了赛,就为了给我赢彩头。
可赛场不分男女,阿姊马上技术虽好,但到底比不得男子有臂力,几番较量下,阿姊败下阵来。
“妜儿对不住了,阿姊没能给你赢到彩头,待会看看谁会赢,到时阿姊一定给你买回来!”
我细致地为阿姊擦汗,安慰道,“焦尾固然稀罕,但阿姊玩的尽心,妜儿比得到焦尾更开心。”
阿姊抚上我的左颊,眼底盈盈泪花,言语里却多了一分坚定,“只要妜儿想要的,阿姊定会送到你面前。”
阿姊总是那么疼我。即使方才有一刻对焦尾失之交臂而失落,如今也荡然无存了。
后面我和阿姊去打捶丸,没再关注马球最后的胜负。
待我玩累回席时,才得知那场马球赛是魏斟得了彩头。
听闻魏斟六艺中御术最弱,在一众贵胄公子间可以说是垫底的,可这场比赛中却拼莽劲拔了头筹,确实令人惊讶。
众说纷纭间,就见魏斟归席,身后的内侍手上正捧着那把焦尾琴,我忍不住多看了几眼,心下有些惋惜。
随后埋头吃糕,面前忽然出现了一双绣着金丝纹的马靴,上面沾了不少泥,抬眼,魏斟正端看着我,嘴角衔着淡淡笑意。
“听闻妜妹妹自幼爱琴,今儿这彩头,就赠予妹妹了,权当我这个做义兄的一点小小心意。”
我懵了半晌,当反应过来要拒绝时,魏斟却直接以有要事为由离了席。
此事立即在贵胄圈中传开,太子马球场上竭力赢彩头,只为博取太傅二姑娘欢心。
翌日,皇后召我进宫。
“妜儿,近日京都里外都在传颂你与阿斟之事,对此你如何看?”皇后手执玉柄扇,有一下没一下地摇着。
我低眉颔首,“不过都是茶后戏资,并无此事。”
皇后却放下扇面,覆上我的手,“本宫是看着你长大的,知你秉性良善,阿斟对你亦是拳拳真心,只要你肯点头,明日本宫就去封家下聘。”
我这才恍然,皇后此番竟是要乱点鸳鸯谱。
我顿时慌了起来,马上俯身跪地,“妜儿惶恐,太子殿下对妜儿照顾有加,妜儿亦对太子义兄十分敬重,并无半点儿女私情,还请娘娘收回成命!”
屋里,瞬间一片死寂,我撑着身子半点也不敢动,半晌,才听见皇后叹了一息,亲自扶我起身。
“好孩子,不必这般惊怕,这婚姻之事自是讲究你情我愿,妜儿若是不愿,本宫也不会强求。”
“回去吧!”
我恭敬地揖了礼,转身离去时,却发现魏斟正站在门外一动不动地看着我。
他到底什么时候进来了,竟没有一点声响。
脑袋一下炸开,手心的汗濡湿了绢帕,我心虚地躲开他的眸子,慌慌张张地出了门。
可走了很久,我还是能清楚地感觉到身后有一道目光在紧紧盯着我,那目光里,有悲伤,有愤怒,有失落,还有那股不知从何而起却又浓烈缠绵的情意。
6
一连几日,当日魏斟的眼眸都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每次回想,心底都会泛起心疼,难过。
就连我最爱的诗集,也没办法静下心来看。
阿姊以为我被魏斟吓癔症了,连忙与父母亲商量,要送我去西南外祖家避暑静心。
我也觉得,应该去外面静一静。
或许换个地方,我就会将魏斟淡忘了。
收整东西时,王檐若搬来那副用锦帕包着的焦尾琴问我,“姑娘,这把琴可要带?”
我看了一眼琴,脑子里又浮现出他送琴时的那抹淡淡笑意,以及,凤仪宫里看我时的眼神。
心里又开始难受起来,我忙收眼不再看,“不带。”
自那日凤仪宫里回来,有好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敢再看焦尾。
阿姊与母亲将我送出城门,仔细叮嘱了许久,就在动身时,东宫的内侍叫住了我。
“封姑娘,这是宫里最好的舒痕膏,殿下特意叮嘱老奴亲自送予姑娘手中。”
我握着手中的小瓷瓶,心中五味杂陈。
本以为凤仪宫一别后,魏斟已经放弃我了,可如今竟还牵挂我的伤势,为我送药。
那内侍临走时,不忘添了一句,“殿下原是要亲自送姑娘的,奈何今日公差繁忙,被陛下绊在了宫中脱不开身。”
瓷瓶在掌心渐渐温热,再看时,洁白的瓷身上晕出一副双猫戏鱼图,釉色鲜艳夺目,栩栩如生,看得出画主花了不少心思。
我自小爱猫,为此,父亲和阿姊聘了许多猫回来,还为它们单独僻了一间屋子,而这瓷瓶上所画的正是我最爱的狸猫。
我不由得深思,这一次到底是巧合,还是他魏斟真的熟悉我至此,若真是,不禁有些细思极恐。
越想,越觉得脊背发凉,随手将瓷瓶扔给了王檐若。
7
外祖家在滇南,听阿姊说,那里是个四季如春的地方,我们赶了半月水路才抵达。
外祖父出自滇州段氏,自古便是西南一带的显赫世家。
我生得病弱,又是个闭塞的性子,这是我头一回来外祖家,而我这一辈,上有五个表兄,仅有母亲育有女儿。
故而,外祖府上上下下对我这位初来的表小姐十分爱重,我来这的一月过得也十分惬意。
每日躺在摇椅上看书,站在窗前临帖,闲暇时去陪外祖母打叶子戏,玩射覆。
依年龄,段家只有五表兄与我年纪相仿,外祖父在府上为五表兄设了学堂,请了名师大儒来做学究教导他。
可五表兄有个鬼马行空的脑袋,在课业上根本就不上心,时常从坊间给我淘来许多新奇的小玩意,他总说我生活寡淡,要带我去外面找新趣。
“妜妹妹,我们去叶榆泽畔放风筝吧。”五表兄趴在我的窗子上,百无聊赖。
我未停下手上的笔,头也不抬道,“不去。不想动!”
“哎呀,你再这样闷下去不怕变成比丘尼啊!”说完立刻夺下我的笔,将我拽出了门。
“常若新做了一只大风筝,上面的雄鹰可是我画的,我保证你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帅气的风筝。”
常若是五表兄的同窗,因与段家是世交,便一同在段府书堂上学,与五表兄很是要好。
和五表兄出来玩时,见过他几次,是一个端方君子,听表兄说,他每回课业都评优,学究也对他寄予厚望,说他明年春闱定能中榜。
他为人谦逊有礼,很是照顾人,几回下来,我与他也算是熟识了。
放完风筝,三人去听风居喝茶。
听风居里文人雅客居多,有同者一起翻书赌茶,消遣时光。
五表兄人情练达,到哪都能与人侃侃而谈,而我和常若,则在旁边的书角看书喝茶。
期间我才知道,原来常若也爱看杂书,他与我讲了许多奇事异闻,凡是我读过的书,他都有涉猎一二。
正听常若讲到尽兴处,五表兄那边突然与人争吵起来,走近一看,一个熟悉的身影映入眼前。
时隔一月有余,我竟在这里见到了魏斟,在我就快要忘记他的时候。
他一个当朝太子,怎会出现这边地之处?
我疑惑地望向他。恰巧与他眼神对视,我立即躲开他的视线。
之后了解了才知道,五表兄在与人斗诗时,因文武孰重与魏斟同行之人起了争执。
这才闹成这番局面,最后魏斟说了一句“武夺天下,文定江山,故而文武并重。”才得以平息。
听到此话时,我不得不承认,魏斟的确有帝王风范。
8
从听风居出来,常若将我与五表兄送回了府。
刚进府就看到两个陌生的侍从抬着木箱子进来,听下人们说了才知道,外祖父有位很重要的客人要来府上小住一段时间。
我对此事本就不上心。加上脑袋里还在想魏斟一事,就先与王檐若回了院子。
哪知刚推开院门就见魏斟坐在树底下喝茶。
“你怎么在这?”
惊怒之下,我顾不上任何礼仪。
魏斟浅浅一笑,饮下一杯茶才道,“滇南普洱,的确是好茶,怪不得你会喜欢。”
我冷嗤,“私闯民宅,目中无人,想不到太子殿下私下竟是此等作风。”
他不生气,反倒笑着朝我走来,目光所及之处是我的右颊,打量几眼道,“本以为你会跟我赌气,不用我给你的舒痕膏,如今看,你倒是听了嘱。”
我不悦地白他一眼,“谁会与自己的容貌过不去。”
“不怕我给你下毒?”
这一问竟让我怔住了,后来才发现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我无形中对魏斟竟然放下了所有防备,总是不经意地露出自己的真性情。
潜意识在告诉我,不论如何,他都不会伤害我。
这种感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晚上我躺在床上,看着帐顶的流苏,脑海里突然晃出他将我从箭矢前救下时,他眸中的担忧与害怕,大概是从那一刻开始的吧,我想。
在我走神时,魏斟已经近身,骤然肃了面,冲我冷笑道,“哼,在想沈家那小子?”
我一愣,“你在说什么莫名其妙的话!”
“据我所知,沈常若的才识虽好,可不及我一半。”
我这才听出他说的是常若,原来他姓沈,一直以为他姓常。
他笑睨着我道,“我看过的书比他还多,你可以来找我,我比他厉害!”
我哼了一声,只觉得他幼稚,未与他搭腔,顾自进屋,将他隔绝在外。
晚膳时,我才知道,外祖父口中的贵客便是魏斟,只不过现在他伪了身份,是江南儒商魏江清。
不知道他要做什么名堂,我也不去费心思想。
9
夜凉如水,许是晚膳后喝的那杯茶沏得太酽,快子时了也没半点睡意。
我拢了件披风去院子旁的望月台,季夏的月色很好看,满天星斗。
正仰头放空时,魏斟突然从身后冒出来,“在想什么?”
我骇了一惊,差点踉跄,瞬间点燃了我的怒火,“要你管,怎么哪都有你。”
“瞧着人前是娴静寡言的封二姑娘,人后竟这般泼辣!”
我没好意地瞪他一眼,揶揄道,“我也才知道,风光霁月的太子殿下暗地里竟是这般孟浪滑舌。”越发肆无忌惮了。
他纠正我,“如今我叫魏江清。”
我撇头不睬他。
就这样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魏斟已经离开时,他突然蹦出声。
“封妜。”
我下意识地转头,撞进他的眸光中。
只见他敛去笑意,凝视着我的眼眸里盈出雾气,“我喜欢你,是真心的,没有目的,没有阴谋。”
他顿了顿,红了眼眶,“可不可以别躲我?”
我被他飞快的转变整得不知所措起来,沉默了半晌,脑子指使着我从喉咙里吐出“好”的音符,到了嘴边却息了声。
他等得有些急了,双手越过我的腰间,落在身后的栏杆上,将我围困在他的身前,“别忘了,你的命是我救下的,不许想沈常若,封妜,你只能想我。”
他好霸道,好专制,可不知为何,我却并没有生气,反而有些开心,心跳砰砰,双耳俱热。
最后我也没坑声,魏斟不再继续为难我,叹了一息,道,“夜深了,回去歇息吧。”
说着,将我送回院子,临走时,又添了句,“记住今晚我说的话。”
说完一转身,袍袖飞扬间,人已经走出了院落。
我静静看着他远去的背影,心里有些懊恼。
第二日,五表兄带我出去看射柳,恰巧魏斟也在,不过他依旧是以往的儒雅君子相,见到我时也不过莞尔一笑,似乎昨晚之事从未发生。
这也令我松了口气。
五表兄学识虽不好,骑射却超群,锣面咚咚,五表兄身后无数人拍手叫好,我被人潮挤了出来。
随即就找了个安静的地方等五表兄。
殊不知魏斟也紧跟其后,双手环胸,正好整以暇地看着我。
我故意不睬他,继续往前走。
“又乱走,迷路了我可不帮你!”
我听后心中更气,脚步加快,偏要与他作对,待停下来时,竟到了断崖处,前方,深渊万丈。
回头看,魏斟在后面慢悠悠地过来,脸上笑意越发明显。
“来都来了,何不如看会儿风景再走。”
说着搬来两块大石头,他先是挑了其中最圆滑的石头吹了吹,接着用他洁白的衣袖仔细地擦去污尘之后,示意我坐。
我也并不客气。
彼时夕阳西斜,我与他静默不语,看霞光漫天,不得不说,这里的景致真不错。
“对面就是支亭山,听闻那里有处十里桃林,三月时桃花迎风初绽,灼灼其华,待到六七月,满树桃果,个个硕大甜美。”
魏斟突然道,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
支亭山是沼国边境,依山傍水,气候宜人,以盛产各种瓜果闻名,只可惜,如今两国关系很是恶劣。
“过段时间,桃果成熟,我给你摘来。”他侧首笑着对我说。
“殿下金口玉言,可不许反悔。”
“不反悔。”
“若是殿下没能摘到桃该如何?”
如今这个局势,想要去支亭山摘桃,简直天方夜谭,我只道他在诓我,便起了揪他尾巴的心思。
我笑的促狭,看着魏斟,他正直面迎着我笑,过了一会,才道,“若我不能践言,我就终生爱而不得,孤独终老。”
听完我嘴角微抽,不知为什么耳根子红了起来。
这算哪门子誓,他是否孤独终老与我有何关系。
我转头不去看他,“那我便静等殿下的桃果了。”
“若是我将桃送过来了,妜妹妹可否也允我一件事?”
“什么事?”果然,天下就没有免费的筵席,我立刻警惕地看着魏斟。
只见他突然凑上前,与我不过两指五指距离,温热的气息喷洒在我脖颈处,“做我的太子妃。”
我登时羞红了脸,瞬间起身,恼了一句,“登徒子。”便快步离开,留魏斟在原处。
夜里再回想时,我竟有一刻感到心中欢喜。
我想,这魏斟肯定使了什么邪术,太子是何等人,若日后真进了东宫,我定容不下他身边的莺莺燕燕。
我日后要嫁的人,一定要一心一意待我的。
魏斟做不到。
10
此后半个月里,魏斟隔三差五来我院里找趣,有时候就静静地在我旁边喝茶,看书,渐渐的,我也习惯了他的存在。
上回射柳回来,五表兄名声大噪,直接旷了两天课,直嚷嚷着要去大表兄的军营里参军。
外祖父知道后发了怒,将五表兄关了起来。
说来,我上头的四个表兄都从了军,在与沼国交界的军营中任职,故而外祖父十分看重五表兄的学业,一来是战场生死难料,外祖父想为段家留个后,二来,四个表兄皆是武将,轮到五表兄,自然是想让他从文走仕途。
六月中旬,魏斟消失了三天,晚饭时,我又听外祖父说,沼国已经在边界蠢蠢欲动,恐有起兵之势。
我心中不由得担忧起来,魏斟身为一朝太子,自然脱不开责,只盼他是回京去了,如此至少安全。
可事与愿违,在他消失的第五天,魏斟重伤归来。
听他身边的侍卫说,他被沼国将军射了一箭,伤了手臂。
也是这时候我才知道,魏斟只身来滇南,是想秘密侦查沼国动向,这才隐身在段家。
可魏斟乃是一朝太子,陛下为何会让他来这边远之地做斥候?
外祖父得知后,立即召了府医来为他医治。
我在榻前看着他鲜血淋漓的手臂,心疼不已,他却还咬着牙关冲我笑,“妜妹妹别担心,不过小伤而已,几天就会好,”
我忍不住挖苦他,“你笑得比哭还难看。”
接下来的半个月,他魏斟在段府养伤,他对我有恩,我自然也对他悉心照顾。
有一次恰巧撞见他换药,那装药的瓷瓶竟与当时送我那只双狸戏鱼的药瓶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