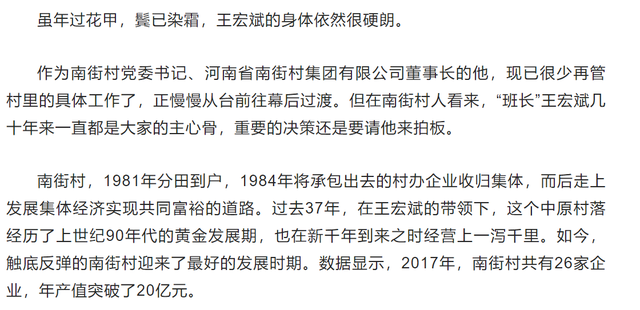年过花甲的王宏斌如今已经很少管理村中的事务了,他的身份依旧是河南省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过去的那几十年里,他这颗“大心脏”也跟着南街村的发展起起伏伏,村民们也早就习惯了找他拍板任何重要决策。
中国的村子有很多,像南街这么有名的还是极少,无论是繁荣与没落,都与王宏斌这个主心骨的决定密切相关。

“红色亿元村”
改革开放时期是中国经济增速最为猛烈的时期,很多人趁着这阵东风起家,创造了一个个“财富神话”。
由于当时的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也有许多人陷入了深深的迷茫,王宏斌便是其中之一。
1978年安徽小岗村开始的“分田到户”拉开了全国农村改革的序幕,这种新制度的优越性很快体现出来。
农民可以根据经验与市场需求自主决策,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稳定的收入也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市场机制伴随出现,也同样加强了农村与城市之间的沟通,提高了农产品的流通性。
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任何变化都该被拥抱。
南街村也很快搞起了分田到户制度,在1981年,村中的土地分到了各家各户,当时刚兴建起来的面粉厂、砖厂也被转为私人承包。
在很多地方承包制都展现出了巨大的优越性,可王宏斌却发现了南街村存在的问题。

这个村子的地理条件优越,和附近的城市间隔不远,很多村民都开始迈向经商之路,根本不把分给自己的那点地放在眼里,那些靠生意发家致富的案例更是促使更多人继续走向这条路。
大多数村民都把地转给其他人耕种了,几年过去,南街村的粮食产量不增反降。
砖厂和面粉厂也很快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的情况,承包人的口袋里财源滚滚,可那些工人却被拖欠工资,人们纷纷去找王宏斌讨要说法,这件事一度闹到了县委。
什么事都没搞好的情况下,王宏斌觉得单干这条路走不通了。
从1986年开始,他要求村民们不得将手中的田出租、转让,鼓励村民把土地交给集体,在他苦口婆心地劝说下,800多户村民的责任田终于回到了集体手中。
按照高层的指导思想,分田到户本就该“宜统则统,宜分则分”,若是各地一哄而起没有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反倒把好政策给用坏了。
集体的力量确实是巨大的,南街村于1988年耗费20万买来一套制作方便面的设备,商品刚刚上架便供不应求,那时就连来南街村进货的车子都得排队。

在尝到甜头后,企业迅速扩大生产,每天都能产出400吨方便面。
有了方便面厂的成功案例,王宏斌更是认为这条路一定可行,他持续推出了包装厂、冷库、糕点厂等项目,还在1992年涉足印刷厂行业,那时南街村的工农业产值已经突破亿元大关。
王宏斌其实已经意识到:在这个充满机遇的时代,做什么都能赚钱,这是市场经济的大环境决定的。
而南街村以极强的号召力把大家汇聚起来,有点类似于“开挂”的感觉。
取得了成绩,村民们的生活好起来了,王宏斌却陷入了思考:南街人该成为什么样的人?有没有能够长期延续的发展思路?
为了解决好这个问题,他苦思冥想了很久,终于想到了一位伟人:毛主席。
毛主席在中国人民心中本就是神一样的存在,若是能借用毛主席思想将南街人民武装起来,那大家始终都是有目标的。
很快,毛选开始在村子里流行,大喇叭中也经常响起《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等经典曲目。

为了能把这件事做好,王宏斌坚持自己每月只拿250元工资,并给自己塑造了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形象;此外,南街村内还大力推行着雷锋精神和“傻子”精神。
实际上,在南街村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所有权力都在向王宏斌一人靠拢。
即便村中有着村党委、村委会和村集团公司这三大班子,但所有工作人员都听从王宏斌一人的安排。
而村民的生活幸福指数又被牢牢控制在王宏斌的手里,他创造了一套极为特殊的村民管理制度:“十星好村民”。
按照他所设置的规定:只要村民表现不好,就会扣除一颗星,当扣到6颗星时,就代表着该村民基本丧失了生存能力。
只要还在南街村生活,就必须得遵循这个规定,因为在集体制的大背景下,从上学一直到婚丧嫁娶都是南街村给的。
可在外界看来,南街村一片祥和。
1998年时村里就盖好了22座楼房将所有人搬了进去,实现了所谓“共同富裕”的目标,村民的生活支出基本为零,而按照王宏斌的说法:“我要让村子里的人富得一分钱都不用存。”

省社科院研究员刘倩说:“在这里,南街村的领导集体对王宏斌没有任何监督机制,形同人治。”
重压之下的祥和终究是虚幻的,总有胆大的人站起来反抗。
第一个“表示不服”的人出现于1999年,他是村大修厂厂长耿宏。
因为检查卫生不合格,耿宏被撤职并要求搬出村民楼,住进了还没来得及拆迁的旧房中,那里被村民们称为“西伯利亚”,意思是“流放犯人的地方”。
耿宏来气了,当即要求王宏斌落实国家政策,他自己要承包一块土地。
几年后,越来越多的“挑战者”出现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具备经营头脑,不甘居于人下。
毫无例外,这些人都选择了离开。

这似乎也预示着南街村的奇迹只能是昙花一现。
“天堂”与“牢笼”
外界眼中,南街村是个其乐融融的乌托邦;可随着村民们的认知逐步提高,大家逐渐发现这里是个被封印的“牢笼”。
王宏斌尝到了身份赋予的荣耀感,这么些年来他始终维护着这片使他功成名就的沃土,为了彰显优越性,他甚至找人修起了城墙,将南街村与其他村子彻底隔绝开。
进入21世纪,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度,很多全新的赚钱思路开始涌现。
有几位南街村集团的高管向王宏斌建言:融资上市是一条绝对可行的道路。
王宏斌当即投了反对票,他是“一言堂”,这一票已经能杜绝一切。
随着旅游业蓬勃兴起,王宏斌从中看到了新的机会:这么些年来一直都在宣传毛主席思想,为何不制造一个“红色旅游圣地”?
于是,他又斥巨资复制了遵义会议旧址、毛主席故居、西柏坡等标志景观。

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南街村已经开始出现了收入下滑、村民不满等情况,因为资金问题,王宏斌设计的“四卷楼”最终没能成功开业。
法律意义上宣告南街村“公有制经济”终结的时刻发生于2004年。
在股东大会上,1809万的股本转让给了王宏斌本人,其余的大头都转给了他麾下的各位高管。
另一边,南街村也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相比于最开始的“东风起”,当时正是国家宏观调控、银根紧缩的时期。
担任总经理的窦彦森回忆:“我是2004年年底接任总经理职务的,到了之后才发现,集团的账目上竟然没有一分钱,很多听到点风吹草动的人都说南街村根本撑不过第二年的劳动节。”
至于原因,这些高管都很清楚。
由于没有其他稳定的资金渠道,南街村一直靠着银行贷款来维持运作,那年正好银行收紧不给贷款,这就导致南街村集团的资金链断掉了,账面上那些用来生产的本金也因需要还上一笔贷款被银行划走。

令人惊愕的是,当时南街村的总负债高达17亿,总资产为26亿,只有9亿是净资产。
各种言论甚嚣尘上,一向能拍板决策的王宏斌也无可奈何。
或许是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亦或是认同王宏斌的发展模式,困难关头,还真的是村民们救活了南街村。
为了能恢复企业运行,很多村民都自发捐款,凑足了100万让优质企业先开始运作,当这些企业的产品售出后,再拿这些钱用于其他企业运作,一步步下来,所有企业都流转起来了。
其实发生在2004年的危机已经能够证明王宏斌走向失败,好在支持他的人不在少数才又创造了这样一个奇迹。
从2007年到2011年,南街村的发展规模再度壮大,王宏斌十分感动,这反而使他没有进行更深入的思考,把村民的帮助视为自己应该带领他们走向共同富裕的动力。
就算生产恢复了正常,可南街村每年需要偿还的贷款利息仍然高达8000多万。
为了坚持自己的想法,王宏斌每年还会从账上掏出2500万来维护村民的高福利,涉及村民的入学、医疗、住房等多个项目。
有一位南街村出生的人曾到广东一所高校读书,在交了学费后,他就会找老师要发票,老师还不解地问:“这么多学生,这么多届,你还是第一个找学校要发票的。”

这位学生笑着说:“我要回去找人报销。”
在光环之下,外界的人也不容易看清南街村的运营规律,他们只是单纯的认为这个村富得流油,没想到这种半遮半掩的宣传方式还能为南街村吸引来不少人才。
只要来到南街村并且有贡献,户口在外地的人才就能成为南街村“荣誉村民”,村子里也会很大方地给此人分一套房子,跟本地村民享受着同样的待遇。
度过危机的多年后,王宏斌也越来越有工作兴致了,他还说:“未来这里还要变,还得有更大的版图。”
有记者前来询问他关于接班人的问题,他也直言不讳地表示:“我会工作到南街村不再需要我的那一天,现在还不会寻找接班人。”
一直到如今,王宏斌仍然在这个岗位上奋斗,即便他的两鬓已渐渐泛白。
在2023年10月的一次会议上,他慷慨激昂地表示:“创新不单单指产品的创新,还包括各项管理工作的方方面面。”
南街村属于幸运的个例,因为他们的企业经受住了30多年的市场考验,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可。
这些,也促使王宏斌始终活跃在新闻媒体上。
参考资料
神话破灭后南街村的当务之急 中国青年报“亿元村”带头人:要让村里人富得不存一分钱 华西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