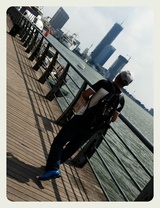凌晨的改则县城仍沉睡在高原的寒意中,虽是夏日里的八月,可街灯却零星地映着结霜的窗棂。我在身上套上几层衣服,将行囊塞进越野车的后备箱。发动机的轰鸣声撕破寂静,车灯的光束刺入浓稠的黑暗,割裂了沉睡的寂静,像是划开一道通向未知的裂缝。下一站的目的地是尼玛县,但心底真正的终点,是阿里北线上那些被藏语称为“措”的湖泊——它们像是神灵遗落的眼泪,散落在荒原深处。


车轮碾过碎石路,车灯的光束刺破黑暗,将前方的未知照成一道狭长的裂痕。高原的黎明来得极慢,天际线从青灰过渡到淡金,雪山的轮廓逐渐清晰,如同巨兽的脊骨刺破云层。后视镜中,改则县城最后一点灯火被荒原吞没,只剩车轮下蜿蜒的土路,像一条褪色的哈达,引我走向更深的孤独。


没有向导,前路未知,方向盘在掌心发烫。我低声哼起一首不知名的歌谣,轮胎与碎石的摩擦声成了唯一的伴奏。海拔表的数字不断攀升,呼吸逐渐变得稀薄,可胸腔里却涌动着一股近乎虔诚的兴奋——这片土地拒绝被征服,只允许敬畏者靠近。此行就是我们与荒原的一场约定。



阿里的措从不迎合人类的审美。它们静卧在海拔4500米的高原上,像是被遗忘的镜子,碎裂成无数片,每一片都折射出不同的灵魂。改则县至尼 玛县的北线,被称为“一措再措”并非虚言,每一处湖面都如一块被风揉皱的绸缎,深浅不一的绿从岸边向中心晕染,湖底的白沙将光线折射成细碎的星芒。我蹲下身,指尖触碰湖水,冰凉刺骨,却仿佛能触摸到时间的纹路——这里的水,或许自冰川纪便未曾干涸。


正午的阳光下,远远地看到在一处措的边上有一位牧羊人,他裹着褪色的藏袍,手中的乌朵(抛石器)在空中划出弧线,石子精准地落在离群的羊羔蹄边。羊群散落在湖畔,像一串散落的念珠。
“这湖,你们叫它什么?”我停下车走近他问道。
他摇头,用生硬的汉语和肢体比划告诉我:“祖辈只说它是‘措’,名字不重要,水能养牛羊就行。”


牧人的回答让我怔忡。在城市,我们习惯为万物命名、分类、赋予意义:这是景点,那是资源,这是“值得打卡”的风景,那是“必须征服”的山峰。而在这里,自然只是自然——无需被歌颂,也无需被利用。牧羊人赶着羊群走向地平线,身影逐渐融进荒原山峦的阴影中。那一刻,我忽然明白:荒原的孤独并非缺憾,而是一种圆满。


行进在这人迹罕见、一措再措的荒原之上,我独自爬上湖畔的山丘,风卷起经幡,猎猎声如诵经般回荡。空气的稀薄让我几次瘫坐在砾石间,呼吸因缺氧而急促,心脏撞击胸腔的声音清晰可闻。没有信号,没有路标,甚至没有方向——这里的一切都在提醒我:人类不过是荒原的过客。可正是这种渺小感,让我前所未有地贴近真实。城市的焦虑、人际的纠葛、对意义的执念,在4500米的高原上,统统被稀释成透明的风。



在一处不知名的措边我反复摩挲一块从岸边捡起的黑石,它粗糙、冰冷,却带着某种亘古的温度。传说每个离开阿里的人都会带走一样东西:一片湖水的倒影,一阵风中的梵唱,或是一块沉默的石头。车窗外,荒原再次被晨雾笼罩,措的身影渐行渐远。但我知道,那些蓝与绿已渗入血液——它们会在某个疲惫的深夜突然翻涌成浪,提醒我曾站在世界的尽头,与永恒对视。



夜色降临时,银河低垂,星子几乎触手可及。我仰望星空,突然想起牧羊人的话:“名字不重要。” 是的,当自然以最原始的面目呈现时,语言不过是拙劣的注脚。阿里的措,是自然写给人类的情书,也是写给自己的墓志铭。在这里,美不是被观赏的客体,而是活着的信仰。当公路最终隐没在地平线,我轻声说:“再见。”
风卷起沙砾,荒原的声音在耳边回荡:“你带走的不是风景,而是被重塑的灵魂。”


色极是空
极度的色彩与视觉冲击
在自然中我们有如匆匆的过客
在自然的博大面前,不需要任何的做作与伪装
灵魂是洁净的。



感谢诸位朋友莅临狼窝,诚望予以批评指导。欢迎各位留言点评、转发、分享、收藏并关注本号,您的支持乃是老狼创作的强劲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