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澳门米其林指南》自 2008 年底发布 2009 年榜单以来,不知不觉已历 17 年之久,其中上榜落榜、开业结业的餐厅多如牛毛,一张榜单勾勒出港澳餐饮业近 20 年的变迁,可谓本地餐饮业一段鲜活的历史记录。
以疫情为分水岭,近几年的米其林指南虽秉持着自己百年来形成的评选标准,却也逐步顺应时代变化,推出一些变革措施。比如除了星级餐厅、必比登推介和入选餐厅三部分传统构成,2020 年指南首次推出绿星、年轻主厨大奖和服务大奖;港澳指南亦于 2020 年同步推出绿星评定,并于 2023 年版指南中增设年轻主厨奖、服务大奖和侍酒师奖三个单项奖项。而自 2016 年版港澳指南开始,必比登推介的触角逐渐深入到更接地气的街边小吃,而不拘泥于成规模的餐厅,不少街档小店都开始入选。
其实再往前推,必比登推介是 1997 年增设的项目,可以看出一路走来,米其林指南并非墨守成规,而是在保证基本标准不变的情况下,去适应全球更为多变的餐饮业态。最近二十年,各类其他国际餐饮奖项逐步兴起,影响力亦越发显著,米其林的垄断局面已变,适当的革新不仅是令榜单更好体现餐饮业发展的客观选择,更是榜单长远发展的主观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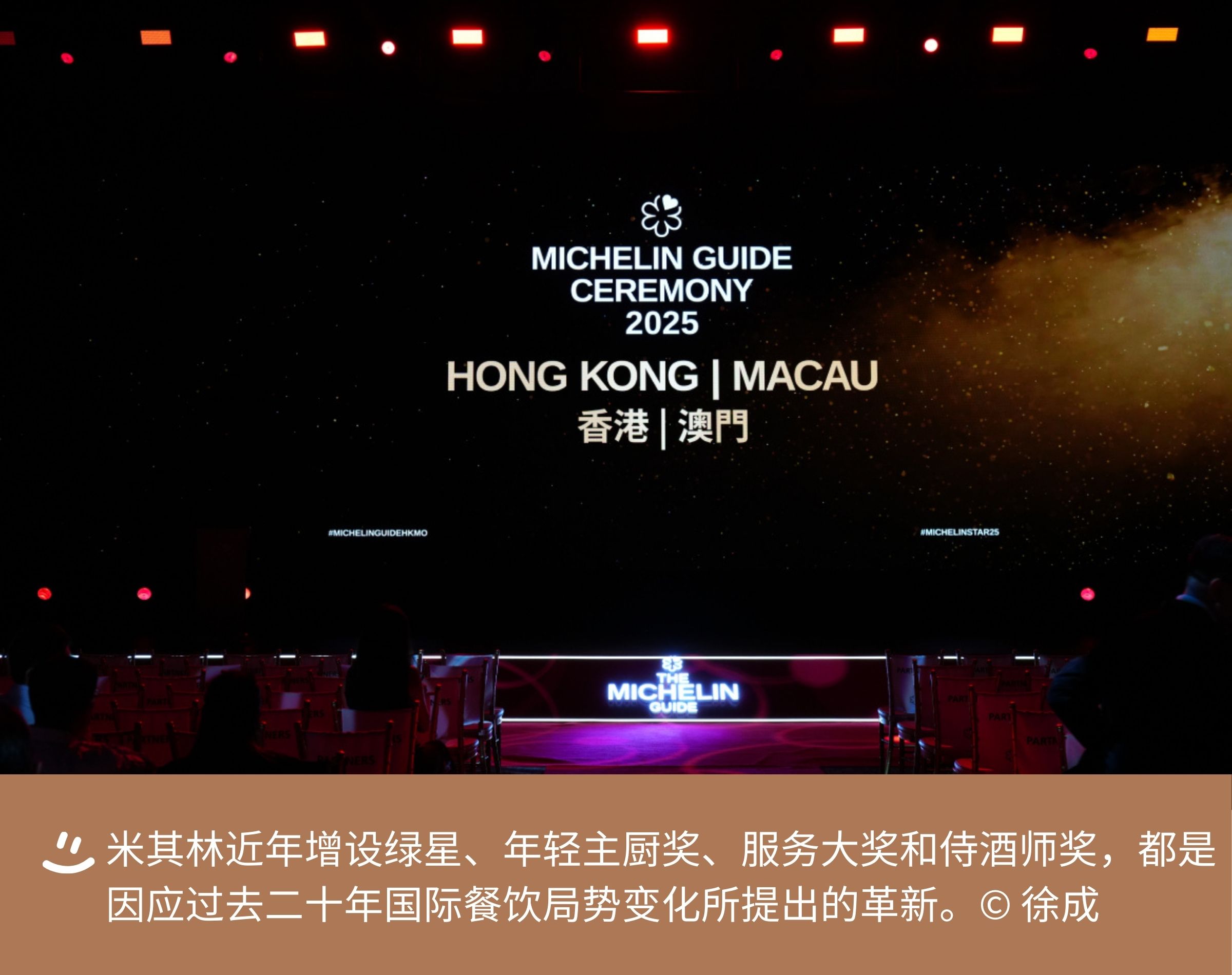
每一年的米其林指南不仅是对餐厅、厨师和餐饮公关的大考,反向来看亦是对米其林自身的考验,榜单能否反映过去一年当地餐饮的新变化,结果是否可令广大食客信服,这都是米其林需要仔细考量的问题。从 2025 年版港澳米其林指南结果来看,米其林还是交出了一份相对令人满意的答卷,但其中遗憾和可改进处亦颇多。
在升星与降星之间,米其林的公道与企图疫情后的港澳指南,可说是前文提及之变革需求的具体实践,今年的结果继续显露米其林指南求变的倾向。 2025 年的榜单最大惊喜在我看来是澳门谭卉从一星升二星,以及十几年来维持二星的 Amber 终于升为三星,这对谭国锋和 Richard Ekkebus 两位主厨都算是“迟来的正义”。


向有“人见人爱”之誉的谭师傅开设谭卉以来,食客多为其一星评价感到不值,如今终于获得实至名归的二星。曾经十分辉煌的 Amber 在装修后的几年里逐渐趋于低调,但 Richard 一直战斗在厨房第一线,对于 Amber 的打磨也从未停息。虽然装修后的 Amber 强调健康环保理念,并停用了奶制品、含麸质食材,坊间很多食客颇有微词,但他的矜矜业业和对行业人才的培养是有目共睹的,这一次的三星更像是对他过去几十年餐饮生涯的肯定,亦是实至名归的。
这几年开始,米其林评审们对本地年轻主厨更为重视,似乎不再痴迷于主厨的家门背景。今年获得年轻主厨大奖的王岁允(Frankie Wong)虽有本地名店的学习经历,但相较那些海外修业履历风光的厨师们而言,他算是本土新星。作为土生土长的香港年轻人,他毕业于香港国际厨艺学院,看简介并无海外顶级名店的修业背景。
俗话说“师父领进门,修行看个人”,这本应是获得广泛公认的判断标准,但考虑到米其林指南面对浩瀚的餐厅海洋,判断什么餐厅值得去探访已是一项耗费大量精力的工作,因此餐厅主厨的背景和派系常作为评审员的判断标准之一。出身名店、师从名厨的主厨一旦独立开店,他们获得评审员关注的机会远高于缺乏显赫名店名厨背景加持的餐厅。虽然指南很难也无必要对一地餐厅做穷尽性的探访,但在判断餐厅是否值得探访时应更关注实际菜品品质和用餐体验,而非主厨的职业路径和派系师承。这样可以鼓励更多有天赋且愿意在餐饮业努力拼搏的年轻人进入行业、展现自己的才华,不拘一格降人才,才能让餐饮业更加充满活力。

最近两年的港澳指南都颇有壮士断腕的魄力,对于拿星多年的老牌名店,尤其是二星、三星餐厅,米其林指南开始摆脱给星惯性,在餐厅未能维持到自身水准时,指南开始不留情面地将其降星。这是一种让自身血液保持健康流动的必要阵痛,亦是维持米其林百年公信力的必然要求。
虽然星级餐厅与指南之间总有难舍难分的羁绊,但当断则断才能显出评鉴的公允客观。当然食客认为应该降星的餐厅与评审员的想法存在差异,每次见到名店被降星,有人称赞的同时也必然有人抱不平,这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不过有些拿星专业户餐厅在坊间的口碑着实一般,但米其林依然连年给予星级评价,甚至主厨换了几波都不影响,这着实令人费解。
百年老店再进化,可行的方向每一年米其林指南依旧能引起食客的广泛讨论,有赞必有弹,应该说没有一份餐厅榜单是完美的,即便如米其林这样的百年老店也依然有维新的空间。
随着世界各地餐饮交流的增进和餐饮人才的流动,各地餐饮图景的多样性越发突出。米其林评审员的背景是否足够多元,以至于他们可以对不同菜系背景的餐厅做出同样公允客观的评价,这个问题是要存疑的。同时,港澳米其林指南对于粤菜之外的中餐重视程度虽然有所提高,但远远不够。

随着港澳与大陆的进一步互联互通,相信后续港澳地区将有更多非粤菜中餐厅开业,亦将有更多大陆品牌来港澳开设分店,建议米其林指南可以多挖掘非粤菜餐厅,相对地,评审员的背景也应更加多元。虽然评审员皆为专业人士,并且广泛拜访各类餐厅,但再专业的人亦受制于自己从小的饮食环境造就的味觉偏好,对于不同菜系很难做到百分百一致公允。因此米其林指南也许后续应该更广泛地招纳评审员,以适应世界餐饮交流的趋势。
米其林对酒店餐厅向来较为重视,近几年来对永续发展和环保理念也相当看重。后续米其林指南应进一步走出酒店,挖掘社会餐厅,并以推广各地饮食文化,增进不同菜系沟通交流为目标之一,而不应过分执迷于饮食本身之外的因素。环保、永续发展这些理念都十分重要,但并非餐饮评鉴的核心要义,侧重上应有合理把握。
对于其他地区有总店,而港澳设有分店的餐厅,应该视乎其运营模式和独立的出品水准分开评奖,而不应受到总店星级的影响。想当年东京鮨金坂本店只有一星的时候,由斋藤孝司师傅主理的金坂赤坂分店逐步从一星升至三星,最后独立为鮨斋藤(Sushi Saito),传为佳话。港澳米其林的评审员其实应该将一些品牌的香港分店视为独立餐厅,每家分店都有主厨,每个主厨的实地表现对餐厅有直接影响,评价时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奖项设置方面,米其林指南增设最佳服务奖是对餐厅服务团队的激励,服务人员的专业付出是用餐体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最佳服务奖应该是颁发给餐厅服务团队而非个人,靠一个人的好服务是无法构建起良好用餐体验的,服务一定是集体努力的结果,任何一环不达标都会影响食客体验。
从香港澳门的星级餐厅情况而言,似乎澳门的日本餐厅较受青睐,而香港大量优秀的日本料理餐厅却未进入指南,这一结果令食客充满疑问。而且疫情后,一些遗珠餐厅一直未能入选确实也令人费解,比如 Wing、好酒好蔡和 Mosu 香港分店,其水准有口皆碑,客观主观上都很难理解至今没有星的原因何在。当然佼佼者如大班楼,至今都只有一星,也令人疑心米其林星级的饮食标准究竟是怎样的,是否受到评审员自身味蕾偏好和习惯的重大影响,这些都是食客非常关心的。

米其林作为有百年历史的餐饮榜单,依然有其自身光环,食客亦仍将其作为觅食参考之一。过去几年,米其林在中国开设多个城市榜单以及福建、江苏两个省份榜单,相信随着米其林指南深入中国市场,中国餐饮将感受到国际上专业标准所在,而评审员的队伍也将越来越多元,他们对于中餐不同菜系的认知必然会逐步提高深入,指南也将从中获益,这是一个双赢的过程。
相较于中国其他城市的榜单,我认为港澳米其林指南应最具国际化特点,这与港澳的人口和文化背景紧密相关。米其林指南入选的餐厅某种程度上既反映了港澳海纳百川的格局,又体现出两地餐厅精工细作的高水准。总体而言,2025 年的港澳米其林指南仍旧全面地展现了港澳餐饮的绚丽图景,为旅行者提供了简便易用的多样化觅食指南。
责任编辑 Hsiang,摄影 徐成,首图 徐成,正文图片提供 谭卉、香港甬府、鮨吉祥 宫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