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写于2023年9月20日:
以下这篇文章,没逻辑、没文化的可以绕过!
洛阳确实有天街,洛阳确实有天街,洛阳确实有天街!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韩愈诗中的天街确实不是指洛阳的天街!不是指洛阳的天街!不是指洛阳的天街!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历代没有任何一位学者认为韩愈诗中的天街是指洛阳天街,没有!没有!没有!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唐诗中只有“天门街”既指“洛阳天街”(定鼎街),又指长安的“朱雀街”,这件事不重要,因为头条上在我相关文章的评论区里有文化的,能正确理解诗词含义的河南人或河南洛阳人并不多,所以就说一遍。顺便说一下,这些没文化的人真是给河南人丢脸。为了公平起见,这句话对类似的陕西人或西安人也一样,包括上海在内的“全国其他地区人民”也一样。
唐诗中有没有一首能从文理逻辑上分析出确定是指“洛阳天街(定鼎街)”的?没有!没有!没有!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如果还有不服的,请在评论区里提供。不过在提供之前,千万别选“非唐诗”以及《和周侍御洛城雪》,《宫词百首》和《酬裴员外以诗代书》这老三篇。我已经在之前的文章里详细分析了这三篇的意思,反证了诗中的天街是指“长安的天街”,包括但不限于“长安朱雀街”。
唐诗中“天街”的意思就是“京城的街道”,不存在任何特指。这件事情很重要,但我已经不想再说三遍!因为你永远叫不醒装睡的人。
题目里的“唐书”是指《旧唐书》和《新唐书》,为什么说“唐诗”要比它们靠谱呢?先看知乎上对这两本书的比较和评价,有文化且有耐心的可以看一下,没耐心的直接看我后面的总结:






我先把重点评论挑出来:
《旧唐书》成书于后晋,唐朝历史文献保存的较为完整,在原始材料上占有较好的条件,《旧唐书》成书之前,唐朝文献多为实录、国史,具有很高的可信度,因此后世司马光在编纂《资治通鉴》唐史部分,史实部分大多采信《旧唐书》部分。从史料学角度来看,《旧唐书》客观上保存了原始文献,对研究唐朝历史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新唐书》大量采用笔记、小说,出现大量错误,《直斋书录解题》批判其“拾取小说私记,则皆附著无弃”,“徒繁无补”。《学林》亦言“盖《国史补》虽唐人小说,然其记事多不实,修唐史者一概取而分缀入诸列传,曾不核其是否,故舛误类如此也。”
也就是说相对而言,《旧唐书》比《新唐书》靠谱一些,为什么说唐诗要比它们靠谱呢?因为这两本史书都是唐朝灭亡之后的后人所编,而唐诗是唐朝人自己写的,即便宋、明、清的个别学者在编录的时候擅自改动了一些字眼,但绝对不会在地名,标题上乱改。
枫桥夜泊张继〔唐代〕
月落乌啼霜满天,
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到客船。
我为什么会扯到张继的这首《枫桥夜泊》呢?因为有人认为“乌啼”是指“乌啼镇”,“江枫”是指“江村桥”和“枫桥”,恭喜“洛阳天街”说的朋友,你们总算找到了“知音”!在你们的认知范围里,从来不知道古诗词里有一种技法叫“意象勾勒”,似乎古诗词里写景的一定是要实写的。居然还有人分析说李白的那句“两岸猿声啼不住”写错了,因为只有一边有猴子。这种诗词分析才叫“吃饱了撑的”!
如果张继的这首诗中的乌啼和江枫成了地名,这首诗的档次就低了不止一个级别,何至于让日本人如此痴迷?古代诗人通过这种意象勾勒,烘托出某种气氛,有时候并非一定是个真实的场景。所以我之前的文章说韩愈诗中的“烟柳满皇都”,这个场景未必是要真的,从文理逻辑来讲,它可以是一个假设的场景,当然也不能排除是真的。但更让我想不通的是:虚构这件事对你们而言,理解起来真的很难吗?
早赴街西行香赠卢李二中舍人韩愈〔唐代〕
天街东西异,祗命遂成游。
月明御沟晓,蝉吟堤树秋。
老僧情不薄,僻寺境还幽。
寂寥二三子,归骑得相收。
当我用上面这首诗证明韩愈诗中的“天街”是指长安的天街时,有人质疑长安哪来的“御沟”(皇宫的河道)和“河堤”?

这位朋友提出的证据绝对要好过一些没文化的喷子,但你选择性失明而无视我文中的这一段又是为什么呢?而且谁说长安没有御沟与河堤的?
 同沈驸马赋得御沟水
同沈驸马赋得御沟水李贺〔唐代〕
入苑白泱泱,宫人正靥黄。绕堤龙骨冷,拂岸鸭头香。别馆惊残梦,停杯泛小觞。幸因流浪处,暂得见何郎。
诗中的沈驸马指驸马都尉沈明(羽),娶唐代宗李豫女长林公主为妻。唐德宗贞元二年公主下嫁,具册礼,唐德宗不御正殿,不设礼乐。此时首都和皇宫不在长安还能在哪(有质疑的可以去查一下史书)?驸马入赘应该住哪?题目里有“御沟”,诗句中有“绕堤”,你说长安有没有御沟与河堤呢?更何况“堤”为什么一定要指“河堤”呢?
沙堤行·呈裴相公张籍〔唐代〕
长安大道沙为堤,
早风无尘雨无泥。
宫中玉漏下三刻,
朱衣导骑丞相来。
路傍高楼息歌吹,
千车不行行者避。
街官闾吏相传呼,
当前十里惟空衢。
白麻诏下移相印,
新堤未成旧堤尽。
诗人张籍就是韩愈诗中的张十八员外,这是不是足以证明“长安大道”又叫“沙堤”?最后“白麻诏下移相印,新堤未成旧堤尽”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一下有关沙堤的解释就知道了:
长安的通衡大道皆为泥土地面,但有雨雪便泥泞不堪。为了便于官员上朝,长安几条主干交通要道铺有沙堤。"沙堤"在唐诗中又有"沙路"、"沙道"、"堤沙"等名称。沙路固然是为了方便百官上朝而修筑,但个别不与要道连通的沙堤有时也专为丞相铺设。《唐国史补》载:“凡拜相,礼绝班行,府县载沙填路,自私第至子城东街,名曰沙堤。”正因为丞相的变更(移相印),所以才有“新堤未成旧堤尽”一说。
沙路曲李贺〔唐代〕
柳脸半眠丞相树,
珮马钉铃踏沙路。
断烬遗香袅翠烟,
烛骑啼乌上天去。
帝家玉龙开九关,
帝前动笏移南山。
独垂重印押千官,
金窠篆字红屈盘。
沙路归来闻好语,
旱火不光天下雨。
这首李贺写的诗中“柳脸半眠丞相树”中的“柳脸”原为“柳睑”,即“柳叶如眼睑”之意。而“丞相树”就是指“柳树”,为什么?看前面那段“沙堤”的解释就该明白了。通过以上两首诗是不是足够说明长安大道叫“沙堤”?这沙堤的两侧是有柳树的? “长安大道”是不是“京城的街道”?是不是印证了古代学者把“天街”解释为“京城的街道”,是泛指而非特指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再来看看“洛阳天街”派们的所谓证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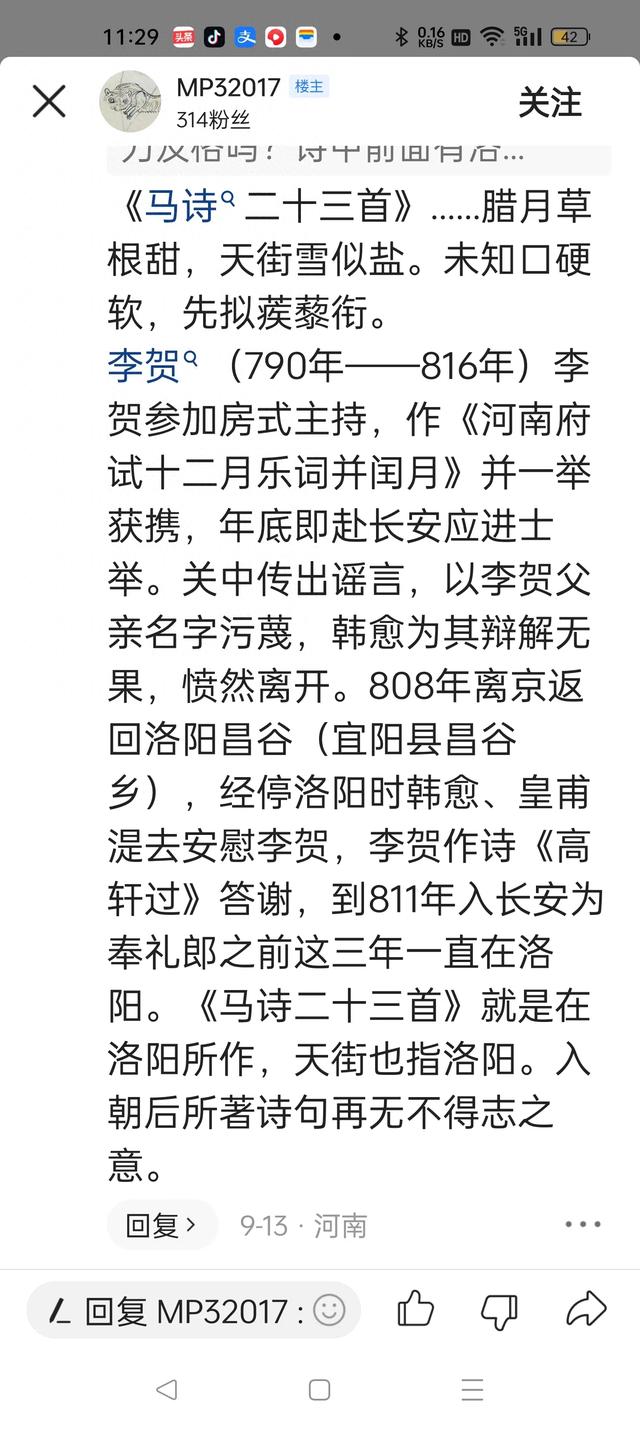


你们不懂我的逻辑我不奇怪,但你们的逻辑我是看懂了:因为李贺和张籍那个时候都在洛阳,而张籍担任水部员外郎后至死在洛阳,所以诗中的“天街”就一定是“洛阳天街”了,而且是实名制的那条。这意思就是:但凡没在北京,就不可能唱“我爱北京天安门”了。然后这位“你说到底什么是真的”嘲讽我说:

好吧,历史确实不是我的强项。但我稍微查了一下:长庆元年(821年),张籍受韩愈荐为国子博士,迁水部员外郎,又迁主客郎中。按你所说,之后张籍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洛阳。不过他写了一首诗,名字叫《送令狐尚书赴东都留守》:
送令狐尚书赴东都留守张籍〔唐代〕
朝廷重寄在关东,
共说从前选上公。
勋业新城大梁镇,
恩荣更守洛阳宫。
行香暂出天桥上,
巡礼常过禁殿中。
每领群臣拜章庆,
半开门仗日曈曈。
题目中的“令狐尚书”是令狐楚,我们来看令狐楚是什么时候做的尚书:大和二年(828年)九月,令狐楚入朝为户部尚书。次年(829年)三月,改任检校兵部尚书、东都留守、东畿汝州都防御使。
我就想问问:如果上述历史和你学的中原历史是一样的,请问从821年开始就一直在洛阳的张籍,如何能“送”828年在京城做“户部尚书”的令狐楚去洛阳呢?难道不应该是“接”吗?你学的“中原历史”到底是谁“编”的?
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韩愈〔唐代〕
天街小雨润如酥,
草色遥看近却无。
最是一年春好处,
绝胜烟柳满皇都。
莫道官忙身老大,
即无年少逐春心。
凭君先到江头看,
柳色如今深未深。
同水部张员外籍曲江春游寄白二十二舍人韩愈〔唐代〕
漠漠轻阴晚自开,
青天白日映楼台。
曲江水满花千树,
有底忙时不肯来。
上面韩愈这首诗的题目中的“白二十二舍人”是指白居易,仅从题目看,是不是足以证明张籍做了水部员外郎之后,和韩愈在曲江春游了?只不过白居易借口忙而不肯来罢了。这曲江岸边的“千树”就算不全是“柳树”,至少也是一大半吧?再加上“长安大道”上的柳树,即便“烟柳满皇都”是真实存在的场景,长安是不是也照样“当得起”?!
酬白二十二舍人早春曲江见招张籍〔唐代〕
曲江冰欲尽,风日已恬和。柳色看犹浅,泉声觉渐多。紫蒲生湿岸,青鸭戏新波。仙掖高情客,相招共一过。
张籍的这首诗题目中的“见招”是“邀请”之意,就算未必是在同一次,至少说明韩愈、张籍、白居易在早春时节共游曲江是他们三个人的“保留节目”。结合张籍的“柳色看犹浅”与韩愈的“凭君先到江头看,柳色如今深未深”,是不是说明张籍很喜欢“深柳”?那么“韩愈用早春时节那若有若无的草色,劝张籍早点出来春游,而不是到晚春柳树遍绿才来”的推测是不是很合逻辑?这三首诗是不是形成了一个可靠的“逻辑闭环”?相较之下,你们的那些证据效力又有多少?
“洛阳天街”派们:不要以为古代的学者都是吃干饭的,就你们发现了新大陆。古代学者的解释不是不能推翻,但你们至少得具备我这样的本事,靠实力、靠理据去推翻!而不是为了要自圆其说,挖空心思地编出一个又一个“历史小故事”,如此鬼迷心窍真该清醒清醒了!你们引以为傲的那条实名制“洛阳天街”,有什么必要非要通过韩愈这首诗来打响知名度呢?
